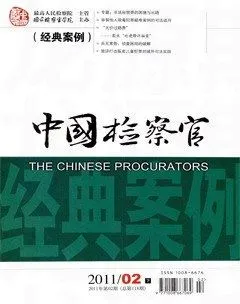容留他人吸毒犯罪疑難案例的司法適用
本文案例啟示:共同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的行為,容留人之間關系的不同、所處的場所的不同,處斷結果是截然不同的;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犯罪主觀方面不及于間接故意,對該類犯罪的懲處應當從嚴,但也應設定一定的入罪和出罪標準:在入罪上可以設定容留的次數或其他情節,出罪上可以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論。
司法實踐中,對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犯罪的認定存在兩個傾向:一方面由于刑法條文對于該罪的構成要件規定較為簡單,犯罪成立的“門檻”過低,有存在打擊面過寬、浪費司法資源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刑法條文對具體的犯罪情節亦未加區分,也存在不能有效打擊犯罪的情形。下文結合近期辦理的審查逮捕案件,分析該罪涉及的幾個法律適用問題。
一、對場所的控制權——合租與同居的區別
[案例一](合租者容留吸毒)2010年3月的一天晚上,犯罪嫌疑人周某某、吳某容留姚某、楊某某及“琪琪”、“韋江”等人在紹興市區燕甸園周、吳二人合租的租房內,共同吸食姚某提供的冰毒1克左右。用某某被刑事拘留,吳某被取保候審。后經紹興市越城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認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故對犯罪嫌疑人周某某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
[案例二](同居者容留吸毒)2010年1月底的一個晚上,犯罪嫌疑人潘某某、胡某容留林某某、周某、鄭某、“光頭”等人在紹興市區潤沁花園,其二人共同居住的房屋內,共同吸食冰毒。潘某某、胡某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被紹興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刑事拘留。后經紹興市越城區人民檢察院審查,對犯罪嫌疑人潘某某、胡某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批準逮捕。
上述兩個案例的不同之處是,前者租房系朋友合租,后者則是戀人同居,檢察機關對第一個案例中的犯罪嫌疑人周某某不予批準的原因在于,犯罪嫌疑人周某某與吳某系合租關系而非同居關系,二人擁有各自的房間,并且吸毒的具體地點是發生在吳某的房間內,故不能對周某某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批準逮捕。
容留他人吸毒罪,是指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場所的行為。如何理解“場所”對理解本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認為此處的“場所”應當理解為主動為他人吸毒提供擁有自主權的場所,這是一個控制權的問題。在合租的情況下,合租者只對自己承租的房間具有控制權,而對其他合租者承租的房間不具有任何權利,如果吸毒行為是發生在其他合租者的房間內,就不能認為其具有提供場所的行為。而同居則不用,同居者對租賃的一整套房屋的任何房間都具有控制權,只要能證明吸毒行為發生在該套房屋中,即可認為租賃房屋的同居者都具有容留行為。當然,其中一名同居者容留他人吸毒,并不能想當然地推定另外的同居者也具有容留他人吸毒的行為,這里還涉及到“主動性”問題,若是同居者對于其他同居者的容留吸毒行為并不知情,根本無法“主動”提供場所,則同樣不能認定該同居者具有容留他人吸毒行為。
二、共同容留他人吸毒實行行為的確定——提供場所與提供毒品的不可分離性
案例二中,犯罪嫌疑人潘某某、胡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其中毒品的提供者為林某某,那么林某某是否構成共同容留他人吸毒的幫助犯。
共同容留他人吸毒的實行行為表現為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場所的行為。在簡單的共同犯罪中,兩個以上的共同犯罪人共同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場所,即構成共同實行犯。然而在復雜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的實行行為則根據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分工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對提供便利條件行為是否能成為共同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實行行為,實踐中有分歧。如案例二,林某某打電話給潘某某,提出去潘與胡的租房吸毒,由林某某提供毒資,潘、胡二人提供場所。顯然,潘、胡二人的行為是典型的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實行行為,即提供場所行為,而林某某的行為則是提供便利條件的行為,這種提供便利條件的行為是否屬于實行行為,實踐中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在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論中,提供便利條件一般屬于幫助行為的范疇,如明知他人要殺人,而為其提供槍支的行為,因此提供便利條件的行為只屬于幫助行為,而不是實行行為,而且容留他人吸毒的實行行為僅僅表現為提供場所行為,并不包括提供便利行為。第二種觀點則認為,這種提供便利條件行為并不是為提供場所提供便利,而是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便利,其行為性質不屬于幫助,而是和提供場所行為形成統一整體,共同為他人吸毒提供了便利,應屬于共同犯罪的實行行為。
我們贊同第一種觀點。刑法理論通說認為,實行行為是刑法分則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就容留他人吸毒罪而言,提供場所的行為是實行行為,只有當行為人實施了提供場所的行為才能認定實施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實行行為。如果根據第二種觀點認為提供便利條件可以成為實行行為,那么將得出,為他人吸毒提供便利條件。即可以構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這顯然和刑法分則的規定相矛盾。因此,提供便利條件是以提供場所為前提的。只有與“提供場所”相結合的“提供便利”行為,才能構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其從屬于提供場所行為,屬于幫助行為。
三、本罪的主觀方面能否及于間接故意
[案例三](放任親屬容留吸毒)犯罪嫌疑人王某系沈某的兒子,二人共同居住,且沈某為房屋產權所有人,一日。沈某聽到王某打電話邀請他人前來自己家中吸食毒品,其并未予以阻止,也未共同參與,而是在王某的朋友到達前,離開了住所,在離開前關照王某在與朋友吸毒的時候必須注意安全,要關好門窗,有陌生人敲門千萬不能開門,防止被公安人員抓住等等。
毫無疑問,本案的王某構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那么沈某是否也構成犯罪呢,關鍵在于容留他人吸毒罪的主觀方面能否及于間接故意。
犯罪故意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犯罪故意的成立,需要同時具備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其中意志因素是直接故意、間接故意區分的標準。直接故意犯罪中,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或者可能發生某種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間接故意犯罪中,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某種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根據刑法條文,容留他人吸毒罪是指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仍然提供場所或者便利條件,表明犯罪嫌疑人主動、積極地實現犯罪目的,追究結果的發生,因此我們認為本罪主觀上不存在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不能及于間接故意。
四、對追訴標準的思考——借鑒容留賣淫罪
[案例四](毒友間相互容留吸毒)2010年3月的一天晚上11時許,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在紹興市市區城北橋附近以400元的價格購入冰毒0.4克。當晚,在市區假日大酒店其所開的房間內,李某某容留犯罪嫌疑人馮某某及唐某某、馮某山等人共同吸食上述購入冰毒。次日晚11時許,犯罪嫌疑人馮某友在假日大酒店樓下,以800元的價格購入冰毒0.8克。當晚,在假日大酒店其所開的房間內,容留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及唐某某、馮某某等人共同吸食上述購入冰毒。
李某某、馮某某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紹興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刑事拘留,后經經紹興市越城區人民檢察院審查,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馮某某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批準逮捕。
本案是犯罪嫌疑人利用臨時性場所相互容留毒友吸毒的情況,對于這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有觀點認為毒友間利用臨時場所共同吸毒,傷害的僅僅是自己的身體健康,對社會危害不大,不宜以犯罪論處,否則有悖于刑法謙抑性原則。我們認為,容留他人吸毒罪侵犯的客體除了他人的身心健康之外,還侵害國家的毒品管制制度,這些為吸毒、注射毒品提供場所的行為,是導致一些地方吸毒者增多和戒毒后又重新吸毒的重要條件。為毒品犯罪提供生存空間的惡劣行徑,也是社會丑惡現象滋生的土壤,必須堅決、徹底地給予鏟除。
誠然,鑒于對毒品犯罪的嚴厲打擊,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成立要求較低,行為人只要有一次犯罪行為,不論容留人數,根據刑法的規定即構成犯罪,也存在著打擊面過寬的傾向,而且刑法未對具體的行為進行區分,實際上也存在著打擊不力的現象。例如有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主觀上出于“還人情”的心態容留他人吸毒。因為別人曾請過自己吸毒,客觀上只有一次容留行為,還有的犯罪嫌疑人具有多次容留他人吸毒、容留未成年人吸毒等嚴重的情節。由于刑法也好,司法解釋也罷,都未對容留他人吸毒中的嚴重情節做出明確的規定。司法人員在實際操作中僅憑個人經驗進行審查、判決,難免會出現司法不公的現象。因此,要解決這一現象,就要對當前的法律法規進行一定的調整。
在完善立法方面。我們認為可以借鑒同為容留類犯罪的容留賣淫罪,對容留他人吸毒行為區別對待,防止刑罰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根據浙江省公檢法三機關《關于辦理傷害等案件中有關法律適用問題的若干意見》第2條的規定:“(1)容留賣淫二人次以上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對容留賣淫只有一人次,但是具有容留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賣淫,或者容留明知有梅毒、淋病等嚴重性病的人賣淫情節的,也應當追究刑事責任。(2)容留賣淫五人次以上的,或者容留賣淫三人次以上,但是具有容留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賣淫,或者容留明知有梅毒、淋病等嚴重性病的人賣淫情節的,屬于情節嚴重。”我們認為完善容留他人吸毒罪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修改刑法中關于容留他人吸毒罪的規定。可將《刑法》第354條修改為:“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三次以上或三人次以上的,或者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
第二,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情節嚴重”的情形。我們認為這幾個方面應當屬于情節嚴重的范疇:(1)具有法定從重情節或兩個以上酌定從重情節的;(2)以營利為目的容留他人吸毒、注射毒品的;(3)容留他人吸毒、注射毒品并提供吸食工具或者毒品的;(4)國家工作人員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5)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6)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7)其他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情節嚴重的。
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未達到三次以上或三人次以上,具有上列情形的,亦可以按照本條規定定罪處罰。
上述幾種情形中,以營利為目的而進行容留,表明行為人主觀上有從事毒品犯罪的故意;容留他人吸毒并提供工具或毒品,表明行為人有傳播毒品的故意,這種行為將嚴重危害正常的社會秩序;國家工作人員相對于人民群眾而言身份具有一定特殊性;容留他人吸毒造成嚴重后果的已經產生了嚴重社會危害性,從根本上就不符合“從寬”處理的基本原則;將容留未成年人進行規定主要因為未成年人作為國家的未來,心智正在發育,所以要進行特殊保護。因此,我們認為上述幾種情形的社會危害性、主觀惡性都遠遠高于一般的容留他人吸毒行為,所以應將其納入從重處罰的情形進行規定,這樣有利于司法機關有針對性地打擊毒品犯罪。
第三,完善《治安管理處罰法》。將容留他人吸毒罪的門檻提高到容留三次或三人,并不意味著三次或三人以下不受處罰,而是不將其納入刑法調整的范疇。我們認為應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2條中可增加1項:“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不足三人或三次的。”結合前文中所述刑法之規定,對于容留他人吸毒行為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懲罰體系。
五、出罪的路徑選擇
[案例五](出租車司機容留他人在車上吸毒)張某是出租車司機,某日晚10時許,兩名乘客李某、孫某搭乘其出租車,并讓張桌在城里轉。二人上車后不久,即拿出毒品在車內吸食。張某發現后來有任何表態,仍載乘二人繼續行駛。二人在車上吸完毒品后,又逗留半個多小時后下車。二人如數支付了車費,并多給了張某20元錢。后來二人因實施犯罪而被逮捕,交代了在張某的出租車內吸毒的情況。
該案例登載于《人民檢察》2008年第6期,作者在文中引入了期待可能性理論,其認為張某在出租車中容留李某、孫某吸毒的行為,可以認為其缺少期待可能性,因而對張某不追究刑事責任。理由有三:第一,出租車司機沒有任意拒載的權利;第二,出租車司機沒有報案的義務;第三,就本案而言,從當時情勢判斷,如果張某停車讓二人下車,可能會遭到人身安全上的危險,作者認為對于發生在出租車上的犯罪,出租車司機當然有義務,在有能力的情形下加以制止。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張某如果要二人停止吸毒或者讓二人下車,他就有可能遭受到人身安全上的威脅。因此,對張某而言是缺乏期待可能性的,進而應否定其刑事責任的存在。
以期待可能性作為出罪的理由,我們認為不失為一條路徑選擇。判斷容留他人吸毒行為的可罰性,首先應考慮法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間的權衡,是否存在義務違反,行為本身是否制造了不被允許的危險等,如果行為缺乏期待可能性,可以作為否定刑事責任的一種途徑。我們同時認為娛樂場所的經營者為招徠顧客而容留他人吸毒的行為,不能以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作為其免受刑事處罰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