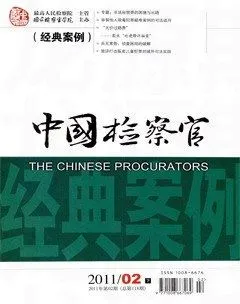女友使用其男友盜竊所得的贓款的行為定性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洪某與其女友楊某共同租住在麗江市古城區一出租房內。二人沒有工作,也沒有其他正當收入來源。2010年8月至11月之間,犯罪嫌疑人洪某以古城客棧內游客為目標,先后盜竊5起,涉案物品有筆記本電腦、數碼相機、攝像機等電子設備,黃鶴樓等名煙9條,以及人民幣現金若干,涉案物品總價值3萬余元,所盜財物被洪某變現為現金。每次盜竊完成回到租住房之后(楊某事先不知情),洪某總是會分給其女友一定的金錢,其女友對于金錢的來源明知。但是沒有參與盜竊的實行行為,全部贓款被二人用于日常生活開支。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認為楊某構成盜竊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楊某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楊某不構成犯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首先,洪某的女友楊某不構成盜竊罪的共同犯罪。五起盜竊案,均為犯罪嫌疑人洪某一人所為,楊某慫恿、鼓勵洪某進行盜竊的表現非常不明顯。卷內其他證據也未反映犯罪嫌疑人楊某參與盜竊的具體實行行為,只是參與事后的分贓行為。那么,楊某是否與其男友進行了密謀等幫助行為呢?當然從五起盜竊案來看,楊某盡管沒有明確的支持其男友進行盜竊,卻也“心安理得”的使用盜竊得來的贓物、贓款,至少已經默認了其男友的盜竊行為,其對男友的盜竊行為采取的是無所謂的態度;然而默認其盜竊行為。并不能代表二人形成了盜竊的合意。二人形成盜竊的共謀,至少要為盜竊“出謀劃策”,對其男友的盜竊行為進行“智力支持”。然而,本案的五起盜竊,二人沒有進行任何事前交流,均為犯罪嫌疑人洪某自己作案,事后將贓款分給楊某消費。因此,二人之間并沒有形成盜竊犯罪的合意,不屬于盜竊的共謀共同正犯,也不屬于盜竊罪的幫助犯。
那么,楊某的行為是否屬于盜竊罪的教唆犯呢?從整個系列盜竊的案情來看,楊某的無所謂的“心理暗示”對其男友有一定的心理支持力。但是這種心理上的支持力很難講引起了洪某盜竊的犯意,因為,每次盜竊,都是洪某偷完東西之后,楊某才知道,也就是每一次具體的犯意產生,都是洪某的發揮的主觀能動性,楊某并沒有挑起其男友的犯意。楊某的漠視其男友的盜竊行為,頂多是強化了其男友的犯意,讓其男友主觀認為,自己“所謂的愛”得到了女友的認可,但是教唆犯的最重要的主觀構成要件就是“挑起犯意”,因此,楊某的行為也不屬于盜竊罪的教唆犯。
其次,楊某的行為涉嫌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第19條將《刑法》第312條修改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與原來的條文比較,擴大了犯罪行為方式,增加了“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兜底規定。
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應當如何理解?所謂窩藏,就是隱藏贓物或者替犯罪分子保管贓物使其不能或者難以發現。轉移贓物是將贓物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的行以逃避司法機關偵查。收購贓物主要是指以牟利為目的而購買贓物的行為。代為銷售則是受本犯犯罪人委托,幫助其銷售贓物的行為。
“其他掩飾、隱瞞方法”,是指法條列舉的四種方式以外的其他能夠起到“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作用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介紹買賣、典當、拍賣、抵押或者用其抵債,以及提供虛假證明、發票或者涂改原始標識,對原贓物進行加工等行為,都屬于本罪的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的行為。從司法實踐來看,常見的“其他掩飾、隱瞞方法”除了上述司法解釋中列舉的方法以外,主要還包括收受、介紹買賣等方法。
由于本案犯罪嫌疑人楊某的行為表現為無償收受贓款。顯然不屬于窩藏、轉移、收購和代為銷售,那么該種無償收受行為是否屬于“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兜底性規定呢?有學者認為,“收受”是指不支付對價而取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為,包括作為贈物予以接受、無利息的消費借貸等。無償收受,在取得了處分權這一點上,與保管沒有取得處分權有區別。從其他國家的立法來看,一般都將收受犯罪所得的行為規定為贓物犯罪。如《日本刑法》第256條規定:無償受讓盜竊贓物或其他相當于財產犯罪的行為所領得之物的,處3年以下懲役。搬運、保管或者有償受讓前項規定之物,或者就該物的有償處分進行斡旋的,處10年以下懲役及10萬日元以下的罰金。
中國《刑法》第312條贓物罪盜的行為方式規定的比較籠統,沒有采取窮盡式的列舉方式,可能是立法者考慮到飛速發展的社會現實,無法預測到以后新型的犯罪方式而采取的一種謹慎的態度,同時也為日后的司法解釋留下必要的立法空間。盡管我國《刑法》第312條并沒有明確列舉出“收受”的行為方式,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六)》出臺之后,將“收受”理解為“其他方法掩飾、隱瞞”也是該法條的應有之義,因為窩藏里面保管之意,沒有取得處分權的行為尚且作為該罪的規制方式,“無償收受”這種取得處分權的行為方式當然更應該是該罪的規制方式,“舉重以明輕”在這里得到適用。同時,從域外立法來看,對于贓物罪均有進行兩種量刑幅度,收受行為法定刑較輕,《刑法》第312條修訂之后也是兩種量刑幅度。分別是3年以下和3到7年有期徒刑,這就為“無償收受”行為的規制提供了更加合理的法定量刑空間。
從本案反應的案情來看,犯罪嫌疑人洪某將盜竊所得財物變現為金錢和盜竊得來的金錢,供二人生活開支,期間不管贓款如何分配,因為二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已經無法具體區分每筆錢歸誰所有,而應認定為共同支配,在此種情形下,犯罪嫌疑人楊某無償收受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已經涉嫌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最后對于第三種意見。有同志認為,本案犯罪嫌疑人洪某與楊某屬于同居的男女朋友關系,對于洪某盜竊來的財物的使用當然“理所當然”,讓其女友舉報、制止男友的行為不具期待可能性。筆者認為,期待可能性作為超規范的免責事由,應當慎用,罪與非罪的唯一區分標準是構成要件,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討論違法性和有責性的問題,而不能一開始就討論免責性的問題,況且,中國傳統刑法理論是主客觀四要件齊備說,德日的三層次理論可以借鑒但不可盲目崇拜。犯罪嫌疑人楊某的行為經過上面的分析構成贓物罪無疑,但是是否可以根據我國《刑法》13條但書的規定,認為是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呢?筆者以為不可,五起系列盜竊案,涉案金額達3萬元,楊某一直“坐享其成”,主觀惡性不可謂不深,同時法律對于“同居”關系也不予保護,法律只是保護“近親屬”關系。鑒于此,楊某不構成犯罪的說法也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