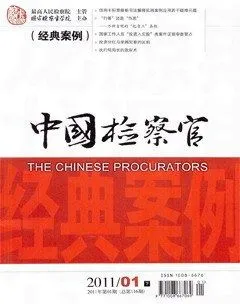以詐賭方式獲取錢財的行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吳某、何某及王某某為獲取錢財,預謀約出馮某某以“悶雞”的形式進行賭博,商定由何某、王某某配合昊某通過洗牌作弊、言語暗示等手段,使馮某桌輸錢,言明賭博的輸贏由昊、何分擔,王某某每參賭一次得“工資”2千元,又商定由曲某某為賭博“放水”,即放高利貸,并每場抽頭獲利2萬元。后吳某約王某某、曲某某,何某約馮某某于2010年1月6日至9日,以上述方式賭博三場,馮某某共計輸掉34萬元,吳某、何某實際各得9萬余元。王某某得“工資”6千元,曲某某得款6.4萬元。后因馮某某報案而案發。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吳某、何某、王某某、曲某某的行為不構成賭博罪。理由是:《刑法》第303條規定聚眾賭博必須組織三人以上,一般理解為被組織參與賭博的人數至少應在3人。而本案中吳某只約了王某某,何某只約了馮某某,均未組織3人以上,吳某、何某、王某某的行為不應以賭博罪論處。曲某某雖為賭博活動提供資金,但因吳某、何某構成賭博罪的前提不成立,也就不能對曲某某以賭博罪的共犯論處。
第二種觀點認為,吳某、何某、曲某某的行為構成賭博罪,王某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吳某、何某的行為符合《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條第(2)項規定:組織3人以上賭博,賭資數額累計達到5萬元以上的,屬于《刑法》第303條規定的聚眾賭博。曲某某明知他人賭博而提供資金,是賭博罪的共犯,也應以賭博罪追究刑事責任。王某某因不屬于聚眾賭博的組織者,不應以賭博罪追究刑事責任,這是立法者對賭博犯罪與違法行為的一個限定。
第三種觀點認為,吳某、何某、王某某、曲某某的行為構成賭博罪。理由是:《關于設置圈套誘騙他人參賭又向索還錢財的受騙者施以暴力或以暴力威脅的行為應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規定:“行為人設置圈套誘騙他人參賭獲取錢財,屬賭博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以賭博罪定罪處罰。”本案的四嫌疑人實施了誘騙他人參賭獲取錢財的行為,均應構成賭博罪。
第四種觀點認為,吳某、何某、王某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理由是:吳某、何某、王某某共謀,有針對性地預謀選定馮某某并誘騙其參賭,設置欺騙性質的“賭局”,通過直接控制賭博輸贏結果來騙取錢財,賭博是吳某等人詐騙的一種手段。因此,吳某、何某、王某某的行為應定詐騙。曲某某因未參與詐騙的共謀,不構成犯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四種觀點。賭博罪與詐騙罪的區別主要在于行為方式的不同,獲取錢財主要是靠“賭局”或“騙局”是區分兩罪的關鍵。
(一)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均不構成賭博罪
首先,關于設套誘賭的《批復》在《解釋》發布之前,本案并不完全符合“批復”的情形,不能機械地套用。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的精神,司法解釋的形式分為“解釋”、“規定”和“批復”三種。“批復”是指對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就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請示所作的答復。因此,盡管批復也是司法解釋的一種形式,但它畢竟是最高人民法院對某個或某類特定案件的答復,必然有著嚴格的適用標準。該“批復”主要適用于多人團伙在公共汽車站、火車站等公共場所設置賭博游戲的情形,同時該“批復”并不包含對所有在賭博過程中采用欺騙手段騙取他人錢財的行為,一律以賭博定罪處罰的意思。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并不是在公共場所設置游戲等待不特定的被害人上鉤,而是事先選擇好特定對象,將其帶到借用的他人屋內進行詐賭,侵犯的客體是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而不是社會管理秩序。
其次。對“解釋”中“組織”一詞的理解,必須從立法本意出發,結合社會生活事實,進行合理解釋。《漢語大詞典簡編》對“組織”一閱的解釋是:“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務和系統加以結合。”因此,在事實上必然存在著組織者和被組織者兩個對應的方面。在一個組織單元里,說某人既是組織者,又是被組織者,是不符合同一律的邏輯要求的。依據“解釋”規定,聚眾型的賭博罪每次被組織參與賭博的人數至少應在3人以上,否則不能稱之為聚眾。本案中,吳某與何某均是犯意的提起者,兩人之間不存在誰組織誰的關系,屬于互相糾約。王某某、馮某某分別是被吳某、何某組織來參賭的。從共同犯罪的角度看,吳某與何某只是組織了兩個人參賭。聚眾型賭博罪的打擊重點應當是“賭頭”、“賭棍”一類,往往被其組織參賭的人員多,規模大,影響惡劣,類似于本案這種特定“圈子”的賭博形式,作為聚眾賭博予以打擊,有點過寬。或許有人以聚眾斗毆罪中的“組織”行為進行類比,因為只要有斗毆故意的一方參與斗毆的人數達到3人就可認定為聚眾,這里的3人毫無疑問是包括組織者本人的,進而推斷本案也屬于聚眾型賭博,其實不然。我們知道。聚眾斗毆罪的打擊重點是首要分子、積極參與者,一般的參與人員是不作犯罪處理的,之所以認為此罪中的3人包括組織者本人,乃是定罪處罰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而且,首要分子糾約人員后,并不排除其他人員再次糾約他人參與斗毆,只要是首要分子授意或默許,客觀上進行了斗毆活動,也認定為受其組織參與斗毆,是符合共同犯罪理論的。只有將本案中的吳某、何某認定為互相組織。才勉強達到“組織3人以上賭博”的底線,這樣的結論是不符合大眾認知標準的。
(二)犯罪嫌疑人吳某、何某、王某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曲某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一般來講,賭博必然包括欺詐,但賭博中的欺詐手段,是通過行為人熟練掌握賭博技巧、結合運氣及心機等來完成的。如果一方采用欺詐手段來支配、控制輸贏,已經單方面確定了勝敗的結果,就不能稱為賭博,而屬于詐騙行為。實踐中常見的有:事先串通、有意識地排座位、偷換牌、遙控骰子或暗中窺視對方牌點等方法往往貫穿于賭博的整個過程,使得另一方信服“愿賭服輸”而自愿賭博輸錢。實際上是以賭博之名,行詐騙之實,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從本案整個行為過程來看,犯罪嫌疑人吳某、何某、王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事先演練并串通作弊手法,約定互相配合,形成了“三打一”局勢,將被害人引入賭博圈套,賭博中采用做牌使詐、言語暗示欺騙被害人,使其有輸無贏。為了獲取被害人更多的錢財,事先連“放水”的高利貸者也選定。可見,本案完全是一場騙局,而不是賭局。被害人被蒙騙輸掉30余萬元的結果,正是犯罪嫌疑人吳某、何某、王某某運用欺詐手段控制牌局形成的,賭博中輸贏的偶然性早已喪失。從王某某不負擔輸贏,每次得“工資”2千元,更足以反映出被害人輸錢的必然性。因此,認定吳某、何某、王某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是符合事實的。而曲某某在主觀上認為,自己就是給賭博的人放高利貸,并抽頭獲利,客觀上事先未參與吳某等人的詐賭預謀,賭博時也不在場,參與賭博的人員更不是其組織而來,因吳某等人賭博罪不能成立,其賭博罪的幫助犯無從談起,也不構成詐騙罪。曲某某的行為是否涉嫌其他犯罪,有待補充偵查后才能判明。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