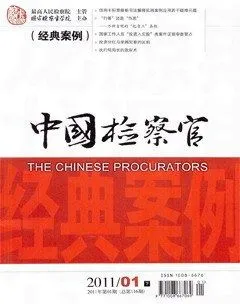國家工作人員“投資人實股”類案件證據(jù)審查要點
案名:甲某受賄案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甲某,系某基層派出所所長,掌握管轄區(qū)域內(nèi)礦山開礦用炸藥審批權(quán)。檢察機關(guān)查明,2008年至2009年間,甲在了解到礦洞已出礦的情況下,分別向私營煤礦礦主乙、丙、丁三人提出投資入股礦洞,并向三個礦洞投入實股總計24萬元(其中12萬系甲的朋友委托甲的投資),后乙、丙、丁三人總計向甲“分紅”138萬余元,其中80萬元系甲朋友的“分紅”款,由甲轉(zhuǎn)交,甲實得“分紅”款58萬元。
本案偵查終結(jié)后,移送檢察機關(guān)審查起訴。公訴部門認為,甲人實股的行為顯系利用職務(wù)之便,強行向被害人索要財物的行為,屬索賄,因此構(gòu)成受賄罪。檢察機關(guān)指控甲索賄的證據(jù)主要是乙、丙、丁三人的陳述。三人的陳述證明因甲握有礦山炸藥審批權(quán),因此當其向三人提出入股礦洞時,雖然三人表面上沒有拒絕,但三人心理上其實并不愿意讓甲入股,但迫于甲的地位和職權(quán),三人害怕不給甲人股會被其打擊報復(fù),所以只得讓其入股。與三人的陳述相對,甲供稱,當其提出入股礦洞時,三人并沒有拒絕,并且其入股過程相當順利,也沒有遭到礦洞其他股東的任何反對,其投資人股系共同合意的結(jié)果。同時,有煤礦主戊的證言證明,甲曾于2008年向其提出過入股干礦的想法,但戊沒有同意,此后甲在炸藥審批過程中也未對戊進行過打擊報復(fù)。還有證據(jù)證明,甲在人股乙、丙、丁三人的礦洞前,曾投資過另外兩個礦洞,但投資失敗,血本無歸。本案一審時,控辯雙方就甲的入實股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385條所規(guī)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的情形展開了激烈的對抗。一審法院判決認定,檢察機關(guān)指控甲索賄的證據(jù)不足,甲的行為不構(gòu)成受賄,只違反了禁止國家工作人員不得從事營利性的經(jīng)營活動的“禁止性規(guī)定”,應(yīng)受行政處罰,但不屬于犯罪。
一、訴訟中反映出的證據(jù)審查問題
從已發(fā)生的訴訟過程來看。一審焦點在于甲的行為是否屬于利用職權(quán)進行索賄。然而,分析一審判決后發(fā)現(xiàn),一審法院之所以認為甲不構(gòu)成索賄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僅憑被害人的陳述無法得出甲索要財物的行為存在,不排除甲在提議“干礦”時,被害人與甲之間確實存在雙方一致同意的“合意”。另一方面,煤礦主戊的證言至少證實在甲投資礦洞這件事上并不存在“只要礦主不同意甲人股就會被甲打擊報復(fù)”的鐵定規(guī)律。因此,僅依靠現(xiàn)有證據(jù),無法得到甲索賄的惟一結(jié)論。而且甲前兩次投資失敗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甲入股投資的真實性。然而,這還不是本案之所以公訴失敗的關(guān)鍵原因所在!
我們認為,就本案來說,一審檢察機關(guān)將訴訟爭點歸納為“是否索賄”才是本案之所以公訴失敗的關(guān)鍵原因,這是一個控訴方向性的錯誤!原因在于:檢察機關(guān)錯誤將證據(jù)審查的火力集中在是否存在索賄這一受賄的手段確證上,而放棄了對甲是否構(gòu)成受賄罪的本質(zhì)審查。是本末倒置!
通說認為,受賄罪保護的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wù)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也可以說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wù)行為與財物的不可交換性。這種法益不是個人法益,而是超個人法益。受賄行為所索取、收受的財物是賄賂。賄賂的本質(zhì)在于,它是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wù)有關(guān)的、作為不正當報酬的利益。它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wù)行為之間存在對價關(guān)系。不正當報酬不要求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wù)行為本身是不正當?shù)模侵竾夜ぷ魅藛T實施職務(wù)行為時不應(yīng)當索取或者收受利益卻索取、收受了這種利益。因此,受賄罪與其它個罪相區(qū)別的本質(zhì)在于國家工作人員職務(wù)廉潔性的“被出賣”,國家工作人員職務(wù)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被破壞”。其行為特點表現(xiàn)為國家工作人員以出賣職務(wù)的廉潔性為前提,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換取“出賣職務(wù)廉潔性”的對價。也就是說,在受賄的行為結(jié)構(gòu)中,國家工作人員除了利用自身的職務(wù)之便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外,也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報酬,國家工作人員所獲得的不正當報酬就是其出賣職務(wù)廉潔性的對價,這是一個行賄人與受賄人“一拍即合”的雙贏模式。與“一拍即合”這一普通的受賄模式相對,索賄是“一拍即合”模式的變種,即只有受賄者的“拍”而沒有被索賄者的“合”,這是一個國家工作人員主動出賣。而被索賄者被動接受的行為模式,也可稱為“強買強賣”。然而,不論“一拍即合”和“強買強賣”行為模式之間的區(qū)別有多大,但其相同點都在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wù)之便,以職務(wù)廉潔性為出賣“標的”,與他人進行對價“交易”并換取不正當報酬,至于是否為他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則可以在所不問。只是在行為危害性的比較上,“強買強賣”比“一拍即合”更具有危害性,因為“一拍即合”模式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守株待兔,表明受賄行為人對于國家法律的威懾還有所顧慮,而“強買強賣”型的索賄人已經(jīng)突破了法律容忍的底限,主動利用權(quán)力向外尋租,是對公權(quán)力的公然濫用,是對法律權(quán)威的公然蔑視!這也是為什么在司法解釋和刑法解釋論上將索賄與普通受賄區(qū)別解釋的原因所在。如目前的司法解釋認為索取他人財物,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均可構(gòu)成受賄罪。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必須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才能構(gòu)成受賄罪,但是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xiàn),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
如果以上有關(guān)索賄和普通受賄的區(qū)別能夠得到認可,則不難看出在前述案例中,公訴方的控訴方向出現(xiàn)重大偏差,僅僅依靠并不充分的證據(jù)就貿(mào)然指控甲索賄,而放棄了對甲是否有出賣職務(wù)廉潔性以換取不正當報酬的情形進行更為詳細的證據(jù)審查,致使本案在一審公訴失敗。
二、國家工作人員“投資入實股”類案件的證據(jù)審查要點
從前述案例可以看出,由于國家工作人員“投資人實股”類案件涉及到罪與非罪、普通受賄與強行索賄的區(qū)別,因此為了確保法律的正確適用,刑罰權(quán)的合理發(fā)動,因此對于此類案件,除了應(yīng)遵循普通受賄案件的證據(jù)審查規(guī)律外,如是否利用職務(wù)便利,是否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等情況。還應(yīng)著重進行以下三方面的證據(jù)審查工作。
第一,審查國家工作人員投資人股的本金與收益之間的比例是否適當。這包括幾方面的內(nèi)容:一要查明是公司(或合伙)的股東結(jié)構(gòu)和股本結(jié)構(gòu)。二要查明公司(或合伙)中其他股東的投資與收益比例情況,以確定公司(或合伙)股份的收益情況,如前案中,乙、丙、丁三人的投資回報率各是多少?三要查明國家工作人員股東的投資與收益的比例是否處于公司(或合伙)股份收益的正常范圍內(nèi),這里需要特別注意如果國家工作人員股東在公司(或合伙)的經(jīng)營活動中承擔了主要的經(jīng)營活動,經(jīng)其他股東同意,則應(yīng)允許其投資與收益的比例超過股份收益的平均值,但應(yīng)有一個合理限度(如150%或200%),反之則反是。又或者在公司章程(或合伙成立規(guī)約)中明確記載有股份收益分配比例,則要查明國家工作人員股東的股份收益情況是否與書面記載相符,不相符的情況下是否有合理說明及其它證據(jù)的印證。如新修訂的《公司法》第35條規(guī)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分取紅利: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有權(quán)優(yōu)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認繳出資。但是,全體股東約定不按照出資比例分取紅利或者不按照出資比例優(yōu)先認繳出資的除外。”就甲案而言,則要求檢察機關(guān)審查清楚甲投入12萬元并獲得58萬元的投資回報是否屬于甲、乙、丙三人所經(jīng)營煤礦的正常投資回報率范圍?是否有超出部分?超出部分是否有依據(jù)?
此方面的證據(jù)審查是國家工作人員“投資人實股”類案件證據(jù)審查的重點。其審查目的在于查明國家工作人員的投資與收益之間是否符合正常的投資回報規(guī)律。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投資入股的收益明顯超過正常的投資回報率,且無法做出合理解釋,則可以肯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超額收益屬于賄賂。
第二,審查國家工作人員投資入股后是否與其他股東一道分擔公司(或合伙)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成本和經(jīng)營風險。正常的投資是以“共同出資”、“共同經(jīng)營”、“共擔風險”為表現(xiàn)形式。同時,我國《公司法》規(guī)定分擔公司生產(chǎn)經(jīng)營成本和經(jīng)營風險是股東是否參與公司管理經(jīng)營,是否履行公司股東義務(wù)的一項重要證據(jù)。
審查此方面的證據(jù),其目的在于配合第一方面的證據(jù)審查結(jié)論形成穩(wěn)定的證據(jù)鎖鏈。一是確證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是真實的股東,如果國家工作人員股東只有投資入股而沒有正常分擔公司生產(chǎn)經(jīng)營成本和經(jīng)營風險的,甚至當公司破產(chǎn)后,國家工作人員還能確保自己的“本金”得到退還,則國家工作人員股東的身份不真實,在不參與經(jīng)營、不承擔經(jīng)營風險的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的微小股本投入僅僅是幌子,其目的在于掩蓋受賄本質(zhì),獲取不正當報酬。二是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分擔了公司(或合伙)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成本和經(jīng)營風險,則可以進一步查明國家工作人員股東所獲收益與其對公司(或合伙)運營的貢獻是否相符,其所獲投資回報的超過部分是否合理。
第三,審查國家工作人員在投資人股時是否有強迫其他股東接受其入股的情況。這包括以下三個環(huán)節(jié):一要審查在案被害人的證言是否有其他證據(jù)相印證,如其他在場人員的證言、錄音、錄像等。二要審查被告人在原職位時,是否具有其它投資入股的機會。如甲案中,則要審查清楚甲管轄范圍內(nèi)共有多少個礦洞可以投資?甲是否向所轄范圍內(nèi)的所有礦洞(或大部分礦洞)都提出過入股干礦的要求?如果提出過,其他礦主的反應(yīng)是什么?其他礦主是否拒絕過甲入股干礦的要求?如果前一環(huán)節(jié)的審查可以得出肯定的結(jié)論,則要進一步審查國家工作人員投資者在其投資要求被拒絕的情況下,其后續(xù)反應(yīng)如何。如甲案中,甲是否對拒絕其入股干礦的礦主進行過打擊報復(fù)等。也正是在甲案中,煤礦主戊的陳述直接擊毀了乙、丙、5MzRlVBDcl5FRjVvP79MrojzAbuZLJzf8fhEI4N77xE=丁三人的陳述,使審判法官沒有形成“只要礦主不同意甲入股礦洞就會被打擊報復(fù)”的內(nèi)心確信。
此方面的證據(jù)審查目的在于將被害人的內(nèi)心想法(如害怕被打擊報復(fù))客觀化、具體化,使被害人的證言能夠得到主客觀兩方面證據(jù)的呼應(yīng)。此類證據(jù)也是確認案件中是否存在“索賄”行為的關(guān)鍵。
三、結(jié)語
司法實踐是司法人員個人激情充分發(fā)揮的戰(zhàn)場,但司法實踐不是個人的主觀想像,所有的控辯都必須根基于真實的證據(jù)事實之上。法學理論要成為實踐中有成效的武器,必須有真實的證據(jù)事實做支撐。特別在是刑事審判法庭上,證據(jù)才是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和最終檢驗法律適用妥當與否的依據(jù),沒有證據(jù)就沒有進一步適用法律的余地。正確認識每一份證據(jù)的價值,正確組織證據(jù)才是司法實踐的治勝之道;相反,脫離證據(jù),或者錯誤認識證據(jù)價值將會使司法實踐成為一場亂戰(zhàn),再深厚的法學理論也不可能在這場亂戰(zhàn)中產(chǎn)生任何有影響力的作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律的生命既在于經(jīng)驗,更在于證據(jù)。本文試圖通過對真實案例的分析,圍線著受賄罪的核心——“職務(wù)廉潔性的被出賣”進行證據(jù)審查,舉一反三,用以說明不論是對于控方、還是辯方,證據(jù)審查都是展開訴訟攻防的第一步,而所有的證據(jù)審查工作都必須也應(yīng)該圍繞著罪名的內(nèi)涵——即構(gòu)成要件來展開。脫離罪名內(nèi)涵來審查證據(jù),即可能錯誤組織證據(jù),形成錯誤的控辯方向,也可能在實踐中以訛傳訛形成理論與實踐相脫節(jié)的假象。這里,本文至少有兩點基本看法:
第一,證據(jù)審查者在審查證據(jù)時不能脫離罪名的構(gòu)成要件來獨立進行證據(jù)審查工作,證據(jù)審查者的眼光必須始終在案件事實和罪名的構(gòu)成要件之間往返回復(fù),既要圍繞著擬訴罪名構(gòu)成要件各要素的內(nèi)容為指導(dǎo)來甄別證據(jù)價值,組織證據(jù),又要根據(jù)證據(jù)材料來考慮擬訴罪名的準確與否,量刑輕重是否合適。
第二,證據(jù)審查者在證據(jù)審查時,必須要對擬訴罪名構(gòu)成要件所反映的犯罪本質(zhì)特點有明確的認識,這樣才能對現(xiàn)有證據(jù)的價值予以正確評估,否則將會出現(xiàn)錯誤組織證據(jù),形成錯誤訴訟方向的結(jié)局。如甲案中,如果檢察機關(guān)能夠查明甲所獲58萬元紅利與其12萬元的投資相比確屬超額收益,則甲在其職權(quán)管轄范圍內(nèi)投資人股獲取超額利潤的行為就可認定為受賄,完全不應(yīng)該僅憑乙、丙、丁三人的陳述就將證據(jù)審查的重點轉(zhuǎn)向甲提出入股礦洞時是否會對他人產(chǎn)生心理脅迫,是否是“索賄”這一錯誤方向上。事實上,乙、丙、丁三人的陳述與甲的供述相互印證,已經(jīng)證明了甲利用職務(wù)之便入股12萬元分紅58萬元的事實。檢察機關(guān)剩下的任務(wù)就是進一步查明這58萬元紅利是否屬于超額收益。
責任編輯: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