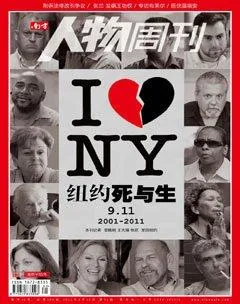“家族政治”與“縣政特色”
2011-12-29 00:00:00何三畏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31期

一位社會學博士在中國中部某縣“掛職”后,寫出一篇討論“縣政”的論文。9月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摘編了“政治家族”一節。中國政治權力機構非常神秘,但“縣政”是公眾的目光勉強夠得著的政治基層,特別是因為在互聯網,縣政正在解脫神秘。因此,這篇文章所提供的內容,很多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認識和判斷去對照。
縣以下有村、鄉,但村不算一級政權,至少理論上有自治組織的標簽,而鄉政權可以稱為縣政權的派出機構,議事決策的功能都很弱,只有縣級政治,開始初具中國特色,這使它成為觀察的窗口。
該文提到縣政的“家族”性,例如,一個家族可能有5位成員成為縣政的公務員。但我要說的是,這并不是縣政裙帶關系的鼎盛狀態。且不說帝制時代的裙帶關系可能遠超于此,即便從60年來的情況看,鼎盛時期也過去了。吳稼祥先生有一本書,記述他上世紀80年代在中南海做文官的見聞。其中寫到,當時的一位中組部副部長口中的段子:有一個市開常委會,一位常委發言說,“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見。”
在新中國,1949年以前的紅色根據地,縣委書記可能是本地人,但根據地以外的,新政權建立得比較晚的地方,則是由隨革命軍隊進來的干部充任。后一種情況,形成了實際上的“回避制”。這種“回避制”還有比較穩定的延續性。某些地方,直到文革結束,縣委書記還是來自革命老區,雖然其中已經經歷過好幾任。這容易理解,因為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勢力,特別是縣政以上的勢力。
這種天然的回避制,仍然不妨礙裙帶政治的生成。出現“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見”的說法時,已經過了三十多年,“二舅”的籍貫,可能是外省,也可能是本縣。三十多年間,第一代被植入的縣級政權首腦已經漸入老境,但他們的下一代又開始進入政治。那時的社會主要是政治,經濟和其他社會機構微不足道,他們的下一代自然以進入政治為首選。
新中國頭30年的社會還相當封閉,官員的任期沒有形成制度,官家往往就地聯姻,無論是“原籍”家屬之間,還是本地“望族”。這樣,到了文革后期,一個縣城的“政治家族”有十來戶成員的,一點不稀奇。而那時的縣城,大約只有今天的縣城人口的十分之一,政治家族非常顯眼,往往是全縣人民的神話。所以,上面這篇論文中提到的縣城“政治大家族”居然由5戶成員組成也算,其實是非常式微的了。當他們被編織在今天的動輒十來萬人口的縣城里,已經難以形成話題了。
但無論如何,到了文革結束,特別是80年代中期,縣政的裙帶關系已經穩定地形成了。老百姓開始咒罵,黨報大張旗鼓地批評“任人唯親”,連中組部副部長都講“二舅”的段子,可見形成了共識。筆者記得,那時有人非常神往地說過,在漫長的清朝,縣令幾乎都來自外省。
90年代后期,中國開始推行“回避制”。有目共睹的是,在整個新時期,黨的干部制度中執行得最嚴格的就是干部年齡限制和地域限制。到21世紀頭幾年,縣級政權基本上實現了“主要領導異地任職”,所謂主要領導,除了書記縣長,還包括組織部長、公安局長等七八個重要部門的一把手。很顯然,這比清代的回避制度更深入徹底了。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縣政官員更不容易濫權,更不容易腐敗。這同樣是一個有無數事實支持的事實。當每隔幾年(原則上5年,實際上經常中場撤換),一組主要領導突然降臨,如同電腦上的棋盤,一眨眼就占定了,對于本縣公眾來說,則意味著一個新的未知,新的惶恐,因為他們不僅不認識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品行,也不知道他們將如何行政。從情理上講,公眾應該希望街坊王五娃來管理身邊的事務,因為他可能更認同本土,更有所忌憚等等。
從縣政來看,傳統的“家族政治”和官場裙帶已經過去了。何況如《家族政治》一文所說,“計劃生育”使政治大家族的后裔減員,縣政主要領導的獨生子女要不在國外,也在縣外念書,回來做官的可能性很小。其實,縣政真正的希望在于,它是最方便讓屬地人民參與的一級政權。做到了這一點,“家族政治”就不是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