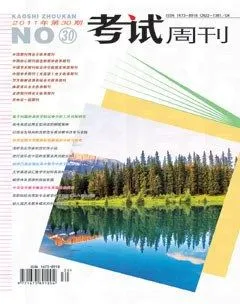論《艱難時世》的語言風格特征
摘 要: 《艱難時世》從表層結構看依然具備了復調小說的主要特征。本文擬從復調理論入手,從個人語言變體、社會方言等方面來分析《艱難時世》的語言風格特征,通過舉例分析來探討《艱難時世》中多言是如何表達意義和互相交叉的。
關鍵詞: 復調論 《艱難時世》 語言風格特征
《艱難時世》是19世紀英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全盛時期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在狄更斯的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對《艱難時世》的評價基本上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它是一部“社會問題小說”,揭露了資本主義的丑陋和罪惡,如辛未艾;另一派則以約翰·羅斯金為代表,認為它是對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宣揚。利維斯說:在狄更斯的所有作品中,《艱難時世》是囊括了其天才之長的一本書;同時還有一個其它作品都沒有的優點:它是一件藝術品。[1]當然,《艱難時世》這本書中也有敗筆,例如:工會的組織者斯拉克布瑞其只不過是中產階級想象中的虛構人物而已。[2]另一個敗筆是女孩西絲的出場,有關她的情況描述得不夠充分。另外,斯梯芬和瑞茄這兩個人物也好得不真實,等等。
這些多是從狄更斯小說的內容、寫作技巧和藝術手法等方面來加以評論。但作品之所以有特色,不僅僅是因為作品所表達的思想,而且也因為他們對語言所作出的與眾不同的選擇。本文將分析《艱難時世》的語言風格特征,探討多言是如何表達意義和互相交叉的。
一
巴赫金認為小說有兩種模式:獨白小說和復調小說。在獨白小說中,只存在作者一個聲音,主人公不能超越、破壞作者獨白式的思考。獨白小說本質上是作者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而復調小說中則存在多種聲音——作者的聲音和主人公的聲音。主人公相對獨立于作者的主觀意識,與作者處在平等的地位上。二者的關系是一種開放性關系,是對話關系。復調世界就是多種聲音平等對話的世界。
從表層結構來看,復調論在《艱難時世》中的運用似乎很成功。小說中被提到的三對沖突的角色(雇傭者與工人、師生、夫妻)在情節中起重要作用。小說中含有許多不同角色和完全不同社會出身及來自不同聯盟的角色群;另外,還提出了許多沖突的觀點。馬戲團演員的與眾不同被大大強調,而這正是對葛擂硬和龐得貝當權的挑戰。但是復調或對話結構不僅限于這些馬戲團藝人,它還存在于許多觀點和矛盾的聲音合奏曲中——斯拉克布瑞其、龐得貝、斯梯芬、郝德豪士、露易莎、西絲等。如果希望弄清楚這些混合聲音,首先有必要詳細展示參與對話結構的多種聲音的語言學和符號學的特點,其次需要按照作者的觀念來理解復調結構,因為多種聲音本身也包含著作者敘述的立場。
二
多言(heteroglossia)一詞源自20世紀30年代巴赫金創造的詞raznorecie(希臘語“不同的語言”)。多言是語言內部的差異或層次,存在著不同變素的相互作用:社會或地域方言;不同職業和社會集團的行話,仿古和創新趨勢的并存等。巴赫金強調:語言沒有中性的詞或中性語調,語言本身不是一種聲音。對巴赫金來說,小說這一體裁的魅力在于它樂意接納多言為結構原則,不同社會團體的異音及各種體裁,敘述者和不同角色的聲音都能得到表現。巴赫金在關于語言風格變體的著述中,提出了“混合”(hybridization)這一概念。它指一個話語片斷或一個句子摻雜著兩種不同的聲音或意識。例如:敘述者與人物或社會群體的混合。但是這種混合沒有形式上的語言界限。狄更斯通過使用混合結構把一種集體話語與敘述者的聲音摻雜在一起,有效地突出了當時社會上的虛偽性。
個人語言特點是指個別說話者使用的語言品種,包括具有發音、語法和詞匯方面的特點。個人語言特點是有一定的語言文化背景的。一般說來,它是每個人自己所特有的更為持久的不變的語言特征。語言學家通過研究個人語言特征來描述語言的一般特性,通常有兩種方法。第一:難以識別的作者風格被認為是個人語言。第二:小說中個人語言的前景化會產生漫畫效果。雖然漫畫藝術是一個具體化的過程,但它是用來陳述的一種手段。《艱難時世》中有兩個比較鮮明的例子:工會組織者斯拉克布瑞其和馬戲團頭頭史里銳。他們每人都有一個相對獨特的但又自相一貫的言語模式。
斯拉克布瑞其用一種激烈的圣經的辭令來表現自己:“啊,朋友們,焦煤鎮受踐踏的紡織工人們!啊,朋友們,同胞們,在專制淫威的壓迫下的奴隸們!啊,朋友們,難友們,工友們,兄弟們!我告訴你們,時間已經到來,我們必須互相團結,成為一股集中的、聯合的力量,把那些搶劫我們家庭,榨取我們血汗,剝削我們雙手勞動、剝削我們精力,剝奪上帝所創在的人類的光榮權利,剝奪神圣的、永恒的同胞特權來自肥自飽的壓迫者,打得粉身碎骨吧!”
狄更斯并沒有刻意地表現任何社會角色,他是為了詮釋斯拉客布瑞其自創了一種象征性語言,但是這種語言并沒有準確地表達什么意義,只不過是依附于教堂布道的講壇、議院或政治、公共集會時的夸夸其談而已。從傳統意義上講,這種語言含有空洞、不真實之意。斯拉客布瑞其的現身對當時復雜的、道德的兩難境地也是一個不和諧元素。狄更斯根據他所說的話及他的外表特征對他直接作出評價說:“他不是那么誠實,他不是那么有大丈夫氣概,他不是那么和善,他以奸猾代替了他們的率真,他以激情代替了他們的實事求是和可靠的辨識力。”[3]
史里銳是小說中第二個語言怪誕的形象。而他的語言卻主要是夸大的辭令,他的話語都淹沒在“摻水的白蘭地”里了,他的聲音像從一個“破風箱”里抽出來的風,有“咝”聲的輔音常發不出來,所有的s,ts,z等都被發成th:
Tho be it,my dear.(You thee how it ith,Thquire!)Farewell,Thethilia!My latht wordth to you ith thith.Thtick to the termth of your engagement,be obedient and well off,you come upon any horthe.riding ever,don’t be hard upon it,don’t be croth with it,give it a Bethspeak if you can,and think you might do wurth.
在小說情節和主體結構中,史里銳的作用遠非一個滑稽的酒鬼。在馬戲團演員與葛擂硬和龐得貝對抗時,他是以馬戲團領導身份首次亮相的,并且很成功地把西絲委托給葛擂硬照顧;最后,他又成功地把葛擂硬犯罪的兒子送到國外使之免于被捕。然后,他又幾乎一字不差地重復了前面引述的那句話:“盡量利用我們,盡量不要糟蹋我們。”小說中史里銳的介入與葛擂硬的命運有著直接的聯系,并且他的人生哲理與葛擂硬的功利主義教育理論恰好相反,他的“馬戲團”代表著一種幻想。狄更斯讓史里銳的語言中充滿了完全古怪的語音變異,所以讀者不得不費勁地去理解他那些古怪的、與生俱來又前后不完全一致的話語,這些語音變異把一些日常用語變成暫時不能識別的拼寫形式,如tho,nutht。這些晦澀語言不能保證史里銳所說的話都是有意義的。事實上,狄更斯把這些晦澀語言擺到讀者的面前就表明史里銳的話本應該被聽,他被專門用來反對葛擂硬主義的一個重要的聲音。
史里銳言語中還有另外的特點被用來進一步區分他與斯拉客布瑞其的話語。除了其個人言語特點外,還有一些暗指社會方言的標志語。狄更斯用史里銳的語言暗示著工人階級的詞法、詞匯,再加上一些暗示著與中產階級語言不同的拼寫形式,還有俚語和詛咒等,這些特征把史里銳與工人階級的利益聯系在一起,并且與馬戲團里的手足之情聯系起來。這些聯系一方面為他建立了一個社會關系體系;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與以葛擂硬為代表的功利主義哲學相對立的基礎。
三
方言指與不同群體的語言使用者相聯系的語言變體。在早期文學作品中區域性變體經常用于對白中以求戲劇或社會效果,方言尤其為社會地位低的角色所廣泛使用。在小說中方言被用于直接引語和對話,作為標示角色籍貫的模擬手段,也作為人物塑造的手段。而社會方言是仿照語言學中的方言與個人語言而創造出來的術語,指某一特殊社會集團或階層所獨有的語言變體。
《艱難時世》包含了許多截然不同的言語風格,總的說來,是社會方言而非個人方言。韓禮德提出語域可描述社會組織的特性,也可闡釋他們不同的價值觀。不妨看一下郝徳豪士與斯梯芬截然不同的言語風格。前者在剛出場時被描繪成一個懶洋洋的、漫不經心的虛度光陰者,說話有氣無力,沒精打采,所說話語斷斷續續不連貫。然而,當他確信自己對露易莎有好感時,卻使用了精雕細琢的句法來表達:
龐得貝太太,我雖粗俗不文,老于世故,但老實地跟你說,我對你剛才告訴我的話發生了莫大興趣。我絕不會苛責你的弟弟。你對于他的錯誤所表示的那種賢明體諒,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我也有同感。……這種不良的教養,使他不能應付他活動其中的社會,長久以來他就被迫走極端——我們毋庸懷疑,驅使他走極端的人的本意很好——但是他沖出來了以后,跑到相反的極端去。……
再有,狄更斯煞費苦心地讓斯梯芬的語言成為他那一階層的代表。許多典型特征使他的語言成為他那一階級語言的代表,其宗教化、未受過教育、口語化特征鮮明。這首先體現在與瑞茄的親密對話中,這段對話表明他的話語風格是有普遍性的而不是特殊的。與史里銳相比,斯梯芬的話語中不合常規的拼寫要少得多。狄更斯用基本的拼寫、詞匯、詞法套路來簡單地陳述他的語言特點。韓禮德[4]認為口語和書面語有不同的信息結構,因此有各自不同的句法結構模式。不同于句子較長、句法精致復雜、多從屬結構的書面語,口語只是由一系列短的語塊或者信息單位組成,這些信息單位又被聲音中的語調分割成一個個更小的語塊。
《艱難時世》中,斯梯芬兩次來到龐得貝的家中,并且每次都與龐得貝發生激烈爭論。斯梯芬開始安靜而有禮貌地回答,所用語言帶有濃重的地方口音且語句較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你要我來做什么?”
“請原諒我,我沒什么可說的。”
當被要求說明他將怎樣解決紡織工業一團糟的狀況時,斯梯芬用了五個長句子來回答;這五個句子的長度遠遠超出了這個角色的特征,違反了他與瑞茄對話的常態。下面是其中的第三句話:
“看看這市鎮——事實上,是非常富庶的——再看看生長在這兒的許許多多工人,他們從搖籃到墳墓,總是靠紡織和梳毛求得生存。”
斯梯芬在龐得貝的挑釁之下說出了工人反對廠主的觀點,而這一觀點與狄更斯本人的人道主義觀點相吻合。斯梯芬不能說出怎樣改造現在的狀況,但他知道哪些方法是絕對不行的,如強硬手段、征服和戰勝的辦法、缺乏人性等。當斯梯芬陳述這些觀點時,他用了一系列平行的、加長的句子,他的語言整體結構變成了公共演講時常用的排比修辭法。下面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不想法子去接近一般的人,不用慈悲心、耐心去對待他們,鼓舞他們,而他們呢,雖然困難卻是相親相愛,只要有一個人陷入困難之中,他們就會友愛地把自己需要的東西分給他——我想這位紳士雖然走遍天下,也不會見過有誰賽過他們——不以這種精神去接近人,也是絕對不行的,除非太陽會變成冰。……等到整個大鬧起來的時候,卻去責備他們跟你們打交道時,缺乏那種人性——東家,除非上帝把它創造的世界重新改造過來,這樣是絕對不行的。”
四
本文列舉了《艱難時世》中幾個重要人物的語言實例,以及這些語言風格所具有的社會價值特點。它們和其它在此沒有列舉的聲音共同構成了一副由各種語音匯聚而成的“文本圖像”。總之,這些語言所表達的意義好似萬花筒,紛繁無序、參差不齊。史里銳和葛擂硬是狹路相逢,所以,他們語言的“幻想”與“事實”特征在這里發生了直接碰撞;葛擂硬和龐得貝表達出功利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斯梯芬和瑞茄代表忠誠和愛;馬戲團里的人們體現和表達出淳樸自然和歡快。這些通過相互對照的多種語言風格表達出來的不同觀點處于經常互相沖突的狀態之中,因此賦予了作品一種極具意義的動態結構。
參考文獻:
[1]利維斯,F.R.偉大的傳統[M].北京:三聯書店,2002:377.
[2]羅經國.狄更斯評論集[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90.
[3]全增蝦,胡文淑譯.艱難時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155.
[4]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r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1985.
基金項目:本文是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10CWXZ06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