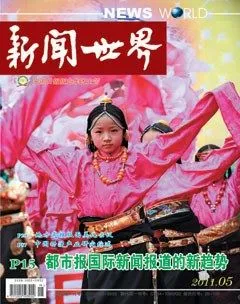人文關懷與商業利益的博弈
【摘要】故事是電視節目的一個重要組成元素。在敘述者干預和敘述視角的選擇上,電視節目中的故事體現出了傳遞人生經驗和傳播價值觀念的倫理傾向。從懸念的設置和“奇觀化”的敘事來看,電視節目中的故事又是為了追求商業利益而存在。
【關鍵詞】故事 電視節目 倫理傾向 敘事技巧 敘事策略
羅伯特·麥基在其著作《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的開篇就說道:“人類對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饜足的”。確實如此,從人類遠古時期口口相傳的神話到印刷時代市民小說的流行,再到電子時代影視劇的熱播,故事在傳遞人生經驗、提供娛樂消遣等方面彰顯了其獨特的魅力和功能。麥基總結道:“我們對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類對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層需要。”①故事的魅力也就在于此,人可以從故事中捕捉人生經驗、體驗心理認同。
從歷史來看,故事的傳播經歷了口語、印刷、電子等幾個載體的轉換。在當今社會,電視無疑已成為最普遍的故事傳播載體。相對于語言文字,由于電視聲像一體化的特征使得它講述故事時在敘述方法、接受形式等方面體現出了與語言文字傳播載體的不同特征。語言文字作為一種抽象的傳播載體,在講述故事時采取的敘述方法常常是多重視角的,傳播時是由中心向邊緣擴散的單向模式。而電視作為一種形象的傳播載體,在講述故事時所采用的敘述方法常常是以內視角為主,力圖通過這種方式拉近故事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在傳播時是雙向互動的模式。并且,在接受形式上,語言文字因其抽象性而使受眾在接受時不得不調用理性思維去思考,在受眾和故事之間容易形成某種間離效果。電視因其聲像一體化的形象性,加上其相對開放的接受環境,受眾在接受時常常調用的是感性思維去感受。因此,電視更加傾向于在倫理層面進行敘事,通過內視角的敘事,博得觀眾對故事中某個(些)主人公的同情,來達到倫理效果。
近年來,在電視熒屏上形成了一股講故事的熱潮,新聞故事化、紀錄片故事化、各種講故事的電視欄目應運而生。由于電視的商業屬性,使得它與用語言文字講故事的方法有著諸多不同。本文擬從敘事技巧、敘事策略、敘事動機等方面來考察在電視節目中故事的存在狀態(這里所說的電視節目是指摒除了電視劇這種藝術形式外的電視節目)。英國學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了媒介的四種傳播模式:專制式,即單純傳達統治集團的各種指令;家長式,即力求對民眾進行保護和指引;商業式,即提供相當自由程度的文化產業環境,但排除那些回報率低的商品;民主式,即提供相當自由程度的文化產業環境,同時又與資本相隔離。②綜觀中國的講故事類電視節目,絕大部分節目既有家長式的特征,同時也具備了商業式的特點。筆者選擇了兩檔具有代表性的電視節目作為考察對象:中央十套的《講述》和江蘇衛視的《人間》。
故事敘事中的
倫理傾向與價值關懷
“敘事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交流活動,它指的是信息發送者將信息傳達給信息接收者這樣一個過程。”③從這個層次上來說,在人類社會中敘事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人們可以通過敘事來理解世界,也可以通過敘事來“講述”世界。在當今的電視熒屏上,有很多類似于《講述》和《人間》的電視節目每天在給觀眾講故事,通過講故事向觀眾展示這個多姿多彩的世界,并通過講故事與觀眾在意識形態上形成同構。既然說到講故事,必然會涉及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故事,一個是講3qWJMxgb5UQ5X7LE9TTOLOXw0Ev50YusnSm0SjJrNfs=,即用什么樣的方式將故事呈現在觀眾面前。通過對兩檔節目的分析,筆者發現在絕大部分的故事中均蘊含了四個敘事功能所共同構建的敘事模式,即:作為普通個體的某人遭遇重大變故或某個家庭遭遇重大矛盾——記者或相關部門參與調查或調解——個體受到幫助或矛盾得到解決——對觀眾形成倫理道德上的詢喚。例如,在2010年8月11日《人間》播出的題為《家里來了免費保姆》的節目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山東省臨清市的張玉華十年如一日地照顧在一場醫療事故中成為植物人的妻子,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妻子終于蘇醒過來,但生活仍然不能自理。某天妻子的姑姑去看望侄女時發現家里多了一個女人。據張玉華介紹這是他的一個朋友,過來幫助他照顧妻子。姑姑不相信他所說的話,認為在張玉華和那個女人之間存在著曖昧關系,因此要把那個女人趕走。在走還是留這個問題上張玉華和姑姑之間產生了重大沖突。在主持人的參與下,那個女人說出了事情的真相,原來她曾經受過張玉華的無私幫助,并且為張玉華對妻子的深情所打動,所以甘愿免費幫助張玉華照顧他的妻子。節目在最后出現了高潮:張玉華帶著妻子去看自己的演唱會,并在演唱會上向妻子表明了自己的心跡,表示自己依然愛她,會對她不離不棄。觀眾此刻被張玉華對妻子的深情打動,并對張玉華產生深深的同情。節目也就是這樣完成了在倫理道德上對觀眾的詢喚,即人間自有真情在,要用一顆真誠、包容的心去對待別人。可以看到,這期節目的整個敘事流程正如前面所說的由四個敘事功能構成了一個封閉的敘事模式。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不僅僅在故事內容中存在著對觀眾的意識形態形成詢喚的倫理傾向,在電視節目中故事的敘述方式、講述技巧同樣也包含了特定的倫理傾向。在電視節目中,敘述者干預即是大影像師慣用的引導觀眾倫理傾向的一種敘述技巧。敘述者干預常常通過對故事中的人物、事件、故事本身來進行評論,以期引起受眾對其價值取向的認同,“在很多情況下,敘述者對人物與事件作出評價性評論是試圖使隱含讀者接受其所作的判斷與評價,按照他或她所給定的意義去對事件和人物加以理解,以使隱含作者與敘事接受者在價值判斷上保持一致。”④通過對《講述》和《人間》的考察,我們發現解說詞往往承擔了敘述者干預的功能。在此類電視節目中,解說詞往往是構成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多情況下故事的起源、發展以及結束常常依靠解說詞來推動。但是,當解說詞超越了其敘事功能,對故事中的人物和人物的行為進行評述時,我們即認為大影像師通過解說詞在建構其價值判斷和倫理傾向。例如,在2010年8月13日《講述》播出了一期節目《驚魂不眠夜》,講述了在暴風雨襲擊的福建省建陽市,因為大水圍困,一位待產的產婦不得不由媽媽在家為其接生。但由于方法不對,在產婦生下小孩后,大人和孩子都生命垂危。建陽市消防隊接到報警后,派五名隊員前去解救。在解救的過程中他們遇到了重重困難,這時解說詞說道:“拼了命,他們也要把這個孩子救出去。”從表面看,解說詞在這里出現非常正常,因為當時情況非常危急,消防隊員也想了很多辦法營救嬰兒。但關鍵點在“拼了命”這句話上,這句話在這里并沒有什么敘事功能,也不是由故事中的人物發出的聲音,而是大影像師在這里跳出來對當時戰士們的心情進行了評論。從這句帶有傾向性的評論中,觀眾可以感受到消防隊員在危險境地之中救人的急切心態,從而對他們產生敬意。當然,在節目中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大影像師也就是通過敘述者干預這種方式完成了對觀眾的倫理傾向的引導和意識形態的建構。
在敘事過程中,大影像師除了采用敘述者干預的方式之外,視角的選擇也是其引導觀眾的倫理傾向的一個重要方式。“敘事視角的技巧是怎樣控制讀者對人物的同情的呢?……(1)當我們對他人的內心生活、動機、恐懼等有很多了解時,就更能同情他們;(2)當我們發現一些人由于不能像我們一樣進入某些人物的內心世界而對他們作出嚴厲的或者是錯誤的判斷時,我們就會對這些被誤解的人物產生同情。”⑤馬克·柯里在這里所說的同情也就是說受眾對于故事中人物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和倫理傾向的認同。
在視角的選擇上,內視角無疑是使得受眾對故事中的人物給予更多“同情”的最佳方式之一。所謂的“內視角”是指敘述者只說出某個特定人物所知道的情況。反映在電視節目中,最直觀有效的方式就是“訪談”,也就是讓當事人親口說出某個事件的過程或對某個事件的評價。在訪談的過程中,一方面使得觀眾對人物的內心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獲得了對某個事件的知情權,由于訪談的對象大多也是普通人,因此觀眾在獲得知情權的同時也完成了自身的主體性建構;另一方面,由于訪談是在記者或主持人設定的框架中進行的,再加上電視節目的后期剪輯,一個符合大影像師的價值觀與倫理傾向的完整敘事結構即被建立了起來。此外,由于內視角的選擇與觀眾形成了同構,使得觀眾對于節目著重展示的某個人物更易于“被同情”,這并不是說“被同情”的某個人物在道德上比其他的人更具有優勢,而是因為觀眾對于“被同情”的人物在內心世界、行為方式上有了更多的了解。在2010年8月11日《講述》播出的節目《錯愛·真愛》中講述了一個嬰兒被抱錯了的故事。浙江省溫州市的白植偉的妻子和黃乾武的妻子在同一時間同一間醫院生出了嬰兒,由于護士的疏忽將兩家的嬰兒抱錯,在時隔4年之后,白植偉找到黃家,要求將孩子調換過來。從倫理道德上來講,白植偉和黃乾武的家庭同為受害者,應該獲得人們的等量同情。但是在節目中,由于將內視角敘述的權利大量給予黃的妻子,白植偉的話語權大量被剝奪。觀眾在觀看的時候會產生這樣的判斷:黃的妻子是一個重感情、有愛心的人,但白植偉是一個冷漠的、為達到調換孩子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觀眾之所以會對兩個本來在世俗道德中應給予等量同情的人產生如此大差別的判斷,原因就在于大影像師敘述視角的選擇。當然,從多期節目來看,每個故事多以大團圓的方式結束,這使得觀眾在某種程度上更加認可隱含在故事中大影像師的價值觀和倫理傾向。
故事敘事中的商業策略
電視的商業屬性要求電視節目在講述故事時不得不采取有別于語言文字時代講故事的敘事策略。在市場體制之下,電視臺或電視節目要想贏利,必須要吸引足夠多的廣告主,而廣告主判斷一個節目優劣的重要指標之一便是收視率。收視率乃萬惡之源這句話雖然有點過,但也顯示出了收視率之于電視節目的重要性。為了留住更多的觀眾,電視節目在敘事策略上挖空心思,其中最常見的策略是對懸念的應用。對于普通觀眾來說,獵奇探秘心理是其收視接受心理中最為普遍的一種。因此,在電視節目中編導便利用懸念做足功夫,吸引觀眾對其節目的關注。懸念的設置可分故事中和故事外。故事中懸念的設置編導常常用一個噱頭,對觀眾產生引導性誤讀,在真相大白的那一刻,觀眾獲得了獵奇探秘后的滿足感和放松感。如在前面提到的節目《家里來了免費保姆》中,開始部分編導的敘事安排使得觀眾產生這樣一種錯覺:張玉華和保姆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曖昧關系。而這又與當下社會普遍關心的“小三”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吸引了觀眾繼續看下去。雖然這種手法的運用流于庸俗,但由于其達到了良好的懸念效果,于是此種手法成了編導屢試不爽的不二法門。故事之外的懸念設置常常通過解說詞來實現。在節目開始之前或節目之中,解說詞常常用一些扣人心弦的詞匯、緊張的設問句式來營造一種氛圍。在這種氛圍中充滿了懸念,迫使觀眾不得不追隨編導的腳步將目光投向故事。且看在《驚魂不眠夜》中節目是如何開始的:“大水圍城,女兒突然臨產,母親親自揮動剪刀為女兒接生;產婦出血,嬰兒告急,驚魂不眠夜里又會發生什么?”在這寥寥數語中,編導既制造了緊急的氣氛——大水圍城,女兒臨產;又創造了懸念——產婦出血,嬰兒告急。事情如何解決的?觀眾自然而然會如此發問。而事情的解決過程只能在節目中找到答案。由此可見,在電子時代的電視節目中,懸念的設置已逐漸成為電視節目爭奪觀眾、爭奪收視率的一個工具。
在敘事策略的選擇上,“奇觀化”敘事是電視節目在講故事時的另一個常用的策略。在美國學者道格拉斯·凱爾納看來,媒體奇觀是指“那些能夠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并將當代社會中的沖突和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它包括媒體制造的各種豪華場面、體育比賽、政治事件。”⑥在當今電視時代,媒體不僅可以制造各種豪華場面、體育比賽和政治事件,普通人的生活通過媒體制造之后,同樣會以“奇觀”的方式呈現于觀眾面前。如前所述,獵奇探秘心理是人類普遍心理狀態之一。編導利用人類的這種心理,通過各種手段為觀眾奉上了一個又一個的人間“奇觀”。通過對《講述》和《人間》的考察,我們發現幾乎每期節目的標題都向觀眾展現了似乎是來自同觀眾身份相同但又有很大差別的普通人的故事。如《危情100米》(《講述》,2010年8月8日)、《拯救花季少女》(《講述》,2010年8月9日)、《莫名“怪火”之謎》(《人間》,2010年7月28日)、《離奇失蹤的一家七口》(《人間》,2010年8月2日)等等。從這些標題我們很容易便會看出其制造“奇觀化”的意圖。同時,在內容的選擇上,節目也往往選擇一些離奇的、與普通人生活狀態差別極大的事件作為故事講述的對象。如在2010年8月10日《講述》播出了一期題為《少女的煩惱》的節目,節目中講了一位來自河南新蔡的女孩的故事。受父親遺傳影響,處在花季的少女胳膊上、腿上、臉上等處都長出了厚厚的黑毛,這使得女孩極度自卑,甚至一度產生了自殺的念頭。聞名全國的“毛孩”于震寰聽說以后,專程去開導了她。在于震寰和記者的努力下,醫院為女孩做了手術。女孩終于走出了心理陰影,開始了正常人的生活。在鏡頭里,女孩胳膊上、腿上厚厚的毛發不斷被展示,觀眾在看這期節目時獲得了某種窺隱的快感,同時也會不由自主的跟隨編導的節奏安排為女孩的命運或擔心或歡喜。當然,這都是表層,電視節目選擇類似于這些有別于普通觀眾生活的事件作為講述內容的目的還是在于吸引觀眾的注意力,爭奪收視率。
人文關懷與商業利益的博弈?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市場體制之下,電視節目中的故事正處于兩難的境地:力圖傳遞人生經驗與價值和服從商業利益之間的矛盾。“今天我們之所以批評影視商品的極端商品化現象,不僅是因為這種現象不利于當代人文精神的生成,并且,更不利于影視產品與市場之間良性關系的形成。”⑦如何在故事的原初意義和商業價值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這不僅僅是編導、制片人、電視節目的責任,也是學界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①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14
②尼克·史蒂文森 著,王文斌 譯:《認識媒介文化——社會理論與大眾傳播》,商務印書館,2001
③④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6、77
⑤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