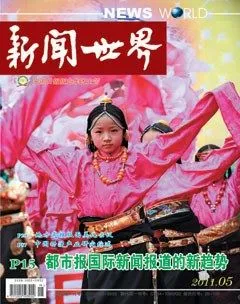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看鄒韜奮及《生活》周刊
【摘要】鄒韜奮從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編到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政府查封,《生活》周刊一直是守望社會,服務大眾的輿論陣地。懷著對職業理想的追求,從社會責任意識到大眾的輿論陣地,從服務精神到受眾自由,從獨立的報格到社會角色的確立,鄒韜奮及《生活》周刊演繹著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公共服務者角色。
【關鍵詞】鄒韜奮 《生活》周刊 新聞專業主義
一、職業理想的追求——新聞職業精神的萌芽
《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11日創刊。作為一份指導職業教育的機關刊物,最初的《生活》周刊主要是贈送給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社員和教育機關,社會影響不大。1926年10月主編王志莘離開了《生活》周刊,鄒韜奮接任刊物的主編,從此《生活》周刊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大眾的視野。
《生活》周刊初創時的條件非常艱苦,三張辦公桌就把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塞得滿滿的,幾乎沒有轉身之地。連鄒韜奮在內一共只有兩個半職員從事具體工作,除了鄒韜奮外就是負責經營與廣告的徐伯昕和兼職會計孫夢旦。同時,因為稿費較低,約稿存在困難。于是每期的稿件大半都是鄒韜奮自己撰寫,他把搜集來的各種材料分類排列,編寫成文章,以各種不同的筆名發表。
條件雖然艱苦,《生活》周刊對于鄒韜奮而言更多是對職業理想的追求,而并非謀生的手段。后來雖然《生活》周刊的發行量增加了,但鄒韜奮的工資甚至比接辦《生活》周刊時還減少了幾十元。刊物的盈余都用在發展事業上。比如給刊物增加頁碼,增加畫頁,發行增刊等等。即使在物價上漲,紙價上升,刊物的成本大大提高的情況下,刊物也是盡量不提價,而是通過增加廣告的收入來彌補虧空。后來由于國民黨政府禁郵、禁運,刊物的經濟收入受到很大的影響,鄒韜奮寧可自己帶頭每月減薪50元,也不提高刊物的售價。
鄒韜奮在《<生活日報>的創辦經過和發展計劃》一文中說到:“我在民國十五年至二十二年間,在上海編輯《生活》周刊,頗得國內外讀者的嘉許,在七年中間,銷數從二三千份增加到十五萬份。我生平并無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資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報業大王。我只有一個理想,就是要創辦一種為大眾所愛讀,為大眾做口舌的刊物。”①
對職業理想的追求,對社會的責任意識和強調服務大眾的自覺態度正是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內化,而對職業理想的追求是鄒韜奮新聞職業精神的萌芽。
二、專業主義精神的公共服務者——新聞專業主義的踐行
鄒韜奮在《我們的立場》中表明了《生活》周刊的立場:“至第四年起,經濟與管理方面均完全獨立,幸得創辦者之絕對信任,記者乃得以公正獨立的精神,獨來獨往的態度,不受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的牽制……依最近的趨勢,材料內容尤以時事為中心,希望用新聞學的眼光,為中國造成一種言論公正評述精當的周刊……”。②
1、從社會責任意識到大眾的輿論陣地
鄒韜奮接辦《生活》周刊后,對刊物的內容進行了革新。根據讀者和社會需要,不斷改變編輯方針。開始時,由于《生活》周刊的主要受眾是青年,因此,鄒韜奮偏重于發表一些職業教育和青年修養方面的文章。但是隨著社會形勢的轉變和人們思想發展的需要,《生活》周刊開始關注并討論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后,他把《生活》周刊的重點轉移到對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上來。
1931年5月,日本軍閥制造了槍擊中國農民的“萬寶山事件”和屠殺旅韓華僑的事件。鄒韜奮獲悉后在《生活》周刊上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和日本必然侵略中國的陰謀。他在《全民族的生死關頭》中疾呼:“萬寶山及朝鮮排華慘案,實為日本積極侵略中國的一部分表現……”③“九一八”事變發生后,鄒韜奮立即在9月26日的《生活》周刊上作了報道,并一口氣寫了《應徹底明了國難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眾實力》《一致的嚴厲監督》《對全國學生貢獻的一點意見》等四篇“小言論”,認為:“全國同胞對此國難,人人應視為與己身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斗。”④另外,鄒韜奮還刊登了“九一八”發生后來自沈陽、長春等地的系列報道,揭露了日本軍閥在東北燒殺搶掠的滔天罪行。針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生活》周刊接連發表了《寧死不屈的保護國權》《戰與不戰的問題》等言論。在抗日救亡運動中,上海的學生罷課舉行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到南京請愿。蔣介石卻聲稱:“學生之職在于求學”。某些大學教授發表《告學生書》,要求學生致力于救國之知識準備等等。對此,鄒韜奮發表了《誰都沒有責備請愿學生的資格》一文,他說:“記者承認‘學生之職,在于求學’,但軍人不能保衛國土,反而奉送國土,官吏不能整頓國政,反而腐敗國政,使青年不能得到可以‘安心求學’的環境,這是誰的責任?”⑤1990年11月,著名記者趙浩生在回憶鄒韜奮對他的影響時說:“每期《生活》周刊在學校飯廳門前的地攤上出現時,同學們都一改擁進飯廳去占座搶饅頭的活動,而如渴似饑的搶購《生活》周刊。……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韜奮的事實評論和連載的游記。……當時每一個人都感到《生活》是我們的生活,韜奮是我們的導師。”⑥
“我們不愿唱高調,也不愿隨波逐流,我們只根據理性,根據正義,根據合于現代的正確思潮,常站在社會的前一步,引著社會向著進步的路上走。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思想是與社會進步時代進步而俱進。”(鄒韜奮:《我們的立場》)⑦鄒韜奮及《生活》周刊緊緊和時代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把社會形勢的變動及時傳遞給受眾。
2、從服務精神到受眾自由
鄒韜奮在《生活》周刊上開辟了談話欄目和通信欄目,設立了《讀者信箱》專欄,從而加強同廣大讀者的聯系,同時也是了解社會現實生活動態的重要渠道。隨著讀者的增多,讀者來信也日益增多,從每天的幾十封逐漸增加到幾百封,有時甚至一天收到一千多封。《生活》周刊把來信的原稿保存下來,把來信者的姓名和地址編入卡片以便聯系。來信的內容也按問題的性質分類歸檔,用于收集材料,發現問題,了解讀者和社會。讀者來信所反映的許多情況正是社會實際情形的寫真。通過與廣大受眾的聯系,記者可以對社會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鄒韜奮在《生活》周刊上通過《讀者信箱》等窗口建立了與廣大受眾的溝通渠道,所體現的服務精神實質上是新聞專業主義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受眾自由。
3、從獨立的報格到社會角色的確立
“本刊是沒有黨派關系的,這并不含有輕視什么黨派的意思,不過直述本刊并沒有和任何黨派發生關系的一件事實。我們是立于現代中國的一個平民地位,對于能愛護中國民族而肯赤心忠誠為中國民族謀幸福者,我們都抱著熱誠贊助的態度”(鄒韜奮:《我們的立場》),1930年)⑧鄒韜奮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尤其是作為《生活》周刊的主編,十分注重報刊和報人的獨立品格,面對各種壓力,甚至強權勢力的威脅和利誘,《生活》周刊都沒有妥協,體現出新聞職業主義精神。
王伯群知道《生活》周刊在調查自己后,便找人去當說客,并妄圖以巨款作為鄒韜奮的封口費。不管他們把這筆錢說成是給《生活》周刊的補助經費還是作為投資《生活》周刊的股本,都被鄒韜奮拒絕了。第二天,鄒韜奮便在《編者附言》中曝光了記者對王伯群的調查,并發表言論:“在做賊心虛而自己喪失人格者,誠有以為只須出幾個臭錢,便可無人不入其彀中,以為天下都是要錢不要臉的沒有骨氣的人,但是錢的效用亦有時而窮。……”
“九一八”事變后,《生活》周刊的重點轉移到對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上,并始終堅持抗日救國、反對妥協。1931年,《生活》周刊的發行量突破10萬份,到1932年底達到了15萬5千份。不管是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城市還是在內地鄉村僻壤以及遠在海外的華僑所在地,都可以見到《生活》周刊。1932年1月,蔣介石命胡宗南以高級軍官的身份把鄒韜奮找去,要《生活》周刊改變立場,擁護國民黨政府。鄒韜奮沒有妥協,他始終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站在一個專業的新聞記者的立場上,承擔起對社會應有的責任。國民黨政府開始施壓于黃炎培等職教社的領導,要求他們出面干涉。1932年底,蔣介石警告黃炎培,如果《生活》周刊不改變態度,就會被查封。為了不使黃炎培為難,鄒韜奮決定《生活》周刊與中華職業教育社脫離關系,成為一個獨立的刊物。他在報上刊登了《生活》周刊脫離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啟事。在保護職教社的同時,更保全了《生活》周刊的獨立,不向強權妥協。1933年12月8日,《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政府查封。
三、《生活》周刊的經營模式是其新聞職業主義道路的保障
《生活》周刊之所以能夠保持獨立,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刊物的經營模式使它不必依附于政黨。鄒韜奮主持《生活》周刊主要負責編輯,他擔當的是“西方教會”的角色,服從于新聞職業理念;而主管經營和廣告的徐伯昕則擔當的是“國家”角色,負責刊物的經濟來源。“國家”負責市場和賺錢,但不會對“教會”施加影響,干預其新聞職業工作,降低刊物的品味。一方面,巨大的發行量和廣告收入成為刊物主要的經濟來源,任何政黨都抓不住《生活》周刊的命脈;另一方面,在當時社會時局處于動蕩不安的情況下,新聞理念與市場理念的重合,《生活》周刊及時傳遞信息,成為輿論陣地是大眾的需要,巨大發行量可以使其在廣告面前始終保持自己的品味,從而化解了來自市場的壓力。《生活》周刊的經營模式實質上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在各種力量的交鋒中,《生活》周刊始終把社會及公眾的利益最大化,擔當著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公共服務者的社會角色。國民黨政府曾經想打擊《生活》周刊,但是在調查后發現《生活》周刊確有近20萬冊的銷路,并沒有受到任何黨派的津貼,因此要想封住《生活》周刊的口,除了查封刊物別無選擇。■
參考文獻
①②⑦⑧穆新,《韜奮新聞工作文集》[C].新華出版社,1985:117、76
③④⑤⑥陳揮,《韜奮傳》[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6、98、84
(作者:均為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08級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