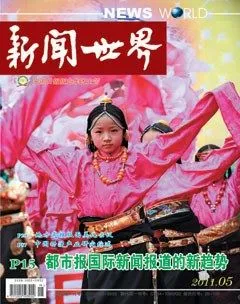淺談近代報刊公共領域的形成
【摘要】近代報刊的誕生,為建構報刊公共領域提供了可能性。鄒韜奮主編《生活》周刊期間,通過設立“信箱”欄目,就社會民眾所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實現了近代報刊建構公共領域的嘗試。
【關鍵詞】《生活》周刊 鄒韜奮 公共領域
按照哈貝馬斯的提法,公共領域的形成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要有獨立于政治權力之外的公共空間;二是參與者能獨立地、理性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三是討論的話題具有公共性。本文通過梳理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的讀者“信箱”欄目所形成的報刊公共領域,以試圖總結建構報刊公共領域的經驗。
中國近代報刊的出現有別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誕生之初,便與各政黨及利益集團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無論是傳教士的辦報活動,還是維新派及革命派的報紙,中國近代報刊很多時候體現的都是一己之私,而非社會公義。各派報紙以“大公無私”的姿態討論中國社會問題,但最后大多走不出謀私利而舍公理的窠臼。精英治國的傳統更是剝奪了社會公眾的話語權,形成“大政府小社會”的景象。表達意見的渠道掌握在權貴及士大夫階層手中,普通民眾少有參與公共話題討論的機會,報刊這一新興的信息溝通的工具也多被黨派所利用并為之服務,黨同伐異的現象很普遍。報紙未能成為社會公器,報刊公共領域的形成也就無從談起。
報刊公共領域的形成,離不開公眾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參與意識的萌發。近代中國的救亡運動與社會轉型,一直是采取從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的。在經歷了對上層政治制度變革的一次次失敗之后,士大夫階層與新型知識分子將注意力集中到了改造民眾的思想上。在這種背景下,新文化運動爆發,隨著民智得以啟發,中國公共領域的形成具備了條件。1926年10月,31歲的鄒韜奮以職教社編輯股主任的身份接任《生活》周刊主編的職位。《生活》周刊地處上海,其目標受眾群體是當時上海有正當職業的“中產階層”,包括律師、醫生、會計師、工程師及工匠學徒等各個行當。這些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或專業技能,有穩定的收入,關心時事。當這些人參與到報刊上社會問題的討論中時,報刊就能為社會主流群體發聲,引起廣泛的共鳴,從而為公共領域的形成創造條件和提供可能性。
鄒韜奮在主持《生活》周刊編輯工作時,一直力求保持《生活》周刊的獨立性。在經濟上,《生活》周刊不接受任何黨派及利益集團的資助,不代表任何黨派及利益集團發言。這一點在中國近代報刊中是難能可貴的,即便是剛開始以宣傳民主科學思想為宗旨,秉持平等開放態度的《新青年》雜志,也在其發展過程中漸漸失去和讀者的商榷態度,而以一黨的立場辦刊,破壞了公共領域建構所必須的平等參與的條件。而《生活》周刊從創刊至1933年停刊,都始終以平等的態度與讀者保持交流,始終保持其立場的公正性。鄒韜奮曾提出“報格”的概念,“記者所始終認為絕對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也就是所謂的報格”,并表明,“倘須屈伏于干涉言論的附帶條件,無論出于何種方式,記者為自己人格計,為本刊報格計,都抱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1927年,國民黨政府對輿論的控制愈來愈緊,公共討論空間不斷受到擠壓,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周刊仍然力圖超越政治,堅持其報刊的獨立性。這些都有利于報刊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發展。
公共領域的形成,最重要的條件,是要有公共意見空間的存在。報刊作為信息溝通的工具,可以成為公眾提供意見表達的平臺。《生活》周刊的“信箱”欄目,便是這一平臺。“信箱”欄目設立后,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到1929年6月,增加到平均每日100多封”,“到1932年5月,最多時竟日收千封以上,每年收到的來信總數在兩三萬封”。1926年,鄒韜奮接編《生活》周刊后,開辟了讀者信箱專欄,親自答復讀者提出的問題,以后其所辦刊物均有這一專欄。二卷一期《生活》周刊發表了讀者禮弘的一封來信,對如何辦好刊物提出7條建議,其中第四條就是增加讀者信箱專欄,韜奮在答復信中說“關于第四條,極端贊同,本期即其開端。”①讀者信箱設立以后,廣大讀者踴躍投信參與到這一欄目。鄒韜奮也投入了很大的心力,以期通過這一欄目實現《生活》周刊“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的宗旨。②他“答復的熱情不遜于寫情書,一點都不馬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由于長期秉持這種服務大眾的精神,“信箱”欄目才能一直關注民眾的生活學習,關注社會所發生的變化,反映人民的生活狀態。
《生活》周刊原是一份討論青年職業教育的刊物,后來逐漸開始討論時事及社會熱點問題。隨著刊物關注點的變化,讀者信箱專欄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1930年以后,讀者信箱欄目開始針對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問題連續發文,與讀者進行廣泛的意見交流,漸漸形成濃厚的討論氛圍。比如對民國初年社會風氣漸漸開放背景下男女交往問題的討論,“信箱”欄目就做了好幾期的討論,如6卷19期刊載的《丑態百出》、3卷44期的《“吾愛!”》、4卷31期的《快跟牢前面一輛女子的車子》等。這些來信大多講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丑態百出》講述某小學女教員Y女士才貌出眾,她的一位泛泛之交的同事,借口傾慕于她,便擅自走入她的房間,跪地求愛并拼命要求和她接吻一次。③但鄒韜奮在編輯回復這些來信時,常常是突破讀者個人的小圈子,將這些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小事放在時代與社會的大環境下,以通俗又有教益的語言加以討論,如此來啟發民眾,引起共鳴。在談論男女交往的問題時,《生活》周刊指出,“完美的社交行為須包含以下三件事:第一完成自己最高尚的人格,第二為他人求最高的幸福,第三為社會求最大的利益”。同時,要對“漫無限制的社交自由”加以約束,使其有“相當的道德觀念及制裁為保障”。④《生活》周刊就是通過這樣富有指導性的語言,從讀者的小事聯系到大的社會問題,再給讀者以意見。鄒韜奮常常在復信中指出,讀者不應“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筆者認為,讀者來信對鄒韜奮及《生活》周刊來說不過是個引子,通過它引出具有公共性的話題,在報刊上形成輿論,使報刊成為民眾討論公共議題的場所,逐漸形成報刊公共領域才是其最終目的。
鄒韜奮和《生活》周刊“信箱”欄目,是中國近代報刊建構公共領域的首次成功嘗試。“信箱”欄目成功的原因,歸結起來,有以下幾點:一是報刊始終保持中立的立場,不代表任何黨派發聲,只為社會公眾代言;二是報刊始終秉持為民眾服務的宗旨,解決民眾最關切的問題;三是編者與讀者間始終以平等的態度交流,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四是在問題討論中,編者始終能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給讀者以有益的建議。縱觀當代中國報刊建構公共領域的成功范例,如《南方周末》評論版所建構的報刊公共領域,可以發現它與《生活》周刊“信箱”欄目有許多共同之處。《生活》周刊“信箱”欄目在建構報刊公共領域方面的雖然是個例,但其成功的經驗是值得研究和借鑒的。■
參考文獻
①《我所望于<生活>周刊的幾點管見·編者附言》,《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
②鄒韜奮,《我們的立場》,《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
③詹季成,《丑態百出》,《生活周刊》,第6卷,第19期
④《介紹費女士的幾篇文章(上)》,《生活周刊》,第4卷,第13期
(作者: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0級研究生)
實習編輯:何健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