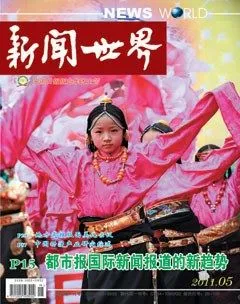對“媒體審判”觀點的不同看法
【摘要】近年來,不少案件由于媒體的報道引發了社會輿論“一邊倒”的情形,司法界和學界因而產生了“媒體審判”的擔憂。筆者認為,輿論評價與法律評價完全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概念,至少在當今中國以及今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媒體還沒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夠真正左右司法審判的結果。
【關鍵詞】媒體審判 罪刑法定 無罪推定 新聞輿論監督
近年來,“媒體審判”(trial by media)一詞頻頻進入公眾的視野。其典型案例是喧囂一時的劉涌案,法院判決從一審的死刑到二審的死緩,再審又改判死刑立即執行,期間由于媒體報道的介入,引發了社會公眾輿論“一邊倒”的情形。“張金柱案”、“夾江打假案”等同樣由于媒體的連續報道而廣受關注,而張金柱的臨終之言“我是死在了媒體手里”更讓許多人感慨媒體影響了司法公正。
殺死張金柱、劉涌的真的是媒體嗎?筆者認為,無論是從“罪刑法定”的角度,還是從“無罪推定”的角度來看,對媒體的指責都是不成立的。至少在當今中國以及今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媒體還沒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夠真正左右司法審判的結果。且從總體上來看,媒體發揮的正面作用遠遠大于負面作用。
罪刑法定——理想與現實的交鋒
如今,當一個新聞事件發生時,媒體報道介入的時間越來越早。越來越多的案件在進入司法審判程序時,甚至在案件發生之時起,就已有媒體以社會新聞的形式進行報道。有的報道以新聞追蹤的形式存在,甚至貫穿了司法審判的整個過程。一些學者提出,媒體是否利用了公眾輿論的力量向司法施壓,從而出現符合公眾的道德判斷、卻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枉法裁判?
作為當代刑法的剛性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最早來源于“刑法學之父”、意大利學者貝卡里亞的學說。縱觀各國刑法,其精髓可歸納為“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其在法律適用上還有幾個重要的含義:一是時效原則,即認定某一行為是否犯罪,須以行為時的法律規定為準;二是對于刑法的規定,法院不能作出超越法律原則、界限和法律原意的解釋;三是罪刑法定原則嚴格禁止類推。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是相對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而言的,確立這個原則,是現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一大進步。罪刑法定原則于1997年在我國刑法中得以確立,成為我國刑法在法治化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尤其是定罪活動的法治化,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司法獨立、法官獨立的問題。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在其文章《入罪與出罪: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雙重考察》就曾提到,從這個意義上說,司法不獨立、法官不獨立是罪刑法定司法化的最大障礙。不可否認,能使法官受影響的因素很多,媒體報道只是其中的一種。我國現行的司法體制是當地司法部門要接受同級黨委尤其是當地政法委的直接領導,很多大案要案都要提交政法委,征詢意見,然后才下發審判結果。那么,如何保證黨政部門的干預能夠促進司法公正而不是相反呢?如果法官素質過硬,敢于并且善于獨立行使審判權,何愁媒體對案件說三道四。相反,由于受輿論影響而不公正判決的案件,也恰好說明法官素質不過硬是影響判決的根本原因。媒體報道所反應的是公眾利益,所要追求的也是公正、客觀、公平,這與司法審判所追求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把影響司法公正的“帽子”全部加到媒體頭上,未免過于偏頗。
在劉涌案的一審之前和一審之后,多家媒體都刊載了內容大致相同的有關該案的消息和通訊。這些消息和通訊反應的事實,無論是公安機關通過新聞發布會的方式向媒體發布的,還是公安機關專門向某些媒體提供的,都明顯具有公安機關利用媒體制造輿論的痕跡。在媒體的報道中還多次提到,偵破劉涌案不但得到沈陽市市委、市政府和人大的支持,中紀委領導也對此案作了重要批示。從中不難看出,劉涌案明顯存在一種政治“角力”:角力的一方是沈陽市公安局及其支持勢力,另一方則是劉涌的保護勢力。
其實,和司法審判一樣,媒體報道也是受到各種社會因素所影響的,不可能做到完完全全的客觀。在西方有所謂“獨立調查”和“獨立撰稿人”的存在,比如美國著名的電視時事雜志《60分鐘》欄目,數千名獨立撰稿人遍布世界各地為其供稿。之所以采用“獨立調查”的形式,就是為了不以任何官方部門為背景、使記者在新聞報道中做到盡可能地貼近客觀事實。不過即便這樣,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觀真實地還原事件的本來面目。
實際上,由于當前大量社會新聞的存在,媒體的報道由于其新聞性和時效性的原因,從第一時間取證的角度來看,反而有利于對定罪量刑所依據的客觀事實的查明。另一方面,通過控制某一家或幾家媒體就能夠掌控輿論導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而如今各家媒體之間由于激烈競爭產生的“新聞大戰”,也給法官提供了更多的公眾視角,增加了從多個角度進行思考的可能性。歸根結底,最關鍵的是,一個具有足夠理性、合格的法官,即便要把新聞報道作為了解信息的一個來源,那么他也要作出合理的判斷:媒體的報道究竟是客觀報道還是一面之詞,輿論是理性的訴說還是情緒的宣泄。“罪刑法定”所依據的法律事實并不會因公眾輿論的評價而改變。法官審判案件是以法庭查明的“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而不是以媒體報道的“事實”為依據,以輿論為準繩。
無罪推定——權利與權力的“誤差”
不少人指責“媒體審判”是搞有罪推定,有違無罪推定的法治精神。筆者認為,這樣的指責仍然是不成立的。
無罪推定原則是刑事訴訟的基石性原則,最早也是由貝卡里亞提出來的,其主旨在于反對封建刑事訴訟制度中對被告人的刑訊成為合法的暴行。作為社會契約論堅定信奉者的貝卡里亞在其著作《犯罪與刑罰》中論及刑訊的暴行時說:“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眾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眾保護”,沒有什么權利能使法官在罪與非罪尚有疑問時對公民科處刑罰。今天,這一原則不僅已被作為人權保護的要求載入國際人權文件,而且也成為了各國刑事訴訟中的金科玉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就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公民所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它有哪些基本內容呢?《世界人權宣言》在序言中宣稱:“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宣言第十九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根據《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它媒介。”一個社會要被視為真正的民主社會,就應該對公開發表的思想言論有高度保護,無論其媒體是報紙、雜志、書籍、手冊、電影、電視,或是最新近的網絡。
輿論的評價與法律評價完全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概念。一些重大案件發生后,作為被關注的焦點,自然會引起享有言論自由權利的公眾的議論和評價。作為世界上媒體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公眾對于傳媒與司法公正的關注,較多地都是以美國為例來論證。考察美國媒體報道的發展歷程,其誕生就是同言論自由緊密聯系的。美國廣播新聞界的“一代宗師”愛德華·R·默羅就曾指出,獨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出版是識別真正的自由社會與其他社會的標準。
傳媒報道作為言論自由的一種,可以明確的是,它不是對司法制衡的制度性權力,不是一種獨立于司法、行政和立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它只是基本人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媒體報道和輿論本身都是公民的自發行為,并不代表國家權力,也沒有強制力,更無所謂有罪推定還是無罪推定。對“媒體審判”搞有罪推定的指責實際上是將司法審判對國家制度安排和權力配置的要求用來要求媒體和公眾。相反的,這種指責反映的是控制言論的邏輯思維,而不是保障言論自由的邏輯思維。
令人可喜的是,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化,“開展新聞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和記者的法定義務和責任”這一觀念越來越深入民心,必須依法保障新聞輿論監督權利的行使,也成為客觀情況的必然要求。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其中明確提到“妥善處理法院與媒體的關系”,“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要求人民法院應當主動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同時,新聞媒體如果對正在審理的案件報道嚴重失實或者惡意進行傾向性報道,損害司法權威,違反法律規定的,依法追究相應責任。
西方有一句有名的格言:正義應當以看得見的形式存在。從這個角度來看,媒體的公開報道其實是對司法審判的另一種挑戰。只有審判結果經得起推敲,才不會害怕媒體報道,以及公眾的輿論監督。法治化進程依然任重而道遠。當代中國應該鼓勵更多的實時報道,如果一味地將其視為洪水猛獸,而拒絕媒體對司法審判的報道,或者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強制媒體報道迎合法院的審判結果,恐有“因噎廢食”之誤。■
(作者單位:汕頭經濟特區報社)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