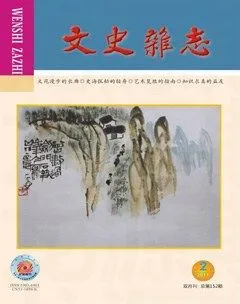張獻忠帝蜀史的畸形研究
2011-12-29 00:00:00馮廣宏
文史雜志 2011年2期



一、偏愛辯解終究無益
現代研究家出自對農民起義首領的熱愛,極力否定張獻忠“屠蜀”一事。其論證方式雖有多端,而目標和趨向則基本一致:
一是痛斥“張獻忠殺盡蜀人”的讕言,以歸還其清白。其實“殺盡蜀人”這句話僅屬文學性語言,既無定量價值,亦非史學定性;即使不做考證,只憑常識也能知道,誰能把四川人殺個一干二凈,不留半口?所以反復辯證根本沒有必要。
二是力辨張獻忠殺人數量不大,以洗刷其罪責。這可能是個可笑的命題:如果在戰爭環境下殺戮和平居民,殺一千人和一萬人有無區別?殺一萬人和十萬人有無區別?人為萬物之靈,能夠隨便去殺?
三是引經據典論述所殺者皆為該殺者,以突出其正義。這種論述就過于帶理想主義色彩了,或可評為迂腐之論。在對敵斗爭的真刀真槍條件下,要說不枉殺一個好人,那是不可能的;但看上世紀歷次運動過后,不也常給千百人平反嗎?何況據以為證的史料,也都是些野史,并非檔案材料。
四是極力強調清初四川人口銳減并非張獻忠主責,以呼吁其冤屈。這一論題也和殺人數量問題一樣,是個五十步笑百步的論題。實質問題是,張獻忠究竟有沒有導致四川人口的減少?
五是挖掘張獻忠性行的優點和行為的進步性,以歌頌其高大。如果說凡屬農民起義都在推動社會的進步,都在摧毀封建腐朽的制度,都在為民造福,救民于水火,永遠是功大于過,誰都不會相信。可是對任何一個人,都需要一分為二,既有長處,也有短處,張獻忠當然也不例外。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正史語焉不詳,野史資料零星分散,詳略不一,有些記載互相矛盾。研究家們大力爬梳、搜采,鑒別真偽,用功極勤,令人欽敬。可是以往較長一段時期,歷史研究須以階級斗爭為綱,以致引導出一種唯心史觀:凡屬農民革命就必須劃入進步范疇,負面也應視之為正面;至于對方,則正面也視之為負面。在實質上,這種做法也和舊史家的“正統論”一樣,曹操須以白臉奸臣形象出現,武則天亦須定位為篡奪。
研究家過去有一定苦衷,有些話不好說、不能說、不敢說,這完全可以理解。不過,仍有不少史家堅持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比如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圖一)就是一部杰出著作。顧誠的書出版于1984年,仍以立場鮮明的階級分析指導全書,但卻沒有失去史學家的公正態度,對于野史記載內容未嘗任意取舍,而是有鑒定、有考證地客觀對待。例如面對“屠蜀”問題,他聲稱“史籍中常常回避張獻忠在四川前期和后期政策上的變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后期客觀形勢的改變和主觀判斷上的錯誤而殺人過多,說成是一貫如此”;“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正視包括張獻忠在內的大西政權領導人的錯誤。把凡被大西軍所殺的人都說成是該殺的,都是農民革命的死敵,不僅違反歷史事實,也不利于從中總結歷史的教訓”。這些話語,應該算是金針玉尺。
二、曲解歷史終究無功
現代研究家孫次舟抱著為張獻忠申冤的心理,總以為《明史》和其他野史中張獻忠形象之不堪,都是以清代“文字獄”為代表的文化專制統治在作怪:
清朝在征服中國和統治中國的過程中,很早就懂得文化統治的重要性。
清朝為了防止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張煌言大舉反攻,進逼南京之威脅的再度發生,因此制定了遷海、告密、奏銷三項政策,對漢族人民進行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多方面迫害。
由于獎勵告密的結果,發生了康熙二年(1663)的莊廷私修明史案,許多無辜者遭到殺害。由此發生了兩方面的影響:在漢族知識分子方面,感到明朝的歷史變成禁物,不能公開寫作,公開談論了;在清朝方面,開始認識到文化統治的需要,對明史要來一番欽定工作,對民間保存的明史資料,也要大力搜查一番。康熙十八年(1679)開明史館,地方官假借修史為名,向東南一帶世家大族強索明史資料。人民懼禍,大批的明史資料被湮沒或竄改了。
的確,清王朝為了鞏固政權,制造了不少文禍,許多民間史料被銷毀和篡改,以致記錄明末史跡的第一手材料,在今天顯得相對欠缺。不過,如果據此推論現存所有野史,統統經過官方有意刪改,或統統由私人因避禍而修改,恐怕也過了頭。因為這種史料篡改,做的是減法而不是加法,凡是描寫張獻忠殘暴的內容,官方不必為之掩飾而銷毀,私人也不會無緣無故地胡亂添加;而且張獻忠在生之日,大西軍并未與清軍大規模作過戰,主要是追打殘明勢力和地主武裝(包括攻擊李自成力量),擴大勢力范圍。照道理說,清廷治下的人士,記載張獻忠事跡應該沒有什么忌諱可言。如果說連私家保存的此類野史也要篡改,在因果關系上恐不能成立。
在互聯網上,有些學者也曾作出類似質疑——
孫次舟的《張獻忠在蜀事跡考察》中是這樣說的:
四路殺人偽說的編造者是馮甦,即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九所引《見聞隨筆》的作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四著錄《見聞隨筆》二卷,并說:“時方開局修《明史》,總裁葉方藹以甦久官云南,詢以西南事實。因摭所記憶,述為此編,以送史館。毛奇齡分纂《流寇傳》,其大略悉取材于此。”馮甦奉命撰寫的《見聞隨筆》,是抄襲與偽造的混合品。其大部分的南明史實,是抄襲的原本《劫灰錄》,又偽造了李自成、張獻忠二傳,冠諸編首。這一隱秘,是清咸豐間一位不慕榮利的老學人葉廷琯給透露出來的。葉氏《吹綱錄》卷四《劫灰錄補注跋并撰人辨》說:“觀《隨筆》一書,大段與《劫灰錄》相近,惟增入張、李二寇及張同敞、李乾德、皮熊三臣。而三臣事跡,《劫灰錄》已散見諸臣傳中。頗疑嵩庵(馮甦號)即取珠江舊史(葉氏考證為方以智)之書為藍本,增刪而成《隨筆》,上之總裁。”馮甦的書,成為毛奇齡據以對張獻忠誣蔑栽贓的資料根據了。由此可見,對張獻忠“屠蜀”的誣蔑,實出于清政府的意旨,馮甦奉命撰寫《見聞隨筆》,“以送史館”,便把這種意旨暗示給纂修官。毛奇齡也就奉迎意旨來擬稿。
雖然孫次舟考證得非常詳細,但是我們不得不懷疑一點:那就是總裁詢問馮甦有關史料,就一定意味著他是奉了皇帝的旨意暗示他修改史料么?從史料而言,恐怕不能如此言之鑿鑿的用陰謀論來解釋吧?咸豐年間的這位葉老先生不過是說馮甦有所增刪,尚未能夠確定是杜撰,那么與《明史》編撰相距更遠的孫次舟,又怎么能夠如此肯定的說這是杜撰呢?
古人對于修史,都抱有一種傳統道德觀念,視為神圣事業;我們決不能隨隨便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俗話說:遠來的和尚會念經。意大利耶穌會教士利類思1637年來華,與葡萄牙教士安文思一同在1642年入川,與成都知縣吳繼善交往,并在成都傳教。此后張獻忠占領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吳繼善任禮部尚書,向張獻忠推薦這兩位牧師。他們從此進入大西陣營,受到一定尊重,也目睹了張獻忠的所作所為,其中不乏種種驚險遭遇。1646年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山中箭身亡,他們兩人也是目擊者。當時他們被清軍俘虜,先到西安,1648年到達北京,受到順治皇帝的禮遇。安文思后來寫下《張獻忠記》,交給耶穌會神父。1866年,法國牧師古洛東來到中國,見到這個抄本,大感興趣。由于他精通中文,便做了翻譯并加注釋,于1904年寫成《圣教入川記》(圖二)一書出版。洋牧師的記錄,顯然沒有杜撰或誣蔑的嫌疑。
再用《圣教入川記》的記載與種種野史所述來進行核對,發現很多情節是相當吻合的。例如:
牧師說:“張獻忠占據蜀川,虐殺僧道。”
——費密《荒書》:“獻賊之據成都,日取人而殺之。先殺衛所指揮千百戶,后殺僧人、道士、匠作、醫士,皆令州縣解入成都。殺則投南門外大橋下。”
牧師說:“二人親見獻忠震怒,七竅生煙。”“野心難化,喜怒無常,咆哮如虎,怒罵之聲,遠近皆聞。”
——《獻賊紀事略》:“忠怒氣沖天,須發為豎,咆哮之聲,徹于街衢。”
牧師說:“獻忠性情殘暴,稍有不順,狂怒隨之,或刑或殺,視人命如草芥。”
——計六奇《張獻忠亂蜀本末》:“獻忠暴狠嗜殺,鞭撻無虛刻。即左右至寵至信者,少失其意,即斬刈如草芥。”
牧師說:“或令絞死、斬決,凌遲碎剮,種種虐刑,令人寒心。”
——李馥榮《滟滪囊》:“賊屠戮經過,斬首、割耳、剁手、剝皮,種種殘忍,見者聞者無不酸心。”
牧師說:“吳繼善以細故觸怒獻忠,即受虐刑斃命。”
——《鹿樵紀聞》:“前縣令吳繼善降賊,授偽官,一日為賊寫祭天文,其紙中接。賊見之,怒曰:‘若不欲我一統乎?’立剮之。”
牧師說:“獻忠殺人無算,屢自解云:吾殺若輩,實救若輩于世上諸苦。雖殺之,實愛之也。”
——《獻賊紀事略》:獻忠曰:“朕向來誅戮者,皆代天行道,非屈殺也。”
牧師說:“獻忠深惡川人。以為漢中及各處之敗,皆由川人使之,故殺川人十四萬之多。擬將川省變為曠野,無人居住。”
——顧山貞《客滇述》:“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老幼男女,逢人便殺,如是半載。”“獻忠又令其眾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歲以下者,僅留一二。四川之禍,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無人,空如沙漠。”
牧師說:“驅百姓到南門就刑。時利司鐸在南門上,安司鐸在東門上,見無辜百姓男女被殺,呼號之聲,慘絕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安司鐸見獻忠大殺之后,不禁凄涼,乃漫步而回。是時日落西山,正直黃昏之際,見道旁死尸狼藉,其中尚有小孩呻吟者。”
——劉景伯《蜀龜鑒》:“復屠成都。”“詭曰:天書降,令我剿絕蜀人,違者門誅!十人一縛,驅至中園殺之。”“所在震栗。人民千百羅跪,賊數十人次第斬之,無一人敢起立者。”
牧師說:“探知人民避跡山洞巖穴者,皆擒而殺之。”
——吳偉業《綏寇紀略》:“搜巖洞,發窟室,登高處以望突煙。”
牧師說:“獻忠由川往陜,離成都時下令將皇宮焚毀。在城外見濃煙騰起,火光燭地,大為狂喜。復令全城四面縱火,一時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樓臺亭閣,一片通紅,有似火海。大明歷代各王所居之宮殿,與及民間之房屋財產均遭焚如。轉瞬間,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實屬可惜。”
——《鹿樵紀聞》:“賊毀成都,焚蜀府宮殿,及未盡民房;火不能毀者,聚薪發炮,必裂碎之而后已。成都有大小城,相傳張儀所筑,劉先主復修之;甃以巨石,貫以鐵縆,雄壯甲天下,宮室之盛,擬于京師,一旦變成瓦礫。”
張獻忠種種惡行,洋牧師和野史所記,并沒有很大出入,可證實孫次舟所論之不確。在時時處處強調愛心的牧師口中,一個惡魔形象,已經無所遁影,無論何種辯解均失去實際意義。反觀清廷所纂《明史·流寇傳》里的張獻忠,好像遠遠不如牧師說得露骨——這難道也是清朝皇帝的旨意?
三、剪裁史料終究無濟
前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郭影秋著有《李定國紀年》(圖三)一書,1960年出版;2006年人民大學出版社重印。這本書,郭先生敘稱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待史料”,著力于替張獻忠“翻案”,就因為他17年間一直忠于農民軍并為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又力辯地主階級誣蔑農民起義軍“流賊嗜殺”的口號,認為地主階級文士偽造了一通“七殺碑”;將史載張獻忠“一日不殺人則郁郁不樂”,斥為謊言,稱“卑鄙到這般程度!”指出殺人最多的劊子手,還是明清豢養的官兵。其結論:“張獻忠所領導的農民戰爭,是為了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利益而進行的”!
郭氏此書體例獨特,以張獻忠義子李定國這個英雄人物為綱,分年記述農民軍活動中的大事,并與李定國事跡掛鉤——從1630年張獻忠起義開始,至1662年李定國病死為止。每年所記述的史事,基本從100多種舊籍中輯出,包括正史、野史、方志、檔案等,不僅盡量引用原文,而且作出不少精當的考證,其學術功力與治學辛勤確實令人敬佩。不過,正如戴逸《再版前言》所說:這部著作,“畢竟是四十多年前的著作,加之,作者撰寫此書時,又正處在頻繁發生政治運動的環境中VdGNB7kJnBkNQx4ztevgrg==,這些帶有極左傾向的政治運動,也勢必在意識形態與學術研究中有所反映。”“這部著作也難免留有時代的烙印,對此既毋庸諱言,也不應苛求。”確屬肺腑之言。
如果檢查一下書中最嚴重的“烙印”,便可發現,那就是對史料的有意剪裁。這里僅舉二例:
1643年張獻忠攻陷蘄州。書中綜合記為“旦日,獻忠入城。開各門放男子出,留婦女毀城。”實際上《小腆紀年》文為“開各門放男子出,留婦女毀城,稍不力即被殺。”《明季北略》文為“遂屠蘄州。留婦女毀城,稍不力,即殺之。”《爝火錄》文為“驅婦女鏟城,尋殺之以填壑。”派婦女拆城墻,顯然是件力不勝任的事,完全屬于虐待,意在置之于死地;為什么把男子放走,不叫他們拆?書中采取模糊處理,不置可否。
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分兵為120營。書中在“各營知名者為”句下,列舉了“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等14個營名和總兵官姓名,下面又有五六個營名,這些材料都來自《蜀記》、《后鑒錄》、《明季南略》等書,但沒有交代原文所述這些總兵之所以能夠名留史冊,皆因受了剝皮酷刑;而罪名則是貫徹張獻忠“除城盡剿”命令不力,“搜括徇庇”,保護了無辜百姓,“坐大惡不道”。
最后,還有一個研究家喋喋不休的問題,就是四川人口銳減,是不是張獻忠所造成的?由于那時沒有任何檔案記錄,大家僅憑推理,難以得出科學的結論。可是有一條卻很明確,就是張獻忠的屠殺軍民,帶有強烈的計劃性、目的性、徹底性。張獻忠仇恨蜀人,有消滅蜀人的意向。張軍紀律格外嚴明,一道命令下來,如果哪一小隊執行不力,整個一營人可能都得去死。大慈寺幾個和尚隱藏了朱姓宗室,全寺上千和尚都要砍頭。加上他清鄉運動中對建筑物和器物的大量破壞,使民眾生產和生活手段基本喪失,無形中制造了饑餓,制造了瘟疫。應該說,在四川人口銳減過程中,他打響了驚天的第一炮,行了一個恐怖的奠基禮。
有歷史唯物主義,也有歷史唯心主義。今天我們研究張獻忠帝蜀史,如果無視眾多史料中的共同指向,一味以某種最高原則為綱,任意割裂乃至曲解原始材料為我所用,就使人不得不懷疑他在歷史研究面前,究竟信奉些什么?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