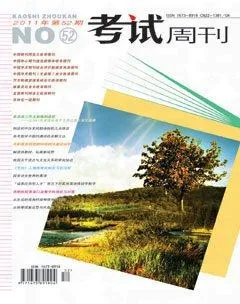郭沫若與華茲華斯的浪漫主義
摘 要: 郭沫若和華茲華斯是中英兩國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義詩人,但華茲華斯重視個人情感與人類共同情感息息相通,不追求奇特的想象和夸飾,不讓放縱的感情扼殺真和美,認為浪漫主義詩學在過分強調個人情感方面可能引起歧義,而郭沫若則追求狂放的自我擴張,表現出一個個性極端膨脹的無所不在的主體。
關鍵詞: 郭沫若 華茲華斯 浪漫主義
一
郭沫若(1892—1978)和威廉·華茲華斯(1770—1850)是中英兩國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們生活的時代雖然相距一百多年,但面對的社會矛盾和訴求有其相似的一面,都要求沖決長期以來的專制社會對于人性和文化的束縛,都要激活一切在陳規陋習下僵死了的鮮活的生命力,都注重自我,注重精神和神性,都熱烈地謳歌和抒發一切屬于個人的感覺、情懷,都敏感于所描寫的生活事件。
可以這樣說,是泰戈爾、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煽起了郭沫若熱愛文藝的心火,是“惠特曼的那種把一切的舊套擺脫干凈了的詩風和‘五四’時代的暴飆突進的精神”,使郭沫若“徹底地為他那雄渾的豪放的宏朗的調子所動蕩了”。[1](143)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郭沫若雖然遠居國外,但是他最深切地感應到了時代的心音。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昂奮。他不僅立即組織了以“排日”為宗旨的留日學生團體“夏社”以響應國內運動,而且立即以本名和“夏社”的名義連續寫出文章發表在1919年10月上海出版的《黑潮》雜志第1卷第2期上,一面用大量事實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瘋狂侵略中國的行徑,一面呼吁同胞迅速奮起,擔負起救國的責任。
他這一寶貴的愛國熱情,緊接著在《匪徒頌》、《鳳凰涅槃》、《晨安》、《爐中煤》等詩篇中燃燒起來,含著血和淚一起燃燒。他控訴帝國主義的凌辱,詛咒祖國的黑暗,還把祖國比作他心愛的姑娘,他的“眷戀”之情像爐中煤一樣燒得通紅。
郭沫若顯然是一個極富激情和理想的革命派和浪漫派,正如他說蔣光赤在“浪漫”受到攻擊時,公開宣稱:“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有理想、有熱情,不滿足現狀而企圖創造出更好的什么的,這種情況便是浪漫主義。”[2](244)
華茲華斯在青少年時受到的思想資源和對革命的向往與郭沫若有大致相似之處。但他沒有郭沫若那樣深受母親和哥哥的教誨和愛護,八歲喪母,十三歲喪父,靠了舅父的接濟,才于1787年進入劍橋大學學習,逐漸接受法國啟蒙思想。此前他能成段背誦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作品,畢業前一年即1790年的暑假,他沉迷于盧梭的思想之中,故與同學一道去法國等地旅行。在法國,他親眼目睹了法國人民歡慶攻陷巴士底獄一周年的情景,一年前的1789年7月14日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在詩人心中喚起了激情。這種激情雖然因為法國革命最終沒有實現“平等自由”的理想,因而——
你們涌上去觀看的,不正是
一根在風中顫抖著的蘆葦?
王公貴族、政客、律師、縉紳之輩,
病的、跛的、瞎的,不分顯要寒微,
好像全一個德性,匆匆趕去法蘭西,
帶著新的貢品,叩見剛登基的皇帝。
……
——《一根風中顫抖的蘆葦》[3](188—200)
但詩人仍然憧憬著讓“自由和偉力”來改變當時的英國。他在《密爾頓,你應該……》一詩中呼吁:“密爾頓,你應該生活在這個時代/今日英國,多需要你那樣的偉才。/她已變成了一灣泥淖,一泓死水/祭壇、刀劍、文明風俗和豪門巨富/已保不住英國人往昔的/得天獨厚的內向的幸福。/啊,請回來使我們從自私中奮起/給我們以道德風范,自由和偉力。/……”[4](188—200)
當然,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在雅各賓專政時期的恐怖政策面前,在英國的腐朽現實面前,華茲華斯的世界觀經歷了最激烈最復雜的斗爭,也是詩人游蕩不定的時期,對啟蒙主義的信念也不無懷疑和動搖。于是他回到湖區,并與柯勒律治、司各特等往還,過上了理想的“田園生活”。他也懷著同情的心理和靜觀的哲學觀察貧苦農民的生活。他滿懷鄉愁,寫下了《采干果》、《露絲》和《露西》等組詩,同時開始寫長詩《序曲》和《孤獨的收割者》、《不朽頌》等名篇。1807年,他出版兩卷本詩集。1815年后逐漸稀薄,1835年后則幾乎不再發表作品。他似乎顯得低調和退化,即使最激情的歌唱也充滿節制,在這一點上與郭沫若簡直有天淵之別。但他卻是公認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奠基人之一,英國文學史家一般傾向給予很高的評價,有的人像安諾德一樣,把他置于拜倫、雪萊、濟慈之上。著名評論家德·昆西則說:“1820年之前,華茲華斯的名字給人踩在腳下;1820年到1830年,這個名字是個戰斗的名字;1830年到1835年,這已是個勝利的名字了。”[5](161)
二
對浪漫主義的理解,因人而異,正如歌德所言:“古典詩和浪漫詩的概念現已傳遍世界……這個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兩人。我主張詩應采用從客觀世界出發的原則,認為只有這種創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卻用完全主觀的方法去寫作……”[6](221)同是英國浪漫主義詩歌驕子,華茲華斯強調自然美,柯勒律治以植物的自然成長來比喻詩情的自然而至,雪萊強調善的美,濟慈則把真與美統一起來,強調真的美。濟慈是與華茲華斯比肩而立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理論散見于一些詩作和《書信集》中,他在《希臘古瓷頌》中說:“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濟慈認為,由于詩人處在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中,一定要強調想象所攫取的美必須是真實的。
對于浪漫主義本質的理解,華茲華斯與他同期的英國同行取相近的步伐。通觀華氏的所有詩歌,沒有大膽的夸張,奇特的想象和環境,而是選擇普通生活中的事件和微賤的田園生活,以及下層人民如個體農民、破產農戶、小藝人作為詩歌主人公,即使是歌頌黑人革命領袖的《致杜桑·盧維杜爾》一詩,那詩情也僅是自然流出,沒有特別的夸飾,最壯麗的詩句也不過是“還有天空,大氣和土壤/是高舉你的旗幟的力量。”(《詩選》,第194頁)
華茲華斯意識到浪漫主義詩學在過度強調個人情感方面可能引起的歧義,于是他力圖把詩人主觀的“目的”和讀者主觀感受的“價值”聯系在一起。他特別強調詩人的個人情感與人類共同情感的息息相通,要做到“詩人唱的歌全人類跟他合唱”。[7](161)詩歌本來具有超越個人感情的屬性,但華氏仍然在強調著共性,這是因為他已經意識到個人感情的放縱可能扼殺了詩真和詩美。
郭沫若與華茲華斯迥然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即表現在詩歌中熾熱的個人情感和個性主義。“五四”前后,個性主義在推翻一切傳統的重壓中有過相當的革命意義。就在這股要求個性解放、呼喚個人自由的社會大潮中,郭沫若帶著他的蘆笛登場了。他的聲音雄渾高亢,迥非尋常。他訴說了人的個性被束縛,被壓抑的痛苦,對摧殘和扼殺人類自由精神的封建制度發出了強烈的詛咒。他高唱“自我”之歌,他熱烈追求“自我發展”、“自我擴張”,凡是讀過《女神》的人,誰能忘記那個“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的歌者?誰能忘記那只不停地在飛奔、狂叫、燃燒著的“天狗”?誰能忘記鳳凰的自焚?誰能忘記詩人在梅花樹下的醉歌?那便是郭沫若的“個性解放”。我們看到,他的追求是那么大膽,那么狂放,真是快要狂了。《匪徒頌》共六節36行,感情強烈的驚嘆號就有42個。再看《天狗》:“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嚙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經上飛跑。//我在我背髓上飛跑,/我在我腦經上飛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8](191—192)可謂靈感爆發,熾熱的情感完全進入了迷狂狀態。這是一個自我極端膨脹的無所不在的主體。
郭沫若和華茲華斯詩歌中的個人情感與個性主義色彩的迥異,除了他們對浪漫主義本質的理解不同以外,還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郭氏反抗黑暗現實的革命性,而華氏“后期的政治思想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9](132)
二是郭氏以“唯能論”觀點解釋生命。
這是過去郭沫若研究中很少言及的郭氏早期的《生命底文學》:
人類生命中至高級的成分便是精神作用。精神作用只是大腦作用底總和。大腦作用底本質只是Energy底交流。
一切物質皆有生命。無機物也有生命。一切生命都是Energy底交流。宇宙全體只是個Energy底交流。
接著,郭氏說明了文學與生命的關系:
Energy底發展便是創造,便是廣義的文學。……
Energy底發散在物質如聲、光、電熱,在人如感情、沖動、思想、意識。感情、沖動、思想、意識底純真的表現便是狹義的生命底文學。[10](62)
這就是“唯能論”。郭沫若以“唯能論”的觀點解釋生命,把“精神作用”說成“能底發散”,就混淆了思維與存在、物質與意識的辯證關系。生命的本質屬性也不是“唯能”,而在于物質運動。文學是精神現象僅是第二性的,社會生活即物質是第一性的,郭氏把文學說成“能”的發散,如天狗憑借“能”穿越一切,這就把“能”看得高于一切,把物質現象與精神現象混同起來了。
三
對于主觀性的重視,對于人的內心世界的表現是浪漫主義文學的突出特點。但是,不能向內心開掘趨于極端而顯得畸形、變態。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曾感嘆:“德國的浪漫主義病院里收容了一些多么古怪的人物啊!”甚至說它“從其源頭來說就中了毒”。[11](8,12)
隨著時間的推進,人們越來越不滿這種泛濫的情感宣泄。浪漫主義詩歌備受新批評的責難,艾略特是始作俑者。他主張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他認為詩人的思想(the poet’s mind)在創作中的作用如同催化劑,并未參與到各類文學、哲學,經驗的材料在“非個人化的實驗室”被加工,發生“化學反應”而成為詩歌的過程中。[12](26)這表示,浪漫主義的情感宣泄和揮灑是為艾略特所厭棄的。
我們所以持相似的看法,乃是覺得放縱的情感內容超出了客觀的物質形式本身的意義,是精神溢出了物質,理念壓倒了形象,即便感到了美,卻又遠離了真。郭沫若的《女神》即是理念的心靈內容大大超出了客觀物質形式本身的意義,是主體性的無限擴張,精神無限地溢出了物質。《女神》中的“我”幾乎征服、占有了“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他“創造日月星辰”“馳騁風云雷雨”。在《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中,“我”像北冰洋的晴景一樣壯麗,像提起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到太平洋那樣蘊藏著無限神力。郭沫若詩歌中那種罕見其匹和超越一切的力量是故意通過一種粗糙的形式來表達的,直到徐志摩從英國歸來并且在1926年創辦《詩刊》的時候,那場嚴肅的革新——特別用詩歌韻律美抗拒粗糙形式方面——才算是開始上路。
上世紀前期的中國新詩對浪漫主義的理解確有其片面性,正如李歐梵所言:“浪漫主義美學的那些神秘和超驗的層面,在贊成一種人道性,社會——政治性的解釋時,大都被忽視了。重點被放在自我表現、個性解放和對既定成規的叛逆上。”[13]那時,把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看成是浪漫主義文學的必須,因而出現了形式的粗糙和內容的空泛。對此,茅盾也說:“因為是一般地要求著自由,就造成了浪漫主義文學破棄一切傳統的束縛。”[14](89)
反傳統、革命、幻想、夸張、個性主義、英雄主義是郭沫若詩歌的特質;而華茲華斯卻重視傳統,重視小人物、和平、寧靜、真實,最大的特點是人與自然的融合。尤其是在目睹了法國的“革命”以后,他說過“革命不像自然那樣給人帶來純凈和和諧”。[15](61)華茲華斯全身心地把目光轉向了遠離暴力血腥的牧歌式田園風光,山川、田野、野鳥、野葡萄、野薔薇、高天的云雀、幽思的夜鶯、嬌小的蝴蝶,無不引起詩人極大的興趣。且看他的《致蝴蝶》:
我整整半個鐘頭看著你,
你在那朵黃花上歇息,
小小的蝶兒,我真不知你
是在安睡還是把花蜜吮吸?
紋絲不動,即便冰封的海洋
亦不過如此凝然靜止!
……
——《詩選》,第35頁
大自然和小生靈的平和、安寧給了詩人極大的滿足,也給予了他敏銳的詩心。正是這種詩心,他把窺探麻雀窩當做拜訪麻雀的閨房,把野鴿的“咕咕”叫聲,既看成是我們對它的呼叫,又是它原來的啼音,也是它孵卵時最喜歡傾聽的聲音——因為它標志平靜安閑的滿足。
華茲華斯也要求所有詩人應“是一個天生具有更強烈感受力,更多熱情”的人,“由熱情給心靈灌注靈氣,真實就是它自己的證明”,這需要“對于人性有著更多的知識”,“比任何人還要喜愛自己的內心的精神生活”,因為“詩的目的是為了真理”。[16](5—19)
真理并且真實,這才是最高的美。這至少消除了浪漫主義在艾略特等人眼中的缺陷:“夸夸其談的辭藻,玄奧抽象的思想,生硬粗糙的感覺。”[17](45)
參考文獻:
[1]我的作詩的經過.沫若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11):143.
[2]郭沫若.我的學生時代[M].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244.
[3][4]謝耀文譯.華茲華斯抒情詩選[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1:188-200.
[5]鄭克魯主編.外國文學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61.
[6]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M].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221.
[7]劉象愚主編.外國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61.
[8]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191-192.
[9]Aidan Day.Romanticism[M].London and New York:Rout Ledge,1996:132.
[10]凌宇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名家研究[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62.
[11]勃蘭克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二冊)德國的浪漫派[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2]John,H.Selected Prose[M].London.Penguin Books,1963:26.
[13]李歐梵.文學潮流(一)追求現代性(1895-1927)[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4]茅盾.兩洋文學通論[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89.
[15]Stopford,A.Brook.Naturalism in English Poetry[M].Dotton Company Republished,1974:61.
[16]謬靈珠.謬靈珠美學譯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5-19.
[17]張耀軍,古克平.布魯姆早期浪漫主義詩歌理論初探[J].外國文學研究,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