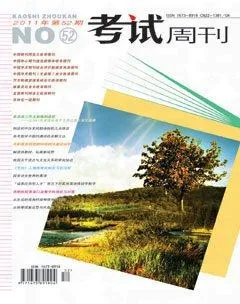略論官商關(guān)系與近代中國企業(yè)的發(fā)展
摘 要: 清末盛宣懷經(jīng)辦輪船招商局之時(shí),其中微妙的官商關(guān)系影響到近代中國企業(yè)的發(fā)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下,前期官商走向合作各取所需,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業(yè)的發(fā)展,推進(jìn)了中國經(jīng)濟(jì)近代化。后期官商合作風(fēng)氣既開,卻依然延續(xù)官督商辦、官辦的企業(yè)形式,甚至封建洋務(wù)官僚從中營私舞弊,排擠商人,壟斷近代企業(yè),最終導(dǎo)致官商交惡。企業(yè)的官化,官商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是制約近代中國企業(yè)發(fā)展一個(gè)不可忽視的因素。
關(guān)鍵詞: 盛宣懷 官商關(guān)系 近代中國企業(yè) 洋務(wù)運(yùn)動(dòng)
一、時(shí)代的產(chǎn)物——官商合作,輪船招商局興起
1870年,秀才出身的盛宣懷依靠父親盛康和李鴻章的交情及楊宗濂的舉薦,進(jìn)入李鴻章幕府,此后20多年他再?zèng)]有通過正途晉升。盛宣懷經(jīng)辦洋務(wù)始于1873年輪船招商局的創(chuàng)辦。最初盛宣懷就力主采取官商合作的企業(yè)集資形式,他在草擬的《輪船章程》中指出:“中國官商久不聯(lián)絡(luò),在官莫顧商情,在商莫籌國計(jì)。夫籌國計(jì)必先顧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不可復(fù)振。試辦之初,必先為商人設(shè)身處地,知其實(shí)有把握,不致廢弛半途,辦通之后,則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祖,償兵之費(fèi)。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務(wù)使利不外散,兵可自強(qiáng)。”[1]可見,在經(jīng)營方式上,他認(rèn)為要經(jīng)營得法必須擺正國家和商民的關(guān)系,要“籌國計(jì)必先顧商情”。由此表明,在西學(xué)東漸中,一部分封建知識(shí)分子向新型的洋務(wù)人才轉(zhuǎn)變,隱含洋務(wù)官員開始注意商人的作用和與商人合作的意愿。同時(shí),盛宣懷早期的思想中還閃爍著一定的民族性。他說:“中國不患弱而患貧,不患在下占上之利,而患洋人占華人之利。”[2]他看不慣中國的商利被外商占盡,想通過中國自己籌集資本經(jīng)商,以抑制外商,與洋商爭(zhēng)利。
為此,盛宣懷與主張官辦的朱其昂產(chǎn)生矛盾,但是初期李鴻章采用朱其昂官辦的主張,可見洋務(wù)當(dāng)局領(lǐng)導(dǎo)集團(tuán)對(duì)商人最初的不信任和戒備心理。然而,事實(shí)很快證明官辦的失敗。朱其昂在籌建輪船招商局過程中曾說:“會(huì)集素習(xí)商業(yè)殷富正派之道員胡光墉、李振玉等公同籌商,意見正同,各幫商人紛紛入股。”[3]實(shí)際上,他在招股方面幾乎一籌莫展。胡光墉是著名的大絲商,在左宗棠幕府中經(jīng)辦洋務(wù),以“畏洋商嫉妒”[4]而裹足不前,始終不肯加入輪船招商局。朱其昂既招募不到商股,又不善于經(jīng)營新式航運(yùn),所以在半年左右的時(shí)間內(nèi),輪船招商局便虧損了四萬兩千兩。他不得不辭去總辦的職務(wù),請(qǐng)求專辦漕務(wù)。于是,輪船招商局進(jìn)行了改組,轉(zhuǎn)入新的階段。1873年,李鴻章委派買辦出身的唐廷樞為商總辦,后來又任命買辦出身的徐潤為會(huì)辦,作為官方代表的盛宣懷和朱其昂只不過是一個(gè)掛名的會(huì)辦,管理官務(wù)。
說明:此期間輪船招商局的會(huì)計(jì)年度大體為第一年的7月至第二年的6月,故年度欄目的數(shù)字均為跨年度的數(shù)字。
資料來源:1.招商局資本、輪船數(shù)、噸位數(shù)引自《國營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紀(jì)念刊》的《附錄》。2.凈收入、折舊和扣除折舊后的利潤三欄目引自張國輝:《洋務(wù)運(yùn)動(dòng)與中國近代企業(yè)》,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79年,第178頁表。[5]
由以上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資料看,1873—1883年,輪船招商局的業(yè)務(wù)和利潤都有所增長。這從表中所列這期間招商局的各項(xiàng)統(tǒng)計(jì)數(shù)字尤其是資本數(shù)、輪船數(shù)和噸位數(shù)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1874年美商旗昌輪船公司在競(jìng)爭(zhēng)中支持不住,旗下大小輪船共有十六艘以兩百萬兩出讓。在李鴻章的支持下,盛宣懷找兩江總督沈葆楨借到一百萬兩官款。于是,招商局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資二百二十二萬,將旗昌公司轄下的全部輪船及碼頭棧房等一起買下。因此,招商局即刻由四條船的小公司變成二十條船的大公司,大大增強(qiáng)了競(jìng)爭(zhēng)力。徐潤后來評(píng)論收購一事說:“……而商局根基從此鞏固,皆盛杏翁之力為多矣。”[6]會(huì)辦朱其昂、盛宣懷負(fù)責(zé)漕運(yùn)和處理一切“官務(wù)”,同時(shí),清政府向招商局提供了許多優(yōu)惠待遇,加以扶持。招商局一改前貌,當(dāng)其決定集資的消息公布后,認(rèn)股情形“大異初創(chuàng)之時(shí),上海銀主多欲附入股份”,很快就招得近五十萬兩。
由此觀之,從早期經(jīng)營的業(yè)績(jī)看,早期的輪船招商局,商辦的色彩濃厚,在洋務(wù)當(dāng)局的庇護(hù)下按照商務(wù)原則開展,也是官商合作的開始,兩者的合作是收到成效的。
探究此次官商邁出合作一步的原因,我認(rèn)為官商合作是時(shí)代的產(chǎn)物,原因有四點(diǎn):首先,最為重要是資金問題。19世紀(jì),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正是風(fēng)雨飄搖之中,對(duì)外割地賠款,對(duì)內(nèi)鎮(zhèn)壓人民起義,國家財(cái)政已經(jīng)是入不敷出,清政府手中已經(jīng)沒有更多的資金投資純粹的大規(guī)模的官辦企業(yè),沒有民間的私人資本支持,洋務(wù)企業(yè)無法順利興起。而朱其昂當(dāng)時(shí)主張完全官辦,很難讓商人取信,從而由依附洋商轉(zhuǎn)而依附官府投資。朱其昂的主張更多是體現(xiàn)封建官僚集團(tuán)的利益,失敗是在所難免的。其次,清政府封建官僚對(duì)經(jīng)辦近代民用企業(yè)缺乏經(jīng)驗(yàn)和管理技術(shù),需要專門經(jīng)營人才,只能尋求與商人合作。再次,當(dāng)時(shí)不少商人手中已經(jīng)通過商業(yè)貿(mào)易積累不少資金,并附股于外商在華企業(yè),已具備了投資近代企業(yè)的能力。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ì)環(huán)境下,工商業(yè)者不僅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排斥和傾軋,而且遭到封建守舊勢(shì)力的盤剝和捐稅的苛擾,只能與官府合作辦企,以尋求官府的庇護(hù),減少阻力。親身參與官督商辦洋務(wù)事業(yè)的鄭觀應(yīng),當(dāng)時(shí)即對(duì)此作過論述。他指出:“全恃官力,則巨資難籌;兼集商資,則眾擎易舉。然全歸商辦,則土棍或至阻撓,兼倚官威,則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辦,各有責(zé)成,商招股以興工,不得存心隱漏,官稽查以征稅,亦不得分外殊求。則上下相維,二弊俱去。”[7]
唐廷樞起草《輪船招商章程》,強(qiáng)調(diào)招商局由自己專管,“作為商總,以專責(zé)成。再將股份較大之人公舉入局作商董,協(xié)同辦理。”[8]又規(guī)定:“事屬商辦,似宜俯照買賣常規(guī)……請(qǐng)免添派委員。”[9]將盛宣懷所擬的《輪船章程》與唐廷樞所擬的《輪船招商章程》對(duì)比,兩人雖然都是主張商本商辦,但是盛宣懷則強(qiáng)調(diào)總辦要“聯(lián)絡(luò)官商”,要“上與總理衙門、通商大臣、船政大臣”等官方權(quán)要機(jī)構(gòu)和人物聯(lián)絡(luò)好關(guān)系。按照盛宣懷的觀點(diǎn),“官”應(yīng)該處于企業(yè)的主導(dǎo)地位,而唐廷樞則要求“商”把握企業(yè)的主導(dǎo)權(quán)。兩者思想的差異,埋下“官”出身的盛宣懷與“商”出身的唐廷樞和徐潤在以后的暗自角力,官商不可避免的矛盾開始若隱若現(xiàn)。
二、官權(quán)和商利的暗自角力、官商交惡,企業(yè)停滯不前
站在商人的立場(chǎng),唐廷樞和徐潤從商人的經(jīng)濟(jì)利益出發(fā),按照商務(wù)原則,擴(kuò)大企業(yè)的經(jīng)營,追逐高額利潤,正如他們所說:“局務(wù)由商任不便由官任”,[10]請(qǐng)清政府“免添派委員,除去文案名目,并免造冊(cè)報(bào)銷”,[11]一切按照“買賣常規(guī)”辦理。但是盛宣懷始終擺脫不了封建官僚的基本屬性,是官股的代言人,他的人生信條是“做高官”,這樣的政治目的和唐廷樞、徐潤的商人利益有沖突和矛盾。
兩者的矛盾首先表現(xiàn)在用人方面。當(dāng)盛宣懷通過朱其詔推薦其親信于唐廷樞時(shí),唐廷樞斷然拒絕,朱其詔將此函告盛宣懷說:“本擬設(shè)法位置,實(shí)源商局用人景翁早已定奪,局中所有伙友,一概不用,以致無從報(bào)命。”[12]
由此可見,早期的輪船招商局的經(jīng)營權(quán)和管理權(quán)牢牢掌握在商人唐廷樞的手中,而這引起盛宣懷奪取“總辦”局務(wù)的企圖。因此,向來說要商辦的盛宣懷,一變初衷地說,招商局應(yīng)當(dāng)“官商合辦,利害共之”。[13]
盛宣懷利用官督的身份,大肆貪污和侵奪,其第一筆就是收購美商旗昌輪船公司所得的回傭。他經(jīng)手二百二十余萬兩,回傭有六七萬兩。當(dāng)時(shí)有御史和兩江總督劉坤一彈劾盛宣懷“工于鉆營,巧于趨避”,“此等劣員有同市儈”,[14]因而請(qǐng)旨將之革職。雖然李鴻章為之“極力剖辯”,但1881年總理衙門奏請(qǐng)“不準(zhǔn)再行干預(yù)局務(wù),并命李鴻章嚴(yán)加考察”。[15]盛宣懷因受到回扣的事情受到彈劾,有三年不再涉足招商局事務(wù)。
1883年,由于世界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危機(jī)和國內(nèi)的資金大批向工礦企業(yè)轉(zhuǎn)移等因素的影響,上海出現(xiàn)了倒賬風(fēng)潮,徐潤挪用局款達(dá)十六萬兩千余兩投機(jī)地產(chǎn)失敗。盛宣懷將此事向李鴻章一稟,徐潤被革職。1883年末,盛宣懷上稟李鴻章,攻擊唐廷樞、徐潤和批判輪船招商局的狀況:“不料總辦之朦混糊涂至于此極也。商本二百萬,乃如開平拖欠八十余萬,各戶往來拖欠七十余萬,各局往拖欠十余萬,各局水腳拖欠三十余萬,則局本已無著矣。其輪船、碼頭、棧房實(shí)估值本不及四百僅足抵老公款九十六萬、新公款五十五萬、保險(xiǎn)存款一百萬、客存客匯一百二三十萬,人安得不望寒心。”[16]他進(jìn)而將招商局存在這些問題的原因歸咎為:“其病在以長存款四十余萬不收帳,皆屬自挪移;又病在多造輪船、多得用錢,而船不能走長江、天津,名為放駛外洋各埠,實(shí)只放駛廣東一無船不虧本;又病在添造金利源三層樓沿河棧房,花費(fèi)四五十萬,而無貨堆,新聞紙招堆客貨亦濟(jì);又病在大小司事皆以貴價(jià)買開平股份,無不虧本數(shù)萬兩,至少亦數(shù)千兩,其勢(shì)不能不作弊。”[17]事后,徐潤曾說:“此亦杏翁居心太苛,防我等重備船只在該處設(shè)立碼頭,與彼爭(zhēng)霸,故為此殺一儆百之事。”[18]實(shí)際上表明了在盛宣懷和唐徐之間發(fā)生了一場(chǎng)長近十年的權(quán)力斗爭(zhēng)。盛宣懷說唐廷樞專說大話,說徐潤忙于私務(wù)。而唐廷樞則認(rèn)為盛宣懷口蜜腹劍,倚仗官僚的支持牟取私利。而盛宣懷一語道破兩人矛盾的癥結(jié)在于權(quán)力被徐潤所攬,他與徐潤“兩人不能再合”,“再合”會(huì)出現(xiàn)“太阿倒持”的。[19]
1885年,盛宣懷被委任為輪船招商局督辦。入主輪船招商局以后,雖然仍強(qiáng)調(diào)“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20]但同唐廷樞主持時(shí)期比較起來,“商辦”大為削弱,“官督”大為加強(qiáng)。在用人機(jī)制上,盛宣懷制訂《用人章程》和《理財(cái)章程》各十條,主要內(nèi)容有如下兩點(diǎn):第一,“專派大員一人認(rèn)真督辦,用人理財(cái)悉聽調(diào)度”,“會(huì)辦三、四人應(yīng)由督辦察度商情,秉公保薦。”[21]這項(xiàng)規(guī)定使督辦能夠控制輪船招商局的人事權(quán)和財(cái)政權(quán),完全廢棄了1873年《局規(guī)》中關(guān)于由股東推舉商董和總董主持業(yè)務(wù)的原則。雖然輪船招商局受到中法戰(zhàn)爭(zhēng)的波及而一度被迫抵押,遭受損失,但是也與盛宣懷官化的管理方式有密切的聯(lián)系。此后的輪船招商局,噸位幾乎沒有增添,通過與外國競(jìng)爭(zhēng)的“齊價(jià)合同”勉強(qiáng)維持其利潤關(guān)系。在盛宣懷主持下的輪船招商局,一直處于停滯時(shí)期。
1916年,盛宣懷去世,盛家為其舉行三十萬兩白銀的葬禮,留下遺產(chǎn)兩千萬兩白銀,超出李鴻章一倍之多,在這當(dāng)中,離不開盛宣懷后期將企業(yè)官僚化管理、霸占企業(yè)的人事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更加離不開他的巧取豪奪和營私舞弊。盛宣懷最初進(jìn)入輪船招商局時(shí),他是官員,并無股份,而后來他擁有招商局股票一萬一千股,占該局的全部股份二分之一,總值銀四百四十萬兩。1894年慈禧“萬壽慶典”,招商局報(bào)孝銀五萬余兩;1899年至1903年四年中,僅招商局因報(bào)效而從折舊項(xiàng)下墊支高達(dá)三十八萬余兩。因此,曾經(jīng)積極協(xié)助盛宣懷經(jīng)辦洋務(wù)的鄭觀應(yīng)也尖銳指責(zé)官督商辦,“名為保商實(shí)剝商,官督商辦勢(shì)如虎”。[22]
從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和明治維新比較來看,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后期1886年中國歲入八千一百多萬兩,至1894年還是八千一百多萬兩,其間各年的歲入雖有波動(dòng),但都是八千多萬兩,也就是說九年間經(jīng)濟(jì)是停滯不前的。1895年的《馬關(guān)條約》規(guī)定外國人可以在華設(shè)廠,清政府也就自然允許中國人自行設(shè)廠,于是民辦企業(yè)發(fā)展起來。至1903年國家歲入達(dá)一億多兩,比甲午戰(zhàn)前增收近兩千萬兩,再過五年至1908年更翻了一番,達(dá)兩億三千多萬兩,再過三年至1911年更達(dá)兩億九千多萬兩。比較前后的歲入,可以看到在以官督商辦為主要形式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停滯的,而商辦以后才快速發(fā)展的。
日本明治維新始于1868年。1880年開始私有化,1881年開始將官營和半官營的工廠絕大部分拍賣處理,國家大都是以極低的價(jià)格甚至是無常轉(zhuǎn)移給民間,投資62萬日元的長崎造船所,以9.1萬元轉(zhuǎn)讓三菱。投資59萬日元的兵庫造船局,以5.9萬日元轉(zhuǎn)讓給川崎。以22萬多日元購進(jìn)2000紗錠棉紡機(jī)10臺(tái),以無息十年償還的優(yōu)惠條件出售給民間,建立九所棉紡廠。將13艘輪船無償交給三菱,并給航路補(bǔ)助金,后又給18艘,使其與英美爭(zhēng)奪航路。民營企業(yè)由此成為明治政府殖產(chǎn)興業(yè)政策的中心內(nèi)容,從而使當(dāng)時(shí)的日本從“官督商辦”的狀態(tài)擺脫出來,實(shí)現(xiàn)了官商分離。后來中日兩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歷史遭遇,可以充分說明這種官商分離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三、結(jié)語:以史為鑒,中國現(xiàn)代的官商關(guān)系
商利與官權(quán)的角力,最終以盛宣懷為代表的官權(quán)取勝。唐廷樞和徐潤的出局與盛宣懷入主輪船招商局成為督辦,在招商局的發(fā)展歷程中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它標(biāo)志著招商局商辦色彩的下降和官辦色彩的加重,也成為官督商辦框架中輪船招商局此時(shí)從“商事商辦”轉(zhuǎn)向“商事督辦”標(biāo)志。
因此,導(dǎo)致唐廷樞和徐潤出局的深層原因是難以調(diào)和的官商矛盾,唐廷樞和徐潤是當(dāng)時(shí)中國民間經(jīng)營新式工商業(yè)的商辦代表,但是他們都是從經(jīng)濟(jì)利益出發(fā),與清政府利用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挽救其封建統(tǒng)治的政治目的不一致,兩者的合作漸漸走向破裂的邊緣,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商人是無力與清政府在政治上抗衡的,他們必須依附清政府。當(dāng)時(shí)風(fēng)氣已開,官辦和官商督辦已經(jīng)成為制約近代中國企業(yè)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清政府洋務(wù)當(dāng)局并沒有及時(shí)改弦更張,反而加速官化近代企業(yè),實(shí)行壟斷,這不能不遭到后人的譴責(zé)。
回顧歷史,反觀當(dāng)下,以史為鑒。歷史從社會(huì)中來,必須服務(wù)于社會(huì)。從清末算起來,中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迄今已轉(zhuǎn)軌了一百多年,但中國的企業(yè)家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權(quán)力的附庸,被斥為依附者群體。在《從顧雛軍到盛宣懷的共同困境》23中,作者將盛宣懷和前科龍集團(tuán)的董事長顧雛軍類比,兩人有很多的相同之處。他指出:“……李鴻章的智囊盛宣懷具有企業(yè)家的天才,但他本身又是大官僚,以兩者結(jié)合的身份,他成為中國近代企業(yè)家中的翹楚。今天顧雛軍所遭遇的一切責(zé)罵,盛宣懷幾乎一一嘗遍,如堂而皇之地將朝廷與股民投入輪船招商局的資金挪作他用,在掌控的所有企業(yè)中任用私人,又如私自涂改賬冊(cè),在朝廷和公司內(nèi)部用兩本賬;事實(shí)上,他主管的企業(yè)一再遭到戶部查核,如果不是李鴻章、張之洞等維新派官員大力扶持,就是十個(gè)盛宣懷也不頂事。……顧雛軍與盛宣懷面臨相同的困境:無法克服的體制性障礙,無法得到保護(hù)的產(chǎn)權(quán),以及輿論的普遍不同情。……顧雛軍商業(yè)帝國的倒塌,只不過證明了他一度擁有的保護(hù)并非根深蒂固。中國企業(yè)家為什么要依附權(quán)貴,甚至成為權(quán)貴階層?”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留下如下解答——將懲罰交給法律,將深入地反省留給自己,才是避免中國企業(yè)家悲劇的正道。
參考文獻(xiàn):
[1]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
[2]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
[3]葉亞康,顧廷龍.李鴻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葉亞康,顧廷龍.李鴻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朱蔭貴.從1885年盛宣懷入主招商局看晚清新式工商企業(yè)中的官商關(guān)系.史林,2008,(3).
[6]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續(xù)集.文海出版社,1978.
[7]鄭觀應(yīng).鄭觀應(yīng)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夏東元.盛宣懷傳.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07.
[9]夏東元.盛宣懷傳.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07.
[10]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1]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2]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3]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4]朱蔭貴.晚清輪船招商局的對(duì)外投資.中國論文下載中心,歷史學(xué)論文http://www.studa.net/lishi/060423/17111060-2.html.
[15]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16]陳旭麓,汪熙,陳絳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輪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7]陳旭麓,汪熙,陳絳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輪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8]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續(xù)集.文海出版社,1978.
[19]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
[20]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
[21]交通史·航政篇.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huì)編,1931.
[22]鄭觀應(yīng).盛世危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23]葉檀.從顧雛軍到盛宣懷的共同困境.中國企業(yè)家,2005,(18).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nèi)容請(qǐng)以PDF格式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