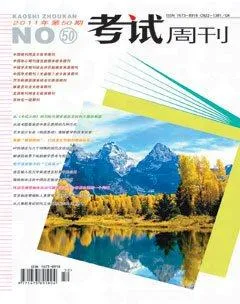“不負責任”的敘述者
摘 要: 莫言的小說《紅高粱》是具有新時期文學轉型意義的一部作品,它打破了傳統敘事的時空界限,表現出獨特的敘述視角和技巧,并開創了中國小說敘事的新紀元。本文從敘述主體和敘述視角兩個方面對《紅高粱》的敘述技巧作簡單分析。
關鍵詞: 小說《紅高粱》 敘述主體 敘述視角
《紅高粱》是具有新時期文學轉型意義的一部作品,它不僅描寫了“草莽英雄兒女,江湖恩仇血淚”的家族歷史,展現了人性的美麗與丑陋、善良與邪惡,更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傳統小說的寫作規范,以一種獨特而新穎的敘述方式開創了中國小說敘事的新紀元。莫言在談到《紅高粱》時認為:“如果《紅高粱》沒有這種獨特的人稱敘述視角的話,寫出來就會是一部四平八穩,毫無新意的小說。”①由此可見《紅高粱》有著獨特的敘述技巧,下面就從敘述主體和敘述視角兩個方面作簡單分析。
一、復調敘述——雙重敘述主體
在敘事學中,敘述主體是指文本中的說話者,也就是文本聲音的發出者,他不等同于寫作主體,因此,他不一定是單一的一個人,在很多敘事文本中,我們都能夠聽到兩個甚至更多的聲音。譚君強在其《敘事學導論》一書中相對于不同的側面,對敘述者作了這樣的區分:“根據敘述者相對于故事的位置或敘述層次,分為故事外敘述者與故事內敘述者;按照敘述者是否參與其所敘述的故事并是否成為該故事中的人物,分為非人物敘述者與人物敘述者;根據敘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分為外顯的敘述者與內隱的敘述者;根據敘述者與隱含作者的關系,分為可靠的敘述者與不可靠的敘述者。”②在《紅高粱》中,莫言將“爺爺的歷史”、“父親的歷史”與“我的現實”剪碎,重新拼貼,文中出現了“我父親”和“我”兩個不同的聲音,它兼具了故事外敘述者與故事內敘述者、非人物敘述者與人物敘述者的雙重身份,使寫作者“變得博古通今,非常自由地出入歷史,非常自由地、方便地出入我所描寫的人物的心靈,我也可以知道他們怎么想的,我也可以看到、聽到他們親身經歷過的一些事情”。③
“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后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奶奶披著夾襖,送他們到村頭。”④這是《紅高粱》的開頭。在整部小說中,故事的主體都是由“我父親”這個親歷者講出來的,比如羅漢大爺的死,奶奶的死,以及那場轟轟烈烈的膠平公路伏擊戰。“我父親”既是故事中的一個人物、一個參與者,又是一個講述者,他親身感受和經歷了戰爭的殘酷與血腥,并以孩童的口吻講述了那段慘烈的歷史。這樣的敘述不僅讓讀者覺得真實可信,而且使作為人物之一的“我父親”形象飽滿、栩栩如生。
從整部《紅高粱》來看,“我”是一個離開家鄉十余年、身上沾染了很多現代社會習氣的人,“我”對自己極其不滿,從而試圖尋找“家族的光榮圖騰和我們高密東北鄉傳統精神的象征”。⑤小說明確地說:“為了為我的家族樹碑立傳,我曾經跑回高密東北鄉,進行了大量的調查……”⑥因此“我”并不是故事中的一個人物,而是處于故事之外的一個敘述者,也即故事外敘述者或非人物敘述者,“我”應該是從現實的角度,通過史書或者幸存者去看那一段已經消逝了的歷史。然而小說曾寫一個光著屁股的男孩在“父親”的墓前放羊:“有人說這個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⑦在對祖輩故事的講述中,“我”甚至比親歷者“我父親”知道得還要多:“父親不知道我的奶奶在這條土路上主演過多少風流悲喜劇,我知道。父親也不知道在高粱陰影遮掩著的黑土上,曾經躺過奶奶潔白如玉的光滑肉體,我也知道。”⑧我甚至還知道父親還未出生時的很多事情,比如奶奶的出嫁,奶奶與爺爺的那段愛情,等等,仿佛我又成了故事中的一個人物。作者在小說中一方面似乎有意處處顯示“我”的存在,以強調作品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又以“我”的口吻描述了許多“我”不可能親見親歷的事,將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幻交融在一起,“我”成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敘述者,而作品也給人回味無窮的韻味。
二、敘述視角的越界——零聚焦敘事與內聚焦敘事的結合
“聚焦”這一術語是由熱奈特提出來的,他認為人們“混淆了其視點確定敘述透視的人物是誰,與敘述者是誰這一完全不同的問題,或者,更簡單地說,就是混淆了誰看與誰說的問題”。⑨受其啟發,人們普遍認為,敘事分析涉及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誰說”,這是確認敘事文本的“敘述聲音”與敘述者的問題;另一個是“誰看”,這是誰的視點決定敘事文本的問題。⑩聚焦指的是誰在作為視覺、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敘述信息透過誰的眼光與心靈傳達出來,在敘事文本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切受到誰的眼光的“過濾”,或者在誰的眼光的限制下被傳達出來。熱奈特將敘述聚焦分為三類,即無聚焦或零聚焦敘事、內聚焦敘事、外聚焦敘事。
在《紅高粱》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零聚焦敘事與內聚焦敘事的相互越界。“越界敘述是以突破原有某一敘述視角模式的習慣性、固定性使用帶來的陳舊感和局限性為前提而形成的。由于它是兩種或兩種以上敘述視角的越界產生的新視角,它在選擇越界點與越界幅度時完全可因敘述者的需要而靈活處置,因而它可兼有幾種敘述視角的優勢與消除其劣勢,從而能傳達某一原來敘述視角難以敘述的藝術世界的新體驗和新感覺”。{11}《紅高粱》中的內聚焦是指敘述是以“我父親”在膠平公路伏擊戰中的所見所聞所感為線索的,“我父親”既是敘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一個人物,就像一個取景框,一切外在的事件都是由“我父親”這個取景框過濾后進入敘述視野的。讀者借助于這個特定人物的眼光去“看”出現在他周圍的一切,同時,也以符合這個特定人物身份的特征行動并與故事中的人物展開交往。比如在打伏擊戰時,“奶奶”來送餅卻不幸被日本人打死的那一段敘述:
“飛落的米粒在奶奶臉上彈著,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開的雙唇間,擱在她潔白的牙齒上。父親看著奶奶紅暈漸退的雙唇,哽咽一聲‘娘’,雙淚落在胸前。在高粱織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睜開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了珍珠般的彩虹。”{12}
在這段敘述中,作為故事中的一個人物,“我父親”以孩子的視角親眼目睹了“我奶奶”的死,親身感受了生命與死亡,“敘述焦點與一個人物重合,于是他變成一切感覺,包括把他當作對象的感覺的虛構‘主體’:敘事可以把這個人物的感覺和想法全部告訴我們”。{13}同時,巴爾認為:“如果聚焦者與人物重合,那么,這個人物將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優勢。讀者以這一人物的眼睛去觀察,原則上將會傾向于接受由這一人物所提供的視覺。”與此同時,“這樣一個與人物相連的聚焦者……會產生偏見與限制”。{14}因此,在作品中,作者同時也采用了零聚焦的敘述方式來彌補這種偏見和限制。
“奶奶”中彈后,零聚焦全知敘述者展示了她的內心吶喊:“這就是死嗎?我就要死了嗎?再也見不到這天,這地,這高粱,這兒子,這正在帶兵打戰的情人?槍聲響得那么遙遠,一切都隔著一層厚重的煙霧。豆官!豆官!我的兒,你來幫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哪!天……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天,你既然給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寬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認為我有罪嗎?你認為我跟一個麻風病人同枕交頸,生出一窩瘸皮爛肉的魔鬼,使這個美麗的世界污穢不堪是對還是錯?天,什么叫貞節?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但我不想死……”{15}
通過上述內心透視,活脫脫展示了一個敢愛敢恨、性格鮮明的女性心靈。我們從中不僅可以看到她對生命的留戀、對現實幸福生活的不舍,甚至可以感受到她對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復雜的感受:悔恨,懺悔,無助,不滿和反抗,等等。而所有的這一切內心活動,作為親歷者“我父親”是無法知道的,因此,作者用了無所不知的敘述方式,以一個高于故事之外的人物的身份來敘述,他以上帝般的眼光深入到人物的內心,看到他們心中所蘊含的一切。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紅高粱》獨特而新穎的敘述手法,敘述主體與視角的變換,使故事時近時遠,時真時幻,結構具有極大的靈活性、人物血肉豐滿,使其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永久的魅力。
注釋:
①③莫言,王堯.莫言王堯對話錄.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155,139.
②譚君強.敘事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58.
④⑤⑥⑦⑧{12}{15}莫言.紅高粱家族.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1:1,8,3,51,56.
⑨⑩{14}譚君強.敘事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83,93.
{11}李江梅.敘述視角越界的“陌生化”創作效果.批評與闡釋·當代文壇,2007,(4):126.
{13}劉俐俐.中國現代經典短篇小說文本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7:2.
參考文獻:
[1]譚君強.敘事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2]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2.
[3]莫言.紅高粱家族.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1.
[4]劉俐俐.中國現代經典短篇小說文本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7.
[5]王耀輝.文學文本解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