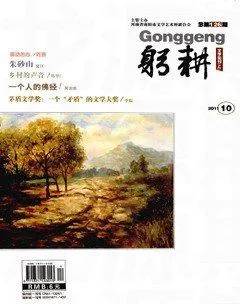理想和現實的距離
如果說我從《滿票》、《村魂》、《問天》認識了鞭撻農民劣根性、被文學界尊稱為“半個農民哲學家,半個農民思想家”的喬典運,那么我是從《遙遠的麥田》《玉米林隨風起舞》《無名橋》又認識了用浪漫的情懷感觸農民良知,追問人生價值多元化取向的西峽作家韓向陽。他用旁觀者的客觀冷靜、憑自己對傳統文化中儒、釋、道精神的獨特解讀,審視我們遠去和正生存著的時代,拷問他熟悉而又陌生的鄉村,用心靈的尺碼,不停地丈量農民理想和現實的距離,愛和恨的距離,生和死的距離,貴和“賤”的距離,貧和富的距離。
出身于農民家庭的韓向陽,對農民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所有作品中他即是農民中的一員,又與農民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他對農民看得清認得準,體貼得到位。他們的呼吸和心跳,他們骨子里浪漫的愿望及對社會美好的幻覺,虛空式的幻想,都被他一一道出,刻畫出基層農民外表的恭順和柔弱,內心的強大和高貴。作為鄉黨委書記,作為農民和政府溝通的橋梁,他也了解農民,喜愛農民,他總是站在農民的立場,體會官場游戲和解讀政策法規,用濃郁的鄉土情結,魔幻般的戲劇色彩表達了對農民深層的愛,對社會不良現象的冷嘲熱諷。
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有儒家積極進取的思想,建功立業的意識,都有飽滿的個性,無論卑微和高貴都能從善良的愿望出發,在社會磨難和不斷打擊中分化,選擇各自適應社會的方式獲得出賣良知的快樂或艱辛隱忍的生存;或在幻想破滅中死亡、或在寧折不彎中玉碎,或在猖狂中被仇殺,或在放蕩中瘋癲,或在平庸里行尸走肉郁郁而終。在各自具體生活過程中,他作品中的人物有道家對生命的樸素領悟,有意或無意追求生存個性適應社會,最終詮釋了人性被壓抑后的豐富,農民生存的艱辛和悲苦。無論你選擇怎樣的人生道路,無論選擇卑鄙或高尚的生活方式都無法擺脫失敗,逃脫冥冥之中的定數,被蹂躪被踐踏,成為在社會大潮面前無能為力的草。他們奮斗的人生歸結為佛家的南柯一夢,這種對農民積極進取意識辛辣式嘲諷最終指向社會深層或局部的不和諧。
《無名橋》作為長篇小說,和作者以前的作品相比較,時間跨度更大,他沒有選擇特定的環境去刻畫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在一個較長的歷史背景下去縱向和橫向地對比,去反復透視。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文革、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到目前盲目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作者以熟悉的大溝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農民的不同反應,成功的塑造一個個個性鮮明的人物,生動地再現了社會前進中的幸福和病痛。他始終站在弱勢群體一邊,客觀公正地再現了農民理想和現實的距離。
初始塑造人物形象,暗示人物命運中,可以看出作者受《紅樓夢》的影響頗深;對人物客觀不加個人評判的描述,讓被社會扭曲變形的人物命運自身說話,有博爾赫斯的影子對人物心理活動和外在環境的反復懸空式的詩意透視、夸張、渲染,又有卡夫卡小說的影子;從生存的當下寫人物,用人物的心理活動敘述人物過去及和過去相關聯的人物及事件,亦有意識流的影子。選擇一個中間點或接近人物命運終結的場景寫人物,回憶過去著重寫人物未來的命運,又酷似魯迅的寫法。使我們閱讀時面對時間大跨度和眾多的人物塑造不感到有脫節的現象,雖是長篇結構卻像中短篇小說一樣緊湊。人物栩栩如生站在眼前,目睹他們被紛紛倒下,我們無可奈何,束手無策,只有哀惋嘆息。作家韓向陽用無意義的形式寫出了有意味的社會內容,開辟了當代長篇小說的新途徑,顯得另類和時尚。這種具有前瞻性的探索,在某種意義上也填補了河南長篇鄉土小說的空白,為南陽文壇傳統小說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人物描述和事件敘述上,不時閃現著馬爾克斯式的把愛埋在心底外表淡漠的幽默、調侃,博爾赫斯式的思想閃爍和詭秘,卡夫卡式的虛幻的環境描寫映襯、烘托,加速人物內心情感異化的荒謬,喬典運式的對農村鄉里俗語的地道的雅化、淳化和戲虐,行者語言的勁道和恣肆,周同賓語言的親切、低調和入心,不激不歷,像八跌河水,時而不溫不火,時而噴珠吐玉。橋無名水有名,亙古的流水、緩緩的水流,目睹大溝村農民的愛恨情仇,成功再現了農民理想和現實的距離,作者的希望和失望的距離。
《無名橋》寫出了作者的無名淚。中國歷代農民無法實現理想和抱負的淚,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淚,弱勢群體的淚,忍辱負重的淚。作家韓向陽是繼喬典運之后,為西峽文壇乃至南陽文壇,增添了一份特有厚重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