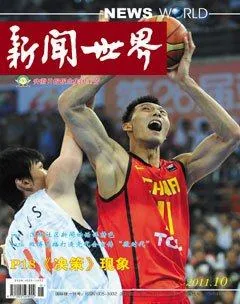胡政之的“文人論政”思想對《大公報》的影響
【摘要】中國公共領域的發展一直和報紙休戚相關。20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因其所處戰爭環境,公共領域開始建設發展,這時期《大公報》發揮了重要作用,而胡政之的“文人論政”思想一直推動著《大公報》的發展,使之獨具特色。
【關鍵詞】胡政之 文人論政 公共領域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正陷于水深火熱之中,國家岌岌可危。這個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感到將國家及人民解救出來的重大責任。如何將他們心中對國家的期望加以實現?報紙此時充當了最好的詮釋的角色。當然,更重要的是,報紙在這里成功地構建了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使得不少思想深入人心。而在近代中國報紙中,《大公報》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一頁。大批的知識分子和文人這時以《大公報》等報紙為主要陣營,不斷獻言獻策,監督當時民國政府,使之政策不斷完善。也因這一公共領域,國人能夠更深入理解整個社會,身邊所處環境,進而參與這一公共領域,發表自己的看法。《大公報》此時發揮的作用正是哈貝馬斯所描述的公共領域的功能:“一則討論公共事務,產生公眾輿論,形成公共意見,進而影響公共決策;二則對公共權力進行監督和批評”。①
提到《大公報》,就不免想起胡政之。一般說法是吳鼎昌負責資本,張季鸞負責文章,胡政之負責經營,這個說法基本中肯。《文匯報》前總編輯、著名老報人徐鑄成曾說:“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采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于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于籌計,擘畫精致,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文、武、昆、亂不擋。后起的如成舍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②老大公報人陳紀瀅也曾說:“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創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的,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③
胡政之早期留學日本,學習法律。回國后,在他第一次主持《大公報》期間,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17年,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誓師反對張勛復辟,胡政之以記者身份獨家采訪;二是1919年,他作為唯一的中國記者采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勝國舉行的巴黎和會,這也是中國記者第一次采訪重大的國際事件,使他成為“采訪國際新聞的先驅”,也是他終生津津樂道、引以自豪的一件事。④此時的胡政之已經認識到中國人缺乏世界知識,這是中國社會進步遲緩的重要原因,從他進入新聞業早期開始,他就非常重視對中外關系、國際形勢的報道、評論。
1926年9月1日,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三人合作接辦《大公報》。胡政之講到他和吳鼎昌,張季鸞創辦《大公報》的初衷是為了“文人論政”。雖按著商業經營,但仍保持著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中國的公共領域從一開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識分子為核心,跳過歐洲曾經有過的文學公共領域的過渡階段,直接以政治內容作為建構的起點,公共空間的場景不是咖啡館、酒吧、沙龍,而是報紙、學會和學校。在風格上缺乏文學式的優雅,帶有政論式的急峻。這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領域,此時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在摸索著救國救民的道路,無論是資本主義道路還是共產主義道路,他們都在積極地表達著自己的想法、意愿,希望國家能夠富強,抵御外敵。但在國共之爭日趨激烈之時,報紙的公共輿論受到很大的威脅,很多報紙難以確保甚至失去其公正性,而日趨黨派化、政治化。胡政之卻依然保持著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報紙“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愿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也正因為如此,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大公報》成為中國民間輿論的第一大報。胡政之自己也曾說:“這張報紙的影響不下于一個政黨,你看辦報是不是很有意義?”此時的《大公報》走上了鼎盛時期,將“文人論政”發揮到了極致。1941年5月,《大公報》榮獲了具有世界聲譽的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密蘇里大學教務長馬丁寫信給胡政之說:“貴報今年被推得獎,端為一外國之自由的報紙,在其悠久的過程中,對于公眾具有優異的貢獻。吾人此項決定,兼得深知貴報偉大貢獻之美國記者的一致贊許。”
新記《大公報》三位創辦人中,吳鼎昌欲把辦報作為進入政界的途徑,而張季鸞可能骨子里還是屬于大資產家的知識分子,后來和蔣介石走得非常近,稱兄道弟,異常熱乎,還想象著抗戰勝利后當個駐朝鮮大使,經常游走于達官顯貴之間。由此引發了《大公報》的公正性危機,也被共產黨罵“小罵大幫忙”。胡政之既沒有吳鼎昌的把辦報作為進入政界的途徑,也沒有張季鸞的“報恩”、“國士”情結,在三人中,他與蔣介石發生關系最晚。胡政之曾言:“我與社會上層人物和達官權貴雖多交往,但只有公誼而無私交,所談皆國內外時勢大事,從不涉私,這樣對于事業是有利的。”⑤難怪人人夸他謹慎、理性,采訪過不少要人,但始終不卑不亢,兢兢業業地為新聞事業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構建當時比較公正的公共領域,讓國人真正了解當時國家實際情況,而非偏向哪一政黨。據《1926年至1949年的〈大公報〉》一文說,“胡政之同蔣介石只是在1935年曾經一度晤談,還沒有深入的接觸……1938年8月胡自上海南下,去創刊香港版。為準備退路,1941年3月又創刊桂林版。約有五六年的時間,他沒有和蔣介石接觸……胡政之同蔣介石發生關系,是在張季鸞死了以后。胡政之對蔣介石的態度和張、吳迥然不同……胡政之和蔣介石的關系,遠不如張季鸞之密切。私下談話,胡對蔣常有尖刻的評語。這也是胡、張之間的矛盾之一。”據徐鑄成說,胡生前,曾屢次對張的政治態度表示不滿,認為張太靠攏蔣,說“辦報應該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據其子胡濟生回憶,1941年,張季鸞病中給胡政之寫信,說“大公報只有緊隨著蔣介石才有前途”,胡政之“大不以為然”,他說“吳、張可以不辦大公報,而夫公報必須辦起來,因為它是社會事業”。張季鸞去世后,《大公報》批評政府的言論更加激烈。蔣介石每每念及張,原因是“胡太不聽話”。抗戰勝利后,胡政之要求廢除戰時新聞檢查制度,呼吁和平,反對內戰,之后在國共兩黨斗爭中鼓吹“第三條道路”。⑥此時的胡政之心中依然充滿著自由主義思想,由始至終的貫穿于主持《大公報》的過程中。司徒雷登曾想物色“民主個人主義者”來取代蔣介石,準備了洋房汽車,讓胡政之出任行政院長。胡政之一心想著自己的新聞事業,不離不棄,毫不猶豫地跑回《大公報》南京辦事處睡帆布床。國民黨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絕。在胡政之看來,報紙是中國文人論政的重要陣地,是千秋萬世的大事業,報紙必須保持其獨立性,報紙的報道空間越大,政府才能越有作為,社會才越安定。一個人、一個組織不可能把一切正確思想集于一身,只有所有人的積極性發明性被調動起來,國家才會治理得更好。報紙等消息媒體正好可以起到這樣一種中介作用。
一份報紙的定位,主要決定于報紙的主持人。胡政之曾說過:“中國素來做報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商業性的,與政治沒有聯系,且以不問政治為標榜,專從生意經上打算;另一種是政治性的,自然與政治有聯系,為某黨某派作宣傳工作,但是辦報的人并不將報紙本身當作一種事業。等到宣傳的目的達到以后,報紙也就跟著衰歇了……”,“但自從我們接辦《大公報》以后,為中國報界辟了一條新路徑。我們的報紙與政治有聯系,尤其是抗戰一起,我們的報紙和國家的命運幾乎聯在一塊,報紙和政治的密切關系可謂達到了極點。但同時我們仍把報紙當作營業做,并沒有和實際政治發生份外的聯系。我們的最高目的是要使報紙有政治意識而不參加實際政治,要當營業做而不單是大家混飯吃就算了事。這樣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報紙真能代表國民說話。現在我們還沒有充分做到這種'代表國民說話'的資格,但只要同人努力,這個目的總會達到的。”⑦
胡政之滿心希望報紙最終能夠“代表國民說話”,構建不包含政治之外但仍談政治的真正的公共領域。《大公報》在其主持之時,基本上都保持著公正性,不偏不袒,實實在在地“文人論政”。雖無法實現他心中的“憲政夢”,但他的辦報目的已基本達到。
參考文獻
①韓敏敏:《中國報刊與公共領域的構建》,《青年記者》,2010(9)
②徐鑄成:《報海舊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③陳紀瀅:《胡政之和大公報》,[M].香港: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91
④《胡政之:開創百年報業“新路徑”》,《百年報人傳奇歷史》
⑤⑥張湛蘋,《胡政之新聞思想研究》,[D].西北大學,2008
⑦1949年4月15日《大公報》上海版,《文史資料選輯》97輯,P104
(作者: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