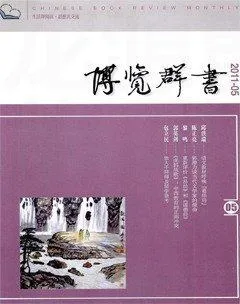《紅巖》作者排名的變奏
就像如今通俗歌壇上的“羽·泉”、“鳳凰傳奇”等形形色色的組合,“羅、劉、楊”也是一個由幾個人組合起來的工作小組,不過他們的工作內容不是流行歌曲,而是在群眾大會上做政治報告和寫作,三個人的全名是羅廣斌、劉德彬和楊益言。
這個組合中的羅廣斌和楊益言,有點歲數的人都很熟悉,他們的名字和上千萬冊的暢銷書《紅巖》一起在中華大地上曾經廣為流傳。劉德彬,這個組合中的重要一員,卻在相當程度上并沒有走到臺前,雖然在重慶和四川,他的名字廣為人知;但在更為廣大的讀者當中,他的名字并不為人所知。研究當代文學的專家們能夠隱隱約約地知道還有一個劉德彬。1963年5月13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署名羅廣斌、楊益言的文章《創作的過程學習的過程——略談(紅巖)的寫作》中提到:“1956年……市委給了我們三個人以半年時間,分頭寫出了五六十萬字的書面材料。”并且也說到了劉德彬中途“單飛”的原因:“最后幾次改寫和定稿時,劉德彬同志因工作原因未能參加。”先不說究竟是什么“工作原因”使得劉德彬沒有參加最后幾次改寫和定稿,而說說“最后幾次改寫和定稿”前后的事情。因為這個“最后幾次改寫和定稿”也就是從1959年2月到1961年12月兩年多的時間而已,而在這兩年多之外的更多時間里,劉德彬的工作和生活是和羅廣斌、楊益言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只不過隨著時間的不同,他們三個名字出現時的排序是不同的。《紅巖》出版之前一直是“羅、劉、楊”,《紅巖》出版之后就微妙地變成了“羅、楊、劉”。除此之外,在不同的情境中,也有“劉、羅、楊”出現在人們面前。這些三個姓氏之間的不同排列看似微不足道,其實卻大有深意。
“羅、劉、楊”的產生
“羅、劉、楊”是自然形成的一個工作組合。1949年11月27日,距離重慶解放還有三天,國民黨當局對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200多個政治犯實行了大屠殺,這就是日后著名的“11·27大屠殺”。雖然經歷了慘烈的火焚和槍擊,但大屠殺過后,兩處看守所仍然有幾十人僥幸生還。在這些人當中,就有身為共產黨員而又被組織信任的羅廣斌和劉德彬。12月初,他們兩人到“脫險同志聯絡處”報到后,隨即被安排到“重慶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追悼會”組織部,開始進行一系列和“大屠殺”善后有關的工作。其中一項工作是編輯一本對大屠殺進行全面介紹的公開出版物《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蔣美特務重慶大屠殺之血錄》。1950年2月,這項工作進行到后期,劉德彬介紹他高中同學楊本泉的弟弟楊益言參加這個特刊的校對工作。這是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一起工作的開始。烈士追悼會結束后,羅廣斌、劉德彬一起到青年團重慶市委工作,隨后,經羅廣斌、劉德彬等人介紹,楊益言也被安排到青年團重慶市委。“七一”前夕,重慶《大眾文藝》雜志發表了署名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圣潔的血花——獻給九十七個永生的共產黨員》,這是他們三人第一次共同署名發表作品。不過,“羅、劉、楊”組合被人所熟悉并不是因為這篇作品,而是此后他們一起在機關、學校、工廠做過的不計其數的報告會。據當年重慶團市委負責人廖伯康回憶:“其中羅廣斌作的報告最受歡迎,其次是劉德彬,再其次是楊益言。”作為從敵人的神秘魔窟中僥幸生還的當事人,他們的報告會在群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尤其是毅然背叛傳統世家加入革命隊伍而且博學多才、善于言辭的羅廣斌,更是成為群眾崇拜的傳奇英雄。
除了做報告,他們繼續以三個人的名義發表作品。由于出版社的約稿,他們先后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紅旗飄飄》叢刊上發表了短篇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出版了中篇的單行本《在烈火中永生》。這兩個和此前發表的《圣潔的血花》一樣并不算成熟的作品卻同樣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由于出版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開始,《在烈火中永生》成為共青團向廣大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教材,發行量達到350多萬冊,《北京晚報》還進行了全文轉載。但早在《在烈火中永生》出版之前的1956年10月,他們三個人就向市委申請了半年的創作假,開始了把他們的革命經歷寫出來的嘗試。這個嘗試的結果就是1957年春天完成的幾十萬字的說不清是小說還是報告文學的一摞子打印稿《錮禁的世界》。“羅、劉、楊”變成了“羅、楊、劉”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他們三人在前一年完成的這沓子并不成熟但是題材重大的稿子就成為各級作協完成躍進指標的重要砝碼,同時,也引起了發表過他們稿子、因此對他們有所了解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們的注意。由于中青社的重視和四川省作協主席沙汀的過問,兩年前完成的、保存在重慶市作協的那個《錮禁的世界》有了起死回生的機會。不過,劉德彬卻與這次機會失之交臂。1959年1月,由于“工團主義分子”、“嚴重右傾”、“攻擊肅反擴大化”等三條“嚴重錯誤”,劉德彬被劃為“中右”。2月,市委研究書稿修改工作時,就沒有同意讓剛剛受過處分的劉德彬繼續參加。雖然沒有正式參加修改,但在羅廣斌他們第二稿的寫作過程中,劉德彬也經常抽時間和他們一起討論、研究。1959年底,《錮禁的世界》修改本出來了,作者署名仍然是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1961年5月,《錮禁的世界》第四稿定稿前夕,羅廣斌曾向市委請示兩個問題:書名怎么定?作者是否仍署羅、劉、楊?市委書記任白戈指示:書名可定為《紅巖》;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李唐彬指示:“劉德彬暫不署名,以免被動。”雖然在《紅巖》出版的1961年重慶市總工會機關支部大會就撤銷了對劉德彬的處分,但劉德彬的名字還是和《紅巖》無緣。雖然沒有署名,但也僅僅是沒有署名而已。在重慶,人們還是把他們三個人當作一個小集體來看待的。1962年,在羅廣斌的要求下,他們三個人一起調到重慶作協,成為專業作家。《紅巖》的大筆稿費也是他們三個人共同使用的。廖伯康曾回憶:“他們常常是同吃、同住、同用,我曾和他們開玩笑說:‘你們現在已經在過共產主義生活了。’”
雖然還是那個三個人的工作組合,但是《紅巖》出版后,他們之間的排名順序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很多時候和場合,劉德彬從排名第二變成了排名第三。如1962年11月在《人民畫報》發表的《血的記憶》,署名就是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
“劉、羅、楊”與“劉、楊、羅”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劉德彬排名第一的時候。比如,1957年2月28日-3月3日《重慶日報》連載的《云霧山》,署名為“劉德彬、羅廣斌、楊益言”;1957年4月4、5、6日在《重慶日報》連載的《江竹筠》署名也是“劉德彬、羅廣斌、楊益言”;1957年5月1、2日在《四川工人報》連載的《工運書記》署名是“劉德彬、羅廣斌、楊益言”。這些在報紙發表的文章就是他們利用半年的創作假剛剛在重慶南溫泉完成的《錮禁的世界》中的片段。當然,除了這些劉德彬排名第一的文章,他們在《中國青年報》上也發表了《小蘿卜頭》、《江姐在獄中》等,署名則為“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很顯然,那些署名時劉德彬排在前邊的文章是由劉德彬執筆寫作的,其它的文章則是由羅廣斌執筆寫作的。當年他們三個人在南溫泉寫作時是按照各自熟悉的題目分工合作的,署名雖然是三個人,但具體到某一段,實際寫作的肯定是某一個人。人們曾經把這些確實為劉德彬所寫的段落和后來出版的《紅巖》中的相應段落進行對讀,發現兩者基本上是一致的。的確,《紅巖》在1959年到1961年之間的幾次大修大改中,經過無數把關者的指點,和最初完成的《錮禁的世界》相比肯定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這些沒有多少改動的段落只能說明劉德彬當年執筆的那些段落是相對成熟的。
再比如,《紅巖》出版兩年后的1964年1月8日這一天,由羅廣斌執筆分別給中青社文學編輯室的“道隆、張羽、維玲”也即編輯部主任闕道隆和編輯張羽、王維玲以及北京電影制片廠的“水華、于蘭”寫了兩封信,這兩封信最后的落款都是“德彬、益言、廣斌”。相比之下,1963年12月18日,由楊益言執筆給“水華、于蘭”的一封信的落款署名則是“羅、楊、劉”。在1月8日給中青社編輯們的信中談到羅廣斌和劉德彬的身體情況時也是先說劉德彬,后說羅廣斌:“劉、羅健康情況較差,不斷治療。目前劉的高血壓已經穩定,尚能堅持工作;羅血壓未穩,心臟略受影響,近來均在家休養。”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劉德彬由于錯誤的政治分類被強制解除了修改小說的工作權和在出版后的小說上署名的著作權,但在《紅巖》出版后,由于羅廣斌的努力,他依然參加了三人組合的各種活動:搜集素材,準備繼續創作以地下斗爭和監獄斗爭d95475d0a8ff12ce7a8ff1708ab66e4882f3fce81cac0c7b8ba16f6ec7ab515e為主題的小說;到北京幫助北影主創人員寫作電影劇本;在作協黨組領導下,總結小說《紅巖》創作的成功經驗,等等。由此也可以看出,雖然羅廣斌是他們三人組合中統籌全局的核心人物,但他在自己執筆的書信中還是很得體地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另外,在他看來,劉德彬雖然沒有在《紅巖》上署名,但他畢竟還是這個組合中的老大哥。或者說,正因為有過實際貢獻的劉德彬沒有能在《紅巖》上署名,所以才更應該給實際上是受了冤枉和委屈的劉德彬以某種形式上的補償。
羅廣斌在“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后的1967年墜樓身亡,從此,這個三人組合真正結束了它的使命。但是,為了給死難的戰友羅廣斌恢復名譽,也為了維護他們的共同的政治資本《紅巖》的清白,楊益言和劉德彬一起到革命中心北京上訪申訴、四處活動。這個時候,包括楊益言本人都是把劉德彬當作是《紅巖》的作者之一來看待的。“四人幫”被打倒后,政治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中青社計劃再版《紅巖》。1977年7月底,受中青社的邀請,楊益言到中青社又一次修改《紅巖》,但這時羅廣斌的政治問題還沒有解決,劉德彬當年遭遇的因為政治原因不能署名的情形有可能再一次落在羅廣斌身上。那樣的話,《紅巖》的署名就會剩下一個唯一作者楊益言。后來,由于羅廣斌遺孀胡蜀興的努力申訴和當時的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安排,羅廣斌的問題才很快得到解決。《紅巖》署名沒有再發生更大的變化,但似乎也固定了十幾年前造成的那個找不到被告的歷史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