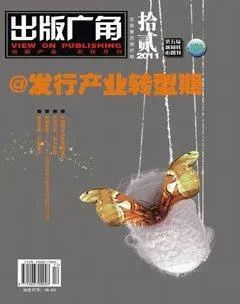以點帶
2011-12-29 00:00:00宋志軍
出版廣角 2011年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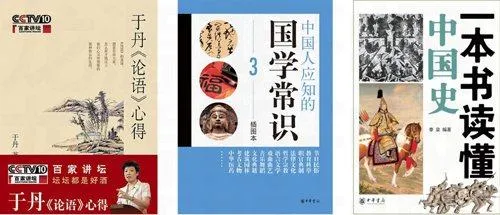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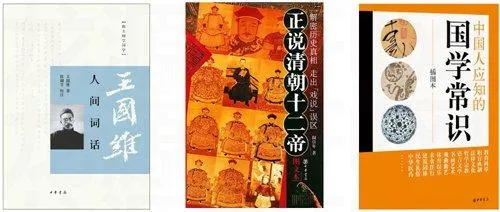
中華書局自進入普及讀物市場后,摸索了十幾年的時間,而真正讓讀者記住并得到市場認可的一個轉(zhuǎn)折點是2004年。這一年,我們有了專門的機構(gòu),即成立了中華書局大眾讀物工作室;有了明確的方向,即圍繞中華書局已有的品牌優(yōu)勢,做面向大眾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普及讀物;也有了標志性產(chǎn)品,就是以閻崇年著《正說清朝十二帝》為代表的“正說”系列圖書。
“中華書局”金字招牌與“百家講壇”強勢結(jié)合
“正說”對于我們,有比碼洋和回款更重要的意義:第一,它為我們打開了渠道,贏得了銷售商的信任;第二,它讓我們看到,與電視結(jié)合,是產(chǎn)生暢銷書的捷徑,因此相繼有了與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和北京電視臺等一些強勢媒體的合作;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它讓我們看到了品牌的力量以及依托品牌可以創(chuàng)造的價值!以前我們一直強調(diào)“中華書局”四個字是金字招牌,卻不知道怎樣把它變成真正的市場價值,是“正說”系列圖書讓我們看到這四個字的含金量。
閻崇年先生為什么從十幾家出版社中單單選擇了中華書局?當時的中華書局談不上有什么營銷能力,甚至不知道還有“簽售”這回事;當時版稅相對較低,首印數(shù)也只有區(qū)區(qū)5000冊;而最終讓我們拿到這部書稿的主要原因還是“中華書局”這四個字。作為歷史學(xué)者,閻先生是有中華情結(jié)的,“中華書局”這四個字,會讓他覺得與自己的作品相稱,也會讓他心里踏實。
品牌的優(yōu)勢,讓我們在圖書運作的最上游贏得了作者。這就是先輩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資產(chǎn),也是我們在市場競爭中的比較優(yōu)勢。有了這個優(yōu)勢,使我們能夠與最具市場號召力的一流作者合作,使我們能夠為市場和讀者提供一流的作品。好的作品會拓寬我們的銷售渠道,店面的需求又會反過來促進我們豐富營銷手段、提高營銷水平。與之適應(yīng),我們內(nèi)部的運作流程、人員配備也都要做出相應(yīng)調(diào)整。這是一個非常良性的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隊伍得到了鍛煉,我們的產(chǎn)品贏得了口碑和可觀的銷量,也使越來越多的作者不僅對我們的品牌認同,也認可了我們的市場運作能力,愿意與我們合作。因此,在閻先生之后,又有了我們與于丹女士的合作,在于丹之后又有了與馬未都先生的合作。
中華書局大眾圖書板塊從2004年初建時的年發(fā)貨碼洋不足500萬,幾年內(nèi)實現(xiàn)了迅速遞增和壯大,2300萬,5600萬,直到2007年接近一個億。如果要把這幾年最值得拿出來的經(jīng)驗與大家分享的話,那就是,我們找準了定位,找到了自己在市場競爭中的比較優(yōu)勢所在。同時,我們也抓住了一個難得的機遇,這就是以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為代表的電視講座類節(jié)目的迅速崛起。一個優(yōu)質(zhì)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出版品牌與一個優(yōu)質(zhì)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傳播平臺相結(jié)合,這就是一個接一個暢銷書產(chǎn)生的全部奧秘。
后“百家講壇”時代,以產(chǎn)品線實現(xiàn)累積式增長
當成功模式可以不斷復(fù)制的時候,危機就來臨了。首先是幾乎所有的出版機構(gòu)都開始盯上了《百家講壇》這個資源,激烈的競爭自然抬高了準入價格,使得出版風(fēng)險加大,作者也開始嘗試不同的出版者;其次是與任何一個電視節(jié)目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一樣,《百家講壇》的輝煌是因為它領(lǐng)了風(fēng)氣之先,隨著各地各電視臺同質(zhì)化的文化講座不斷推出,《百家講壇》也漸漸回歸到一檔文化類節(jié)目的常態(tài)。所以從2008年之后的幾年,對于我們來講,是一個比較艱難的轉(zhuǎn)型期。沒有了超級暢銷書,使我們經(jīng)歷了一段碼洋下降、利潤下滑的日子,我們不得不做出調(diào)整,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xùn),逐步明晰了在“后百家講壇時代”所該走的道路。這條路簡而言之就是:圍繞品牌優(yōu)勢,堅定已有的出版方向不動搖,以暢銷書為龍頭,以常銷書為基礎(chǔ),不僅追求單本書的銷量,更強調(diào)產(chǎn)品線的概念,做結(jié)構(gòu),做規(guī)模,實現(xiàn)累積式增長。
這可以稱為我們第二個階段的產(chǎn)品發(fā)展戰(zhàn)略。制定這樣的戰(zhàn)略,一方面是要擺脫對于暢銷書的過分依賴,解決書局大眾圖書板塊大起大落、基礎(chǔ)不牢的問題;另一方面仍然基于自己和競爭對手的比較,仍然是立足于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并希望努力擴大這個優(yōu)勢。
以暢銷書的“點”帶動品牌的“線”和“面”
現(xiàn)在出版業(yè)的基本態(tài)勢,可以用“三化”來概括:即“出版社集團化” “文化公司主流化”和“出版物數(shù)字化”。而這三方面無不對傳統(tǒng)的出版社和傳統(tǒng)的資源運作方式帶來了沖擊和挑戰(zhàn)。
數(shù)字出版使我們安身立命的古籍資源面臨著維權(quán)的困難和流失的風(fēng)險,是我們未來命運的最大威脅。出版社集團化,加劇了地方割據(jù),我們這樣沒有“根據(jù)地”的出版社,實際上生存空間被擠壓,我們只能靠品牌和產(chǎn)品說話;而我認為,在大眾出版領(lǐng)域,目前真正對體制內(nèi)品牌社構(gòu)成現(xiàn)實生存威脅的,是體制和機制更具活力的文化公司。我所說的文化公司不僅指像北京磨鐵圖書有限公司、新經(jīng)典文化有限公司等民營公司,也包括體制內(nèi)的出版集團在異地成立的文化公司,如北京貝貝特、接力出版社北京中心等,還包括原來被我們稱為“二渠道”的文化公司加盟出版集團后新成立的實體。
數(shù)量龐大的文化公司(包括個體書商),在我們看來,非常具有進攻性——從上游以高版稅搶奪作者資源,在下游以低折扣搶占貨架資源,其觸角之長,反應(yīng)之快,運作手段之靈活,相對于我們確實有不少先天優(yōu)勢,在市場競爭中也讓我們吃了一些苦頭。比如當年我們推出“正說”系列圖書,《正說清朝十二帝》之后,后續(xù)產(chǎn)品沒有及時跟上,結(jié)果許多跟風(fēng)之作反而出在了我們前面,使整套書的銷售碼洋大打折扣。在目前情況下,如果我們與文化公司比拼速度,顯然是取敗之道。所以我們在競爭中實際上采取的是以慢搏快、以長搏短的策略。
首先是以陣地戰(zhàn)對游擊戰(zhàn)。雖然現(xiàn)在一些比較好的文化公司開始有了明晰的出版方向和出版板塊,但還有大量文化公司依然利用自身船小好調(diào)頭的特點,隨著利益驅(qū)動不斷調(diào)整出版方向,或者說,基本沒有方向。而我們是有方向的,并且這個方向是緊緊依托于品牌優(yōu)勢的。我們做的是長線,做的是積累,做的是質(zhì)量,做的是口碑。我們不求速勝,而是著眼于未來。
其次是強調(diào)做有效品種。我們所說的有效品種,不僅要能帶來短期內(nèi)的經(jīng)濟效益,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我們確定的出版方向,在質(zhì)量上能立得住,最好還能留得住。這樣的品種才能形成真正的積累,即便一時做不到很大的規(guī)模,但只要不間斷、不放棄,終能有所成。
第三是謀定后動。我們既然在速度上沒有優(yōu)勢,那就要在計劃性上做得更出色些。事實上,這些年來,我們有不少項目因為后續(xù)產(chǎn)品跟進速度上不去,最后慘遭跟風(fēng),事倍功半。所以我們越來越強調(diào)準備充分了再出手,對于可復(fù)制性比較強的叢書、套書,我們一般是有了后續(xù)產(chǎn)品的準備才推出,這樣就減少一些被動。
第四是借鑒競爭對手的思路,并超越他。通過研究開卷數(shù)據(jù)等圖書排行榜,我們發(fā)現(xiàn)總有一些書,作者不知名,出版社無品牌,內(nèi)容編排也不怎么專業(yè),編校質(zhì)量也算不上上乘,也看不到多少書評、營銷活動,但監(jiān)控銷量一直不少,并且持續(xù)相當長時間。只能說,是它的編輯思路適應(yīng)了大眾的需求。那對我們來說,學(xué)習(xí)其思路并不困難,如果再加上我們的品牌、加上我們的作者和編者更加專業(yè)和敬業(yè),那是不是就能青出于藍而超越它?其實,我們所做的“一本書讀懂”系列和“中國人應(yīng)知的常識”系列圖書,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我們通過同類書的持續(xù)熱銷看到了大量讀者“快餐式閱讀”的需要,因此有了上述選題的創(chuàng)意。“一本書讀懂”采用的是“知識濃縮”的辦法;“中國人應(yīng)知的常識”采取的是碎片知識重組的方式,兩者都可以滿足大眾這種功利性、碎片式閱讀的需要。因此,一投入市場就受到讀者的歡迎,其中,《一本書讀懂中國史》面世兩年多銷售近10萬冊;《中國人應(yīng)知的國學(xué)常識》推出一年半的時間就銷售53000冊。在當今的市場狀況下,這兩本書也可以算做是暢銷書或者準暢銷書了。這些書更大的好處是,策劃編輯在運作中發(fā)揮了主導(dǎo)作用,不受制于作者,也不需要更多的營銷配合,可以較快形成規(guī)模。比如一本書讀懂系列,目前已經(jīng)有17個品種,發(fā)貨碼洋1000多萬,可以說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產(chǎn)品線。若干個這樣的產(chǎn)品線組合起來就形成一個眉目清晰、方向明確的出版板塊。
第五是利用品牌優(yōu)勢和專業(yè)優(yōu)勢,爭奪進入公共領(lǐng)域的出版資源。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對于民國時期國學(xué)大師經(jīng)典著作的整合出版。對于這部分著作,因為免費、因為經(jīng)典,歷來為出版者所垂青。比較著名的有東方出版社的“民國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書系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萊閣叢書”。其他各種名目的出版物就不計其數(shù)。單以《人間詞話》為例,現(xiàn)在當當網(wǎng)上銷售的版本就不下100個。同質(zhì)化如此嚴重,那我們?yōu)槭裁催€要進入這個領(lǐng)域呢?因為我們看到了自己的競爭優(yōu)勢。
首先是品牌支撐。除了原有品牌優(yōu)勢得到學(xué)界的廣泛認可外,這幾年《正說清朝十二帝》《于丹論語心得》《馬未都說收藏》等暢銷書的熱銷以及媒體的廣泛宣傳,實際上把中華書局的品牌影響擴大到了大眾這個層面,這是其他許多競爭者不具備的。
其次是市場空間。同類書更多的是在“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家庭典藏”上做概念,于是我們打算在大眾經(jīng)典學(xué)習(xí)上下工夫,以“跟大師學(xué)國學(xué)”作為叢書名。在書目選擇上,把《經(jīng)典常談》《書畫淺說》《文字學(xué)常識》《國學(xué)常識》等大家講常識的讀物列入其中,于是做出來一套有自己特色的大師經(jīng)典讀物,最終得到了市場的認可。
第三是品質(zhì)提升。我們利用專業(yè)優(yōu)勢,在版本選擇、內(nèi)容增值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幾乎每本書都增加了相關(guān)內(nèi)容,同時參考同類書定價,做到優(yōu)質(zhì)、增值但相對廉價。從2009年5月國學(xué)大師經(jīng)典讀物推出第一輯開始,到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做了三輯,共24本,發(fā)貨碼洋超過了500萬。
這是我們發(fā)展的第二個階段,也是目前所處的階段。暢銷書是我們努力爭取的,但它只是我們整個出版板塊里面最活躍的“點”,我們更大的力量在做“線”和“面”,這也是我們長久發(fā)展更為重要的基礎(chǔ),而這同樣是基于我們在市場競爭中的比較優(yōu)勢做出的戰(zhàn)略選擇。
但在市場競爭中,優(yōu)勢和劣勢是可以逐漸轉(zhuǎn)化的。我們這些大社老社有品牌優(yōu)勢,但一些做得比較好的文化公司的品牌意識也越來越強,甚至可以說重視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比如磨鐵,他們從多年前就著力宣傳磨鐵這個品牌,而有意淡化出版物所掛的出版社的名字。我們這些大社老社有自己的出版方向和多年來的堅守,一些做得比較好的文化公司也早就放棄了游擊戰(zhàn),開始打陣地戰(zhàn)。比如新經(jīng)典,現(xiàn)在就有四個大的出版板塊:外國文學(xué)、華語文學(xué)、兒童繪本、財經(jīng)勵志,每個板塊都做得非常好。品牌優(yōu)勢、專業(yè)優(yōu)勢需要好的產(chǎn)品和相當數(shù)量的品種來支撐,沒有這些,品牌就會空心化,我們就會被邊緣化。我們的競爭對手是咄咄逼人的,其成長速度之快令人震驚。磨鐵也好,新經(jīng)典也好,共和聯(lián)動也好,成立的時間都不超過十年,但他們的碼洋規(guī)模已經(jīng)超越了我們。為什么他們能夠如此快速地成長,而我們沒有做到?他們的優(yōu)勢,比如說公司化運作體制,可否被我們借鑒并超越?我想,這是我們必須想清楚并且必須馬上著手做的事情。
現(xiàn)實的市場留給我們的空間確實越來越小,我們的比較優(yōu)勢不是在加大,而是在縮小。我們只有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速度來加大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這個比較優(yōu)勢才會保持下去,反之,不僅優(yōu)勢將不保,生存也會成為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