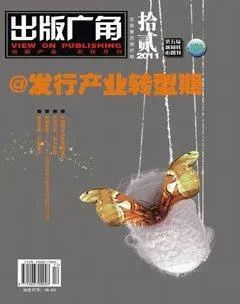詩性的生命與文化
福建少兒出版社最近推出廣西作家王勇英的“弄泥的童年風景”系列,受到兒童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的好評,在廣西文壇引發了系列關于文學創新的思考。我有幸參加廣西壯族自治區作家協會、南方文壇雜志和福建少兒社聯合主辦的研討活動,認真地閱讀了王勇英的這套兒童小說新作,也和與會的專家們進行了近距離的交流,大家都認為這套書在書寫童年、地域文化和生命方面是很成功的。
“弄泥的童年風景”系列包括《巴澎的城》《弄泥木瓦》《花一樣的村謠》和《和風說話的青苔》等四部,每一部都很有特色,都有不同的視角,都能從作家童年的經驗出發,找到全新的兒童文學的突破口。讀此系列小說,感覺它有幾個方面打動了我,也是體現了作家的藝術水平。
第一,它是一部詩意兒童情感小說。不但有詩性的或詩意的語言,還有詩意的文化,在語序方面也是意識流的,是詩性氣質的。詩意的語言,主要體現在作家對客家文化及自然風景的描寫上,還有青苔靠在窗口邊的喃喃自語,它們都是充滿詩意畫意,天然清純而且富有童話色彩的。詩性的文化,主要體現在小說表現了客家文化的神巫色彩與大自然的神秘感的有機結合,讓讀者領略到了客家文化里的原生性的同時,還感受到了那里風土人情人性的淳樸與清澈。而語序的詩性,主要體現在小說的敘述里既有夏風的視角,這是寫實的;還有青苔的視角,是抒情的;這兩種視角交叉起來,使小說里的敘述結構有了跳躍性和詩的情感節奏,給讀者陌生化的閱讀感受。
第二,它的敘述結構非常巧妙,用的是“雙線敘事模式”:一是夏風的身份的揭密,即小說從頭到尾講述了夏風是如何來到這個世界,又是如何經歷成長,如何明白自己的真正血源并理解母愛親情的,這根線索賦予了小說比較豐富的社會生活內涵,它涉及了計劃生育、成年人的情感糾葛,還有復雜的社會關系等等,使兒童小說的視野開闊起來。二是風與青苔的相遇、相識與相知,即風與青苔交往的過程是第二根線索,這根線索使小說具有了少兒成長小說的內涵,因為這根線索是敘述友誼的建立,表現的是兩位少年對友誼,對生命,對社會的理解,它體現了作家的兒童本位的立場,即對童年生命的人文關懷,對童心世界的真誠呵護。
第三,從它的主題來看,小說不但揭密成長,而且表現了兒童成長的智慧。在《和風說話的青苔》里,風和青苔都是有成長智慧的孩子,它們不是傳統兒童小說里被成年人完全規范的“好孩子”或“聽話的孩子”,他們是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力量的生命。夏風被養母安排躲避“龐少”到各地生活,雖然過的幾乎是流浪的生活,但他并沒有因為遠離至親而深感無望,變得孤獨自閉,反而在顛簸動蕩的生活中學會了自我調整,自我成長,尤其是后來,當他了解了母親的真實身份后,他能坦然地接受現實,并深深的理解長者的愛,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而青苔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堅強不屈的品質,以及對生命、生活的理解,也是一般的少年兒童所難以達到的。
第四,小說的藝術元素非常豐富。可以說,《和風說話的青苔》里有童年生存狀態的呈現,有鄉村風土人情的描繪,有客家文化的書寫,還有作家對現代文化的思考,尤其是融入了現代性的批判意識,特別是生態關懷,這是非常有力量,也有深度的。作家站在現代人的視角,來審視城市化進程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及淳樸鄉土文化的摧毀,表現出了一種人文知識分子在現實面前的清醒與獨立。小說也具有悲劇的力量,風的經歷有一些苦難性,但青苔這個女孩子,可以說是一個真正苦難的形象,她因為一次車禍,導致了膝蓋骨受損及小腿的截肢,于是,小小的懷著夢想的她,不得不遠離學校,遠離童年的伙伴,獨自呆在舊樓,去世時還不到14歲。作家沒有過多地詳細的敘述青苔的遭遇,沒有刻意渲染青苔的身體與精神之痛,而著力展現了青苔的堅韌與明朗,以反襯的方式把她的生命的力量給呈現出來,使小說因為悲劇色彩而顯得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第五,對廣西人文地理的直接呈現。這也是王勇英的“弄泥的童年風景”系列小說的總體特色。一般的鄉土小說,或者一般的鄉土文學作品,作家的故鄉只是一個朦朧的文化背景,作家的故鄉只是一個文化鄉愁的寄托物,但王勇英的這系列小說里,故鄉、家鄉或鄉村,清晰而明朗,不是文化鄉愁的寄托物,而是一種純美質樸的生活空間和文化空間,它寄托了作家的愛、關注與期待。
王勇英剛剛涉足兒童文學創作時,主要寫熱鬧的幽默的兒童故事,也發表一些巫婆童話,走的差不多可以說是藝術模仿之路,但經過三、四年的嘗試與探索,她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狀態和寫作方向,“弄泥的童年風景”系列就是她立足童年經驗的基礎上,對兒童小說文化性與詩意寫作的一個大膽嘗試。
王勇英的“弄泥的童年風景”系列小說的創作與出版,在童書日益市場化通俗化、部分作家價值觀迷失的背景下,顯得格外令人驚喜。反復閱讀,感覺它給當下兒童文學諸多的啟示:第一,作家要堅持自我,同時要在不斷探索中勇于超越自我。第二,不做迎合市場,而要做引領讀者的作家,以優秀的精神產品來滋養童年的生命。第三,作家寫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尋找屬于自己的文化位置。第四,作家文化身份的認同,基于她的藝術創新;沒有創新的實踐,就會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感,就無法得到讀者的認可,更談不上自我精神的熏陶或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