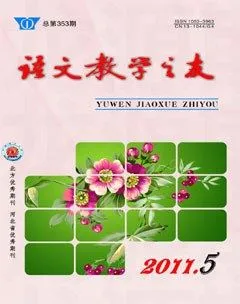試論“處”的時間和空間兩重意蘊的生成及其美學意義
“處”一般指處所,即“……地方”。這在先秦兩漢,尤其是現代,其用法基本一樣。如:
遷徙往來無常處。(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班固《漢書·張騫傳》)
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范曄《后漢書·烏桓傳》)
但在古典詩詞中,“處”字卻往往用以指示時間,作用與時間名詞略同,有“……時”、“……際”的意思,并不是指處所。如:
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杜甫《述懷》)
江海相逢少,東南別處長。(劉長卿《江州留別薛六柳八二員外》)
掩妝無語,的是銷凝處。(賀鑄《點絳唇·一幅霜綃》)
夢回處,梅梢半籠淡月。(阮逸女《花心動·春詞》)
待繁紅亂處,留云借月,也須拚醉。(程垓《水龍吟·夜來風雨匆匆》)
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
《漢語大字典》在第四卷第2823頁亦明確標出:處chù②時刻;時間。并舉了三個例子:
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柳永《雨霖玲》)
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岳飛《滿江紅》)
他變廟宇,正打處,就走了。(《西游記》第六回)
當然,蘇軾《江城子》“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中的“處”,亦不例外。
在詩中,“處”有時與“時”、“中”互文見義。如:
朝朝聽得兒啼處,正是黃炊欲熟時。(楊萬里《兒啼索飯》)
更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簟竟床。(李商隱《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
梅欲開時多是雨,草才生處便成春。(高九萬《歸寓舍》)
何時最是思君處,月入斜窗滿寺鐘。(元稹《鄂州寓館嚴澗宅》)
明妃愁中漢使回,蔡琰悲處胡笳哀。(顧況《劉禪奴彈琵琶歌》)
在詞中,“處”有時與“時”互文,與“正”相應。如:
瞥地見時猶可可,卻來閑處暗思量,如今情事隔仙鄉。(韋莊《浣溪沙》)
飲處交飛玉斝,游時倒把金鞭。(歐陽炯《春光好》)
燕燕巢時簾幕卷,鶯鶯啼處鳳樓空。(馮延巳《舞春風》)
銷凝處,別離情緒,正是海棠天。(胡蒙泉《滿庭芳》)
但是,當我們對大量古詩詞中的“處”細細品味,若簡單地只是理解為“時候”,又似乎不能把握詩詞本身從整體上所呈現給我們的意蘊。“抬望眼”時,“瀟瀟雨歇”;“憑欄”之處,“壯懷激烈”。“明月夜”是面對“短松岡”的“夜”,“短松岡”是“明月夜”中的“岡”。也就是說“處”又含蘊了非一般狀態下的“處所”,我們在“處”的“時間”意義上,同時又獲得了“處”的“空間”意蘊。時間與空間彼此不可分割,呈現出相互規定性。此處之“處”兼具了詩詞中意象事物所構成的整個“時空背景”,從而形成特定的情境。再如:
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秦觀《滿庭芳·山抹微云》)
信人間,自古銷魂處,指紅塵北道,碧波南浦,黃葉西風。(賀鑄《好兒女·國門東》)
在古典詩歌中,“南浦”是指水邊的送別之所。如屈原《九歌·河伯》:“與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古人水邊送別并非只在“南浦”,“南浦”已成為水邊送別之地的一個典型意象。這里都是既描繪了“傷情”、“銷魂”的地點(高城望斷、紅塵北道、碧波南浦),又描繪了“傷情”、“銷魂”的時間(燈火黃昏、黃葉西風)。
同樣,在古典詩詞中,“處”有時表“處所”義,但又含蘊了非一般狀態下的“時間”。如: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霖玲》)
“楊柳岸”乃“曉風殘月”之時的“楊柳岸”,“曉風殘月”乃“楊柳岸”之地的“曉風殘月”。 “我”的沉沉愁醉今夜將在何地(時)醒來?恐怕只會是醒在楊柳依依的隋堤岸邊,那時只有曉風冷冷,天上一彎殘月。空間和時間交糅在一起,呈現出相互規定性,不但組成一幅美妙的圖畫,情景交融,而且與詞的整體意蘊相諧和,美不勝收。
為什么會這樣呢?筆者認為此處之“處”時間和空間意義的兩重性,“是作為場的結構屬性存在著”(愛因斯坦語)。“處”所展示的時空,也只是作為意象事物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引力場的一個結構屬性存在著。意象事物相互作用形成的引力場是意義的引力場,這個意義的引力場也就造就了詩詞意境的雄渾、深邃,使得此處之“處”獲得了時間和空間的兩重意蘊,表達了更為概括的意義。否則,“處”所觀照的事物只能是事物本身,即詩人“反映”所得的境界“物境”;物象便不能成為意象,即詩人“感應”所得的境界“情境”,也就形成不了“物境—情境—意境”的鏈式遞效的佳境。“處”所聯系的“物境”是“此時”(就在那個特定時間)的“物境”,也就是說,詩人“此時”的特定心理指向正是有“感應”所得來的“情境”,是在物我情融之下的圓融。“處”起到了將“物境”轉化為“情境”的紐帶作用,起到了在意義的引力場內由物境達至情境直至兩者融合為一(意與境融合為一而成意境)的中介作用。“處”在詩詞意義引力場中的位置,恰恰是在詩詞所展現的整個時間和空間網絡中的位置,“處”的時間和空間兩重意蘊正是由此而獲得。
由上可知,“處”所兼具的時間和空間兩重意蘊并不是本身存在的、原本應有的,而是與物和場相結合存在,獲取作為“這個”的物象和情境。當此之際,時間被時間化,可以“能看到”,空間被時間化,可以“能動地被感知”。這就使抽象概念的時空有了綿延性與廣深性,空間的某個地點和時間的某個時刻就可以互通無阻。正如“長短”、“前后”、“里”、“中”、“內”、“外”等一些詞,既可指空間方位,同時又表時間。在這里,我們把“處”語言的理解和文學的理解交融在一起,使其顯在意義展現的時間與潛在意義存在的空間并舉,這就獲得了一個嶄新的詩詞理解的“情境脈絡”,從“現場”的意義關系結構(場)中去發現事件發生的連續關系和意義。
其實,在古典詩詞中,時間和空間對舉出現這種表達形式本身,一方面使詩詞的意蘊更加豐富;另一方面使得我們對“事件發生的連續關系和意義”的理解就更為全面和深切。如:
故園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祜《宮詞》)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別舍弟宗一》)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杜甫《登高》)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飛《滿江紅》)
進一步來說,“處”的這種時間和空間意義建構(不僅僅指“處”一字,還有其他一系列詞語如“長短”、“前后”、“里中”、“內外”等),從一個側面也道出了詩詞的時空建構的美學意義——時間的空間化、空間的時間化,使屬于主觀范疇的“意”與屬于客觀范疇的“境”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妙合無垠”,從而達至詩詞中所謂“意境”的真諦之所在。
換種角度看,從哲學上來說,時間空間化與空間時間化是完全可能的。正如海德格爾在其哲學名著《存在與時間》中所說:“‘在空間中’的現成事物的種種經驗表象作為心理上出現的事物‘在時間中’進行,于是‘物理的東西’間接地出現‘在時間中’”,“此在特有的空間性也就必定奠基于時間性”。意象就是在空間中的現成事物的種種經驗表象,就是奠基于時間性的“此在”。“處”所展現的時間和空間兩重意蘊,就是時間和空間經意象事物的有機組合,而相互轉化與合一的結果。
(作者單位:徐州高等師范學校
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