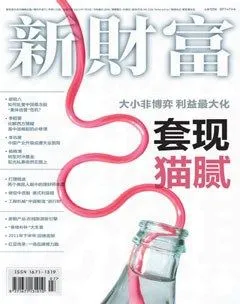經濟進入弱周期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可能維持數年的偏低增長期,而整個社會對其后果估計不足。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已經歷過三個超高的持續增長期,每次5-6年,增速維持在10%以上。在超高增長期之間,也出現了偏低增長期,持續3-5年,同時伴隨著經濟的結構性轉型。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可能維持數年的偏低增長期。弱增長期的背后,是信貸、房市、出口、中小企業的弱周期。中國在此期間將面臨兩大結構性轉變: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必須改變,信貸催生式增長模式必須改變。
2010年中國經濟的最大意外,不是通脹失控,不是房地產新政,而是民營企業家蜂擁投向PE,在泡沫的海洋中暢泳。做實業艱辛,工資漲、成本漲、匯率漲,做財務投資則易如反掌,房地產、股市分分鐘可能賺出實體利潤數倍的回報,其背后其實是天量信貸擴張所帶來的資產泡沫。
然而,民間資金投資偏好上的突然變化,并未引起政策決策者的重視,全國上下沉浸在最先從金融危機中復蘇的主要經濟體的自信之中,中央政府忙于抑制房價,地方政府忙于賣地,工人要求漲工資,熱錢從大蒜炒到字畫。當財政擴張的效力消失之后,當天量流動性進入收水階段之時,實體經濟自主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便暴露了出來。
首先,目前的信貸結構問題嚴重。當年不顧后果地擴張信貸時,大型國企、地方融資平臺是主要受惠者;而貸款收緊時,中小企業卻成受害者,中國人民銀行在貨幣環境正常化實施上,采取了數量型收縮孤軍深入的策略,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了600基點,4.5萬億元流動性遭抽離。但是,流動性的減少并非由所有經濟參與者共同承受。銀行對大型國企仍是全力貸款,而中小企業則被完全摒棄,陷入近十年來罕見的流動性危機,灰色貸款利率飆升。“錢荒”處理不當的話,中國經濟難免全面滑坡。
信貸更大的問題是,隨著貨幣政策的收緊,銀行業務對象的減少,銀行作為金融中介的功能有明顯弱化的趨勢。大量資金或被鎖進準備金賬戶,或以金融產品形式進入投資領域,或轉入對資金并不渴求的大型企業手中,信貸在經濟中的影響弱化了,信貸的乘數效用下降了。
同時,以出口業為主體的沿海中小企業,正面臨一場現金流危機。除了信貸緊縮外,工資上漲、匯率上漲、材料價格上漲,扼殺著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企業遷往內陸省份,是為制造業設計的退卻之途,也是中國平衡地域經濟的國策。可是漲工資成了地方政府政治正確的做法,今天上海加工資20%,明天重慶便宣布加工資30%。
產業升級、企業轉型,是中國經濟再上一個臺階的重要環節。漲工資,更是擴大內需、將增長果實分配給勞動者的關鍵舉措。這些無疑是必要的。但是,過快、過激地推行這項政策,帶來的不是企業成功轉型,而是企業倒閉,工人最終未必受惠。經濟轉型是要調結構,而不是促成產業空洞化。
通脹升溫,令政策的選擇空間、回旋余地大幅收窄,許多政策由主動調整變成被動應對。
經濟轉型中,在不影響社會安定、金融穩定的前提下,犧牲一點增速,也無可厚非,不過筆者看來,整個社會對轉型的艱巨性認識不足,對經濟進入弱周期所產生的后果估計不足,對可能需要的反周期措施準備不足。
不要預言通脹何時見頂、增長何時見底、貨幣政策如何轉向、房價有無反彈,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中期的弱周期。通脹見頂后未必回落,增長見底后也難反彈,貨幣政策的決策難度越來越大,銀行信貸“去”中介,民間實業投資持續萎靡。這種環境下,房價該升該跌,讀者自己去判斷吧。
對于本文內容您有任何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