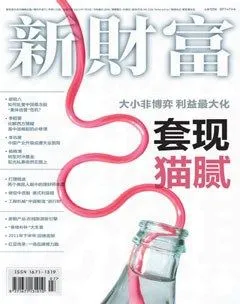被綁架的美國醫療體系中國不能學
在醫療費用昂貴、患者得不到保護上,美國醫療健康體制的這兩大弊端與中國驚人地相似。美國醫療體制的失敗,在于其醫療健康體系受到了市場中各方力量的綁架與祟尚自由的價值觀限制,其經驗教訓值得中國借鑒。
在中國醫療改革徘徊不前、“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并強調了“增加財政投入”的手段和“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的原則,令人為之振奮。然而,如同所有的改革,醫改光是增加財政投入和有一個明確的原則是不夠的。“好事多磨”是對醫療衛生體系建設這一全球性難題的精辟定性,在全球,特別成功的模式幾乎沒有,13億人口的中國,更不可能照搬任何所謂的世界先進經驗,但這也恰恰提供了一個機遇,中國有可能摸索出一個具有特色的醫療衛生體系。為此,對他國醫改的研究顯得尤為必要。
強大的美國,脆弱的醫療健康體系
美國的醫療健康制度雛形初顯于二戰期間,其后以醫療保險和醫療資助(medicare and mediaid)為里程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系,即以政府為主導的對老人和窮人的醫療資助和以雇主為主導、以市場為體制的員工(包括家屬)醫療保險這樣公共和私營兩大資源支撐的體系,配之于人人有權享受的急診室法律保證。
應該說,這一體系曾經成績卓然,其在過去一個世紀將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延長了30年;但是,它最終演變成了一個臃腫龐大、集各方利益集團為一體的錯綜復雜的體系,成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瓶頸。美國人盡管在世界上為醫療健康付出最多,可與其他發達國家人士相比,在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等健康指標上都略遜一籌。
美國醫療健康體系的優勢顯而易見—這個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每年不惜傾GDP的17%花于醫療健康費用,并具有世界領先的醫藥研發和生產能力、一流的醫學院和醫療人才,以及最嚴謹、最挑剔的醫療管理和審核體制。但是,美國依然被醫療健康體系的種種弊端所困擾,無論企業、政府、政客或是百姓,對于醫療健康體制幾乎都是怨聲載道;而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卻又根據自身的利益五花八門。
被市場導向綁架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美國醫療健康體系的運行方式,那就是一駕被脫韁野馬拉著橫沖直撞的馬車,而這匹野馬就是市場經濟。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美國醫療健康體系的運行充分發揮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功能,但這并沒有帶來鼓吹者所預言的效果。美國醫療健康體制的兩大弊端與中國驚人地相似:一是醫療費用昂貴,老百姓病不起;二是患者沒有得到保護。
我們常常聽說美國的東西比中國的東西便宜,尤其是房子比中國的大城市便宜多多,但相比中國,美國的醫療費用實在令人咂舌:2008年,美國人花在醫療方面的費用為2.3萬億美元(平均每人7681美元),占當年GDP的16.2%,是1990年7140億美元的3倍、1980年2530億美元的8倍!而同期美國的CPI僅僅翻了一倍(1982-1984 = 100;截至到2011年4月 = 224.9)。扶搖直上的醫療費用,無論對個人、公司還是政府,似乎都永無止境。
我前不久扭了腳腕去看醫生,除了第一次幫我用石膏固定腳腕外,以后每次都是例行的拍X光片和1分鐘醫生面談,半年時間看了5次醫生,費用是2800多美元。如果不得不住院,那就是宰你沒商量了,一天的住院費根據地區、治療和服務而有所不同,但平均為3000-5000美元/天,住院一周花個三五萬美元根本就是尋常事,而在美國住院的平均時間大約是5天。一個朋友前不久做了換膝手術,光是手術費用就達4萬美元。
雖然美國花在醫療健康上的費用是世界之冠,但有將近1/3花在行政管理上(加拿大為16%):從接線生的工資、銷售經理的出差費用到首席執行官天文數字的獎金,當然,還有他們的利潤和投資者的回報。在美國,醫療事業是純粹的私營盈利企業,醫生診所和醫院是名符其實的“有病沒錢莫進來”。在這樣的制度下,真正能夠享受一流醫療水平的人只剩下少數富人,全世界的富人都能選擇到美國享受最先進的醫療技術、最有效的藥物和最無微不至的服務。純粹以市場為導向的醫療體制,最終導致了醫療事業的扭曲。
被利益與醫療事故保險綁架了的醫生
盡管費用昂貴,但患者獲得的醫療服務與保護卻與之并不相稱。首先是服務越來越差。前不久,一個朋友因為內風濕引起的關節及腰背疼痛約見醫生,沒想到醫生辦公室告訴她要約三個不同的時間,看三個不同的醫生。結果她花了三個半天、1000多美元,平均每次只見到醫生不到10分鐘。
其次是花樣越來越多,手段越來越可疑。前不久我去做例行體檢,體檢前我一看讓我簽字的一大摞表格里有張醫生聲明,他在將要為我做的使用某種先進技術的醫學圖像診斷室里有股份,而這一診斷保險公司是不負擔的。顯然這里面有著利益沖突,我斷然拒絕做那項檢查。去年的一次體檢,醫生要求我用心臟核磁共振做心臟的檢查,我一向心臟特別健康,更是聽到“核”就反感,提出異議,醫生沒堅持。事后問一位心臟科專家朋友,他說像我這樣的情況完全沒有必要,純粹是醫生要賺錢。
一位在美國行醫多年的中國朋友告訴我們,任何時候如果被醫生要求作子宮切除或卵巢摘除手術,一定要去詢問她的意見:“美國醫生的原則是能切就切,能摘就摘。這是他們的賺錢之道。反正切除的理由有得是,不切除的害處舉不勝舉!”談及過度醫療,說者義憤填膺,聽者毛骨悚然。
差不多有98%的醫學院學生在入學或畢業時要做不同形式的宣誓,雖然誓詞不同,但大意都是要盡力為病人解除痛苦、遵守職業道德等等。但宣誓歸宣誓,這些年,以救死扶傷為天職的醫生丑聞不斷,其道德水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每況愈下。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醫生是在一張錯綜復雜逐利群體的蜘蛛網上的犧牲品。我幾年前曾和一個獵頭打交道,他曾經是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沒想到在一次醫療事故后被患者告上了法庭,結果不但聲名狼藉,而且一貧如洗。雖然行醫執照保住了,但傷透了心的他決意從此改行。
美國的律師之多世界出名,其中有相當一大批人是“追趕救護車者” (Ambulance chaser)。這個頭銜很形象,描述的就是一批嗅著血腥味替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師群體。當然,他們不是什么拔刀相助的綠林好漢,他們要的是錢。雖然美國的法律明文規定不容許追趕救護車,可是這樣的行為屢禁不止,愈演愈烈。想賺錢的律師加上本來就愛打官司的美國人,美國的醫療行業不知不覺地被綁架起來。
2010年,紐約州法院判給一個腦癱瘓的3歲男孩7500萬美元賠償,原因是產科醫生在他出生時的某個判斷失誤造成了他的腦癱瘓。因為害怕被患者起訴,絕大部分醫生都會去買醫療事故保險。據估計,只有5%的醫生選擇不買保險的行醫方式,在某些州的醫院里,不買保險的醫生根本就不能看病人。醫療事故保險的費用因地區和專科差異很大,以最高的佛羅里達州為例,內科醫生的保險在2009年為56000美元左右;外科醫生的保險在9-17萬美元之間;至于婦產科的醫生則高達10-20萬美元。同時,醫生為了免于被起訴,往往要做更多的試驗和治療,這在行內被稱為“防御性治療”(defensive medicine)。
我在佛羅里達生活了4年,可以說深深體會了美國公認最差也最貴的醫療服務。乍一聽很奇怪,費用高應該服務好才對啊?其實不然,你想想,醫生每年要付如此高的費用買事故保險,好醫生誰還來佛羅里達?不得已來了的,當然要想盡辦法多看病人多收錢,不然連買事故保險的費用都不夠,還怎么養家糊口?在這樣的壓力下,醫生有心情、有時間提供良好的服務嗎?所以,昂貴的醫療事故保險費用和不被保護的患者,變成了被綁架的醫療體系中的一對孿生兒。
被醫藥公司綁架
心平氣和地說,我比較欣賞美國醫藥分家的做法。在美國,醫生只管開處方,到哪里拿藥是你的自由,而藥房已完全融入消費者市場,很多大的連鎖店和超市都經營藥房。市場競爭的確帶來了相當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消費者的利益。
但是在美國,醫藥業的影響力非同小可,這是一個有著3000多億美元銷售額的行業。其影響力首先表現在狂轟濫炸的廣告宣傳上。1997年,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放松了對醫藥公司在宣傳藥物效用同時要聲明潛在副作用的要求,從此藥物成了消費品,幾乎每個人都會有幾個自己信奉的品牌。網絡的出現則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消費行為和廠方的行銷方式。
美國醫藥業還通過專業的說客(常常是前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向政治選舉獻金,游說和影響重要決策部門以維護行業的利益。在首都華盛頓,光是注冊登記的藥業說客就有1500多個。據統計,僅在1998-2004年間,美國藥業就對1600件法案進行了游說,1998-2008年間,游說費用高達9億美元,其中光是對聯邦和政黨的政治獻金就高達9000萬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共和黨收到的獻金是民主黨的3倍。
中國老百姓常常抱怨的醫藥公司給醫院和醫生回扣,與這樣合法的、大規模的游說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他們給錢的目的五花八門,一言蔽之就是為了多賺錢,比如延長和保護專利、放寬對新藥上市的要求等。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在美國形成了一個從加拿大進口美國藥物的黑市,出口到加拿大的美國藥物被進口回到美國后反倒更加便宜,這在美國是公開的秘密,也是一個市場經濟中的最大笑話。美國醫藥行業滲透政治、影響市場的能量由此可見一斑。
被醫療保險公司綁架
美國幾乎所有的醫療活動都被五花八門的醫療保險公司所把控,是公司就要賺錢。凡是在美國生活過的人,都會領教醫療保險公司繁縟和令人窒息的程序與文件要求。民間戲稱醫療保險公司的文件比在當得·米夫林(美國電視連續劇《辦公室》里一家賣紙為主的辦公用品公司)的紙還多。
保險公司常常雇用廉價勞動力來辦理理賠,可是你要想得到合理的賠償和支付,非得有個碩士學位不可(本人有,但在與保險公司打交道時常有力不從心之感)。當然也可以很簡單,保險公司說付多少就付多少,其余的你自己買單。我去年與保險公司有470多美元的糾紛,在公司一位員工福利主任指導下與保險公司交涉,結果3個月下來,來往的電子郵件和傳真足有300多頁,保險公司只同意退回17美元。我一看賠不起這個時間和精力,只好叫停認輸開一張支票完事。
在美國,社會醫療保險并不包括所有的醫療項目,所以很多人還不得不買一份附加險(Supplemental Health Insurance),用來補足社會醫療保險不負擔的部分。我一對做生意的朋友每年光買醫療保險的費用就是15000美元,我們作為雇員雖然有公司承擔大部分醫保費用,但自己負擔的部分自1999年以來已經增長了131%。按照現在的上漲幅度,很多公司將會因此倒閉;更多的個人將會因無力支付而選擇鋌而走險—不買保險。因此,雖然美國老百姓和政府以及商界對醫改持有不同的立場,但對醫療保險費用上漲制約了經濟發展、非改革不可,觀點卻是前所未有的一致。
被個人自由與黨派政治綁架
研究美國醫療體制的失敗,不能不談美國人關于自由的價值觀,其代表名言是“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