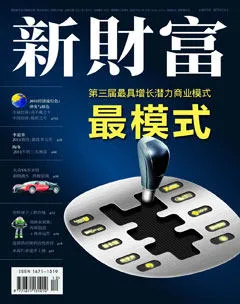新一年的三大地雷
新興市場債券、西班牙國債與銀行、美國國債等隱患將使2011年的市場動蕩更甚于去年。
2007年的次貸危機,拉開了去杠桿的序幕,這是對連續十幾年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銀行信貸擴張及金融創新的一次清算。今天的形勢,較前兩年要好許多。但是,全球范圍內的去杠桿進程并不均勻,政府財政狀況仍在惡化,貨幣政策的亂象激起市場的亂波,全球經濟尚未走出高危期。
步入2011年,筆者認為全球經濟的增長勢頭趨向平穩,不過市場的波動可能加劇。超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主權債務危機的衍變、G3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政策上的背馳、美元匯率的大幅波動,均可能帶來變數。筆者看來,2011年至少有三大地雷。
新興市場債券。雷曼兄弟倒閉后,資產價格升值最多的,不是黃金、股票、商品,而是新興市場的高息債券。在過去十年中,新興市場的基本面有所改善,而且涌現出“金磚四國”這樣的精英經濟體。
不過必須看到,新興國家的崛起過程中,流動性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利率的下降拉低資金成本,同時令更多的資金矚意高收益債券;外資流入抬高了匯率,降低了通脹水平,令新興國家利率下滑,發債成本減輕,財政負擔減少,更進一步刺激了資金的流入。
換言之,在新興國家中,有經濟前景出現結構性改善者,也有一批國家拜量化寬松政策下高流動性、低資金成本所賜,償債能力有所改善。對于后者,一旦資金成本有變或美元大幅升值,海外資金流入情況隨時可能逆轉,并帶來匯率、通脹、利率上的連鎖反應。發達國家出事,不代表新興國家不會出事。許多新興市場債券,價格已進入不合理狀態。
西班牙國債、銀行。歐元的出現、歐洲就業市場的互通以及信貸的擴張,在過去10 年給西班牙經濟帶來了過去30年所罕見的增長機遇,也為當地房地產市場帶來了不亞于美國、英國的泡沫。可是西班牙政府卻沒有采取美英那樣激進的銀行拯救及重整措施,拖慢了房價的調整過程,在銀行壞賬處理上也采取駝鳥政策。
希臘、愛爾蘭債務危機,將西班牙的主權債務困境顯性化了,其國債發行利率大幅飆升,過去行之有效的發新債還舊債模式變得難以為繼。西班牙并不在歐洲央行購買債券施援的名單上,不過歐洲與IMF隨時可以獲授權干預市場,拯救西班牙。然而,歐債危機走到這一步,全部涉及人為的政策失誤,歐洲領袖意見之繁多、決策之慢,增加了西班牙陷入危機的可能性。
西班牙經濟體量占歐洲總量的11%。一旦西班牙陷入危機,幾乎所有歐洲金融機構都會受到影響,美國與拉美國家、歐元也不例外。
美國國債。美國長期國債利率近期突然大幅上升,是一個危險的警號。奧巴馬政府將布什應對危機所作出的減稅措施全盤延期,觸發了市場對山姆大叔償債能力的擔心。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美國國債收益率與其隱含的違約風險不成比例。近來美國國內金融機構對國債的購買已超出海外。其實,這背后是美聯儲的量化寬松。央行將大量流動性注入銀行體系,而銀行借貸意欲不強,于是資金被轉投國債市場,拉低了商業利率。美聯儲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將進一步加劇這種政策造成的價格信號(利率)扭曲。
美國經濟恢復之時,便是美聯儲退出之日。當增長預期、通脹預期上升時,美國國債市場便可能孕育出一場變化,甚至動蕩。由于幾乎所有銀行、保險公司均在投資組合中大量持有國債,國債一旦出事,便可能產生數倍于雷曼倒閉時的震撼。
以上三個地雷,屬于“已知的未知”,此外還可能有事先未可預見的“黑天鵝”事件。2011年市場的動蕩程度,應該更甚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