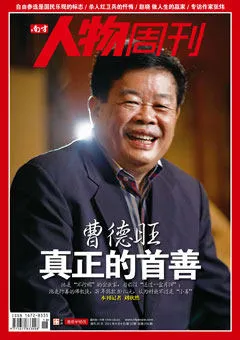自由參選是國民樂觀的標志
2011-12-29 00:00:00彭淑陳漫清張嘉衍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18期

5月30日晚7點,姚博與他剛組織起的“參選班底”在北京市某餐廳大快朵頤。
姚博的網名“五岳散人”。這位媒體中人、知名的時評作家,數天前在其微博上坦言:經過審慎的考慮,我決定以無黨派、少數民族的身份參加今年舉行的北京市區縣人大代表選舉。……我選舉的目的是代表本區的選民爭取他們的利益,為他們說話。所有選舉費用由我個人承擔,如果當選,在任期內的辦公費用亦由我個人承擔,有可能接受義工的幫助。
“我是參加昌平區人大代表選舉,參選要做的各個步驟已開始進行。”吵嚷中,姚博說,5年前,他已有此想法,“這是一個公民的合法權利。說得直白一點,都是自己的事,為什么不去干呢?”
恰如社會學者于建嶸論及一位女性自由參選者時所說:“我認為她為秋季選舉吹響了號角。”——響應這片號角聲的,除了姚博、還有作家李承鵬、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來自廣州天河區的“擁有九年黨齡”的梁樹新、杭州下城區做房地產工作的徐彥等全國各地的黨內黨外不同職業人士。
“號角”早在80年代吹起,于1998年形成一波高潮。王亮、司馬南、姚立法、黃松海等都是多年前成功當選縣級人大代表的“獨立候選人”。以現在嚴謹的說法,他們被稱為“聯名推薦候選人”。
只是,“其中大部分人勝出后,面臨的局面并不理想。”被喻為“獨立代表新生代”、迄今仍“自由參選”的江西鄱陽縣人大代表黃松海表示。
他以4年來的“參政體驗”婉轉地分析,“不管是哪一批‘自由參選者’,都要面對一個共同問題,即人們的思想觀念。其中,一方面是官方的看法,一方面是民間的看法。”
“雖然現在網絡輿論和信息發達,公民的聲音很多時候可以發出來,政府對公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認識,越來越開放,不可能像以前那樣完全操控。但還有個別官員持保守、‘很左’的眼光看待這件事。
“官方的開明也需民眾的推動。很多人公民意識不夠,漠視,認為選舉沒意義。抱怨者很多,一邊聲稱自己從沒拿過選票,一邊不愿參與這件事。其實這個權利是實實在在的,如果大家都參與,應該好很多。”
黃松海強調,作為自由參選,“與當地政府溝通”是成為人大代表后可持續性的“緊要技巧”,“如果不學會妥協,不注重持續性與復制性,再轟轟烈烈都將是曇花一現。要么自己心灰意冷,要么就被同化了,最后自身利益至上了。”
但不可否認,雖通過自己的策略取得官方一定的認可,“真正認可我們的很少,多為表面上。很多官方人士,當你觸及到他切身利益時,會對你恨之入骨。當然,我們還觸及不到主要官員的私人利益,因為我們不可能掌握到那個層面。比如交通局亂收費、供電局違規供電,我們可以監督,這些事情都擺在面上。一旦要牽涉到體制問題,就難以做到。”
“都多少年過去了?我們要相信這個社會在進步。如果不從他們那時進步,我們就沒法自由參選,如果我們不參選,接下來的人就無法繼續參選,讓人大這種制度成為真正的鋼印。”姚博回望黃松海等人的參選歷史時說。
他與黃,兩撥自由參選者卻共同篤信:自由參選人大代表在中國,普及了民主理念,推動了民主的進程,“這已相當不錯了。有多少人還在反問民主,還在反問普世價值,還在認為應該有一個強力的統治,而不是用一種民主協商制度來平衡我們社會關系。”
“這就叫‘人心不死’。” 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聽完,幽然一笑。
這特別值得我們廟堂之上的人高興
人物周刊:現在很多網民在微博上發出要自由參選人大代表的聲音,本屆的聯名推薦候選人的數目也遠遠超過以往。你覺得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賀衛方:我覺得最主要是,現在國家的體制改革已經成為很多人關注的焦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見證了國民政治意識、民主意識的覺醒,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最近大家越來越傾向于說:爭取參與到哪怕是基層的人大,去競爭,這是一件特別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在這樣一波大潮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點?
賀衛方:首先,他們不是官方指定的人參選。第二個特色是,新媒體提供了很好的技術。博客、微博、論壇,能讓網民了解到某個人要參選,而這些人也利用網絡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樣會強化網民對候選人的認知。人們選舉的時候會變得更加理性,有真正選舉需要的判斷力。
人物周刊:您覺得相比一般候選人,中國現有的選舉法為聯名推薦候選人提供了哪些渠道?
賀衛方:從渠道上講,候選人如果不能跟選民有直接的溝通、交流,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選。
如果說我們在制度上有什么改進的話,我們應該讓參選人有機會、有途徑,甚至有官方途徑去跟選民們溝通,讓我們的選民做出選擇。
人物周刊:根據憲法,公民具有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權利。可在實際情況中,以獨立資格當選人大代表的屈指可數,面對這樣一個現象,政府和各級人大應該怎么樣去對待?
賀衛方:我覺得首先應該對民眾煥發的參與意識要表達關注和支持,這可能需要有關部門和高層明確表達支持。
這首先表明,民智未開這種說法很荒唐。只要是制度有一定空間的話,這些人一定會去做的。
第二,我們現在需要設計一些更加合理的制度,讓擁有參加政治生活熱情的人們能獲得一種途徑,比如如何能跟選民交往,如何通過公眾表達自己,如何進行辯論。
第三個方面,我覺得從長遠來看,他們當了人大代表以后,要有制度保障他們能對包括官員的選舉、財政方面的審查、立法等進行深入的審議。現在很多人參與到選舉過程中,但接下來可能就會覺得,其實選上去也沒什么多大的意義。
人物周刊:我們還關注到,有些地方官員打壓公民自由參選人大代表?
賀衛方:地方領導都會特別關注這個過程,想方設法把他們認為應該選上的人選上。有些受打壓的參選者在微博時代能得到這么多的關注,而在“前微博時代”,也有不少人受到相同待遇,不奇怪。這需要各級官員從根本上扭轉對民主的態度。
人物周刊:自由參選人大代表,對中國的民主進程有何預示呢?
賀衛方:我想,其實最讓人欣慰的事情就在這里。這說明很多國民對現行體制還抱著樂觀的情緒,這特別值得我們廟堂之上的人高興。
如果是“上梁山”的人,他們不樂觀,他們覺得一切沒有希望。我特別愿意借你們這個雜志呼吁,這些人特別值得我們去支持。無論是升斗小民,還是權貴們,都應該知道這是一個多么好的事情,都應該給他們空間。如果有人打壓封殺自由參選人大代表,這會是讓對體制抱著樂觀態度的人心灰意冷的做法,是對我們國家和體制不負責任的,是在拆我們大廈的磚。
其實,最美好的狀態并不是社會沒有弊端,而是說我們社會封殺了我們改善弊端的空間。
中國式的選舉,那真的是特別需要超強智慧
人物周刊:若干年前,就有人成功獨立參選人大代表,這個現象出現不過十幾年。你覺得他們在民主進程中有什么作為嗎?他們成功當選后的現狀怎樣?
賀衛方:確實不怎么樂觀,制度運行情況對自由參選比較艱難。太多代表是官方指定的;太多人大代表是企業家為了獲得榮耀,通過政治身份獲得經濟收益成為人大代表,還有演藝界的。這不利于自由參選人在人大里面發揮作用。
人物周刊:不少人正是擔心,如果自由參選人勝出后,面臨的仍是不樂觀狀況,會讓一些民主意識尚未開蒙的人更疏離他們本應具有的權利。
賀衛方:其實民主是許多不同階層和利益群體的愿望,希望大家表達出來,進行博弈。沖突并不要緊,其實這是整合我們國家、團結國民的非常好的途徑。最可怕的是我們沒有機會說話,沒有途徑表達自己,決策過程跟我們沒有任何關系,這會讓所有人心灰意冷,愛國熱情和其他對具體制度的看法,都會四分五裂。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如今到了改革的重要關口,網絡上這么多人有政治熱情,讓我們特別欣慰!
人物周刊:當年那些人成功當選的經驗和參政實踐,對于現在參選的網民有沒有可以借鑒的地方?
賀衛方:以前的經驗是在前微博時代,今天是一個微博時代。過去的經驗跟現在做法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到底怎么去做,與其說是民眾的問題,不如說官方如何對待不同的時代,如何去適應社會的潮流和趨勢,讓這次改選真正成為國家民主發展的契機。
人物周刊:以往一批自由參選人里,如黃松海,屬于堅持下來的類型。他認為,他之所以具有可持續性,是因為自己善于與官方溝通。他不否認這是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一種妥協的技巧。如果在真正實行民主的國度里,是否還需要這種“技巧”?
賀衛方:我跟他們個人很少接觸。中國式的選舉,那真的是特別需要超強智慧。選舉畢竟需要選民去投票,選民要知道你這個人。
任何地方的民主,包括成熟國家的民主,都不是那么單純,沒有任何弊端的。在美國,選舉過程中的技巧和智謀都是有的。民主只是所有制度中,壞處少一點的制度。但是我們人類無法做到完美無缺,我們大可不必把民主開啟時出現的一些問題看得太重,以至于成為不搞民主的借口。
民主其實是人性中的內容,沒人生下來喜歡被奴役
人物周刊:過往參選者中,出現了勝出后被迅速“同化”的現象。有人質疑,今天參選的網民,會出現同樣的狀況?
賀衛方:慢慢地有些人被同化,有些人沒有被同化,可是慢慢地被同化的人就很少了,慢慢地體制就會被塑造。
人物周刊:一個成熟的參選者應該具有什么樣的素質和條件?
賀衛方: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的表達能力都很重要。參選者的這種能力特別重要,怎樣跟人溝通,讓人理解你,不會誤讀你。
另外,一個人的人格魅力、已經取得的成績,比如冰心女士的女兒吳青,本來在北京市民心中享有很高聲望。還有不要把自己標簽為政府的敵人。
人物周刊:有人認為中國投票者沒經過民主的訓練,還不成熟。
賀衛方:這種說法是阻礙民主發展的最大障礙,民主不是培訓出來的,是實踐出來的,沒人看教科書學會游泳,先嗆很多水才學會。民主其實是人性中的內容,沒人生下來喜歡被奴役。
人物周刊:不同自由參選者在不同地方,所受際遇也不同。如江蘇常州與有些地方不一樣,表示熱烈歡迎參選。依照同樣的憲法和法律體系,出現不同的對待方式,這是什么原因?
賀衛方:這個完全取決于地方領導自己的觀念,我們知道不同地方的領導人,政治信念、對國家前途的理解差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