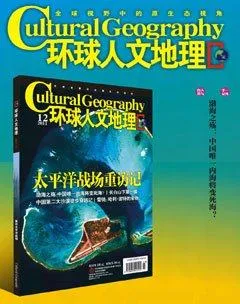晉南考古手記探秘“最早的中國”
2011-12-29 00:00:00姚於
環(huán)球人文地理 2011年12期









明清以前,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帝在登基前必須做兩件事——泰山祭天,后土祠祭地。因此,后土祠又堪稱“中國最早的地壇”。
陶寺,這個汾河之濱黃土塬上的村莊,從它的懷中不斷發(fā)掘出來的一件件器物,仍在為人們展示中國歷史上的堯舜禹時期。
在周家莊遺址內(nèi),我們用剛剛學(xué)來的考古知識,發(fā)掘出3口甕棺——這是龍山時期兒童墓葬的標(biāo)志。
中條山懸崖邊上的虞坂古道,是多個王朝的命脈。相傳遠古時期,河?xùn)|鹽池的鹽正是通過這條古道源源不斷輸往中原,最終助黃帝打敗了蚩尤。
在應(yīng)邀參加“發(fā)現(xiàn)中國”考察團穿越晉南地區(qū)之前,重溫了我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當(dāng)年,這個美國人對于我們即將踏上的這片“龍興之地”的評價,充滿了震驚與遺憾:“這一個令人驚嘆的黃土地帶,它成就了最早的中國……地質(zhì)學(xué)家認為,黃土是有機物質(zhì),是許多世紀以來被中亞細亞的大風(fēng)從蒙古、從西方吹過來的……”
他的話讓我躍躍欲試。我知道,自己即將踏上的是最早的中國,也就是華夏文明的源頭。于是,我心中不由得泛起愁思,其實那是一個民族繞梁千年的鄉(xiāng)愁:從軒轅到春秋,再到漢、唐、明、清,這些帝國的命運,似乎都隨著這片土地的繁華而鼎盛,又隨著其衰落而消亡……
“中國最早地壇”后土祠見證堯舜禹時光的陶寺遺址
此次旅程開始時,我們選擇了萬榮縣的后土祠為出發(fā)點,因為這座小廟背后有一段宏大的歷史:明清以前,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帝在登基前必須做兩件事——泰山祭天,后土祠祭地。因此,后土祠又堪稱“中國最早的地壇”。
初秋的10月,在后土祠很容易想到那位比我們早來2151年的皇帝,他在這里寫下了千古流芳的《秋風(fēng)辭》,可以說,是他開啟了后土祠輝煌的香火。
他叫劉徹,歷史上被稱為漢武帝。據(jù)祠中保存完好的《歷朝立廟致祠實跡》碑記和《蒲州府記》記載,后土祠本是軒轅皇帝一統(tǒng)天下后,為拜祭中國最早的祖先女媧氏所建。而從漢武帝16歲登基到去世,這位帝王一生中曾6次前來拜祭,儀式相當(dāng)隆重,繼而為后世形成了這樣一個制度:每3年,皇帝都要來這里舉行一次大祀——于是,從漢宣帝、東漢光武帝開始,到后世的唐玄宗、宋真宗等歷朝歷代皇帝,都曾先后來此祭祀,并對后土祠進行修葺、擴建。
站在后土祠的秋風(fēng)樓上,能見到汾河與黃河交匯的雄壯,也能感受到漢武帝所述“秋風(fēng)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的蒼涼。那么,后土祠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逐漸被世人遺忘的呢?史料上是這么說的:明清時期,朝廷采集后土祠的土,在北京建起地壇,祭祀后土的儀式也因此遷徙,后土祠從此開始淡出帝王祭祀的歷史舞臺。更為不幸的是,從公元1567年開始,黃河屢發(fā)大水,后土祠連同秋風(fēng)樓一起,多次被黃河淹沒沖毀,后又屢毀屢建,直到1870年,后土祠被徹底移建于原址背面的高崖上,才得以保全真身,至今已有131年。
在觸摸過大漢的輝煌時光后,我們繼續(xù)向更古老的時代進發(fā)——向?qū)Ц嬖V我們,當(dāng)天晚上的宿營地是陶寺遺址,那里有中國最古老的觀象臺,以及4100年前的古老時光。
陶寺,這個汾河之濱黃土塬上的村莊,其遺址發(fā)現(xiàn)于上世紀50年代。而現(xiàn)今,從它的懷中不斷發(fā)掘出來的一件件器物,仍在為人們展示著中國歷史上那個屢遭西方質(zhì)疑的堯舜禹時期。
由于堯舜禹時期在文獻中沒有完整的文字記載,因此就被一些人視為傳說,但經(jīng)過考古學(xué)家對陶寺遺址的墓葬的鑒定,證明它們都屬于龍山文化晚期(也就是堯舜禹時期),這就為這段中國歷史的真實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2009年6月21日,考古學(xué)家利用陶寺遺址出土的“圭表”復(fù)制品測量日影宣告成功,這表明了早在那個時期,我國就已經(jīng)擁有了兩套當(dāng)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測量儀器及方法——“測日出方位”和“測正午日影”,也確認了當(dāng)時即有了“地中”之說,把中國考古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我們的營地設(shè)在一片很大的農(nóng)田上,扎營時,來自北京的蘇子靈跟我開玩笑,說咱們打地釘時一定要小心,萬一扎到文物就不好了——想來他的話也不假,人們說“陶寺境內(nèi)隨便一鋤頭就能挖出文物”,作為現(xiàn)今中國最早金屬樂器的那枚銅鈴,就是當(dāng)?shù)剞r(nóng)民無意間一鋤頭挖出來的。不過我也調(diào)侃了他一句:“那你也要小心,說不定你今晚扎營的帳篷下面,正好埋著一具古尸……”
西陰村:夏代以前就開始人工養(yǎng)蠶
周家莊遺址:現(xiàn)場挖出3口兒童甕棺
們又繼續(xù)出發(fā)。上午的目的地是夏縣的西陰村遺址,那里被視為我國現(xiàn)代考古史上的一塊標(biāo)志碑——它是由中國考古學(xué)者主持發(fā)掘的中國第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也是中國人首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考察隊中的岱峻先生,與當(dāng)年主持這場考古發(fā)掘的考古學(xué)家李濟先生的兒子李光謨交往甚密,一路上,他告訴了我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1926年2月,時任清華學(xué)校(清華大學(xué)前身)國學(xué)研究院人類學(xué)教師的李濟,與中國地質(zhì)調(diào)查所袁復(fù)禮考察完傳說中的堯舜帝陵后,在路經(jīng)西陰村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這塊寶地。“李濟是這樣來形容他的震撼的:‘我們突然震驚了,當(dāng)我們穿過西陰村后,突然間一大塊到處都是史前陶片的場所出現(xiàn)在眼前。第一個看到它的是袁先生。這個遺址占了好幾畝地,比我們在交頭河發(fā)現(xiàn)的遺址要大得多……’”
盡管當(dāng)年的發(fā)掘地現(xiàn)今已種上棉花,但村內(nèi)年逾古稀的老人對那位“李教授”印象依然深刻。文獻上這樣記載著中國考古史上的那次重大發(fā)現(xiàn):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李濟與袁復(fù)禮采用了“探方法”以及他們首創(chuàng)的“三點記載法”和“層疊法”,對整個遺址進行發(fā)掘,發(fā)掘出的陶片共裝了60多箱,其中彩陶片有1356塊,可謂收獲頗豐。同時,他們還在遺址中挖掘出一個龍山時期的蠶繭標(biāo)本(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將其送往美國華盛頓驗證后,證實了早在夏代以前,中國晉南廣大地區(qū)就已經(jīng)開始人工養(yǎng)蠶。
在山西考古所王益人教授的傳授下,我們不僅學(xué)會了如何使用洛陽鏟和探鏟,還學(xué)會了如何在遺址內(nèi)進行劃線、挖掘。而更令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在隨后的絳縣周家莊遺址中,我們這些“初生牛犢”的考察隊員,竟然現(xiàn)炒現(xiàn)賣,現(xiàn)場挖出了3口龍山時期埋葬兒童尸體的甕棺。
當(dāng)時,考察隊進入周家莊遺址內(nèi)的一處正在發(fā)掘的場地,大家分為幾組,分別對8個遺址坑進行發(fā)掘。突然,考古所一位專家大喊:“注意了,這里下面有東西,鐵鍬不能來了,用小鏟。”隨后,在小探鏟慢刨多時后,一口甕棺出現(xiàn)了——這是龍山時期兒童墓葬的標(biāo)志物。
“旁邊肯定還有。”王益人教授說,周家莊遺址總面積約500萬平方米,是一處以龍山時代遺存為主的大型遺址。這里曾發(fā)現(xiàn)大規(guī)模成人豎穴土坑墓和兒童甕棺葬,兩種墓葬成排分布,混雜共處,在中原地區(qū)極為少見。由此推斷,這里應(yīng)該屬于當(dāng)時的群葬區(qū),在部落成員因天災(zāi)等原因大規(guī)模死亡后,便將成人與兒童尸體混葬在一起。
果然,我們在旁邊的兩個遺址坑中,又慢慢發(fā)掘出了兩口甕棺。這3口甕棺中,有兩口里面裝有兒童骸骨,而另一口卻是空的,骸骨則被埋在棺旁,原因不得而知。此外,還出土了大量陶片和一枚鋒利的箭頭,經(jīng)專家鑒定,這枚箭頭鋒利至極,能在20米外射穿人的頭骨……
穿越中條山的虞坂古道
隨鹽業(yè)而生的血淚黃金路
第三天,考察隊接到了一項極為艱險的考察任務(wù):徒步穿越中條山中那條血淚黃金路——虞坂古道。
說到虞坂古道,首先要從聞名于世的運城鹽池說起。在古代中國,產(chǎn)鹽的地方并不少,有些地區(qū)的鹽產(chǎn)量后來也遠遠超過了運城鹽池,但是因鹽而建城的,僅有運城一地。
實際上,早在春秋之前,運城所屬的河?xùn)|地區(qū)經(jīng)濟中,一個重要支柱就是運城鹽池的鹽生產(chǎn)、運銷。城市建立后,以鹽業(yè)經(jīng)濟為核心,帶動了其他經(jīng)濟的興起和發(fā)展,因此運城就成了河?xùn)|經(jīng)濟的中心。
就這樣,虞坂古道因為鹽而誕生了。因其位于平陸縣張店一帶,是舜的先祖虞幕率領(lǐng)的部落的發(fā)祥地,所以得名虞坂。相傳虞氏部落居于虞坂上的虞城,部落成員從河?xùn)|鹽池運鹽,經(jīng)過這條古道,將鹽送往河南新鄭一帶的軒轅黃帝部落,黃帝部落正是吃著從這條大道運來的鹽,打敗了蚩尤部落,占領(lǐng)了中原。
當(dāng)然,這個傳說是否真實,以及這條古道修建于何時都已不可考,但現(xiàn)在看來,這條古道對于當(dāng)時晉南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河?xùn)|鹽池是我國最早開發(fā)的鹽池,早在原始社會,先祖?zhèn)兙驮谀抢镩_采食鹽;盛唐時期,河?xùn)|鹽業(yè)稅收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八分之一,成了唐帝國的錢袋子。到了明代,這里的鹽業(yè)更是達到了頂峰——作為運城鹽池最早開發(fā)的運鹽古道,從今運城鹽池出發(fā),登中條山后,途徑虞坂,運至圣人澗,然后在茅津渡裝船過黃河,運往中原及以南地區(qū),因此可以說,它就是一個國家的命脈。
我們一路前行,腳下是坎坷不平的青黑色硬石道,道路兩旁是纏滿荊棘藤的山棗樹,稍不注意,身上就會被樹藤上的刺劃出血痕,這就是我對這條古道最初的印象與體驗。徒步行走了數(shù)公里后,我似乎又看到了當(dāng)年這條鹽道上車馬交錯、鹽運繁忙的壯觀景象。那時運鹽民工為了生計,不惜以生命為代價,鋌而走險,墜崖身亡的悲劇時有發(fā)生,這些慘象也一一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虞坂古道之險,從古詩中就能讀到:“孤勢卻成三晉險,削痕爭道五丁開。路在缺嶼連如斷,人在回崖去若來……”
同時,我們還在古道上聽到了那一個個陌生而又熟悉的故事。比如那個關(guān)于馬的傳說:遠古時期,在尚未發(fā)明釘馬掌來保護馬蹄的技術(shù)之前,當(dāng)負重的馬踩在如錐的尖石上,鉆心的刺痛就會令馬匹前撲摔倒,牙碎血噴——這刺人心肺的慘狀,也就為一項偉大的發(fā)明帶來了機緣,這個發(fā)明者,名叫孫陽,在歷史上被稱為“伯樂”,相傳他不僅在這條古道上發(fā)現(xiàn)了那匹外表就是普通馱馬的千里馬,還發(fā)明了釘馬掌護馬蹄的方式。
再如那個“假道伐虢”的故事。春秋時期,虞坂古道上的鎖陽關(guān)成為3個國家的分水嶺:南麓是山水相連的虞、虢兩個小諸侯國,北邊則是地處汾河谷地,正急于四處擴張的晉國。晉獻公,這位擁有強大國力的晉國國君,把國寶棘璧屈馬當(dāng)作誘餌下給虞公,條件是借一條消滅虢國的道路,面對唾手可得的稀世寶貝,虞公慷慨借道,作壁上觀。所以,公元前655年,借道的晉國大軍穿過虞坂古道,先滅了虢國,于回師途中又順勢滅掉了虞國,只留下虞公忠臣百里奚“擇良木而棲”的選擇,與“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的警世寓言流傳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