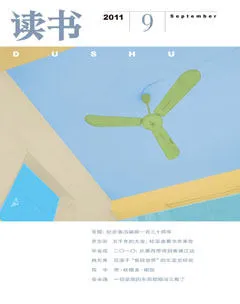魯迅與日本書
一、外文:半數藏書,半數業績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自從魯迅說了這話以后,對此如何理解就一直爭論不斷,直到現在。不過就其躬行而言,至少有一半還是“合得上”的,即后一半,“多看外國書”。
根據《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內部資料,北京魯迅博物館一九五七年刊印)檢對,魯迅所藏中、外文書籍和期刊有三千七百六十種,其中,中文一千九百四十五種,外文一千八百一十五種,所占比例為52%對48%,幾乎一半對一半。“多看外國書”,翻譯外國書,甚至用日文寫作,的確是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開山作家的又一大特色,這樣的作家到現在也不多見,而在同時代的作家中,恐怕也只有周作人可與之比肩。二○○三年夏,曾去中國現代文學館參觀。每個作家的展區都設有藏書專架。“魯迅展區”與其他作家展區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擁有大量的外文藏書,而在其他也同樣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書架上幾乎看不到這種情形,至多只有幾本外文詞典或外語教材之類。這一發現,可謂自己的一大收獲,過去竟未意識到,魯迅的業績其實可由他的藏書數量獲得物理性印證;同理,也可以印證其他作家為什么沒留下魯迅那樣的——至少是翻譯方面的成績。據統計,魯迅的翻譯作品,“涉及十五個國家,一百一十多位作者,近三百萬字”(顧鈞:《魯迅翻譯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九年版)。
這三十年來所通用的魯迅文本是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本《魯迅全集》,二○○五年同一出版社又重出修訂本,增加到十八卷。但與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島”首次出版的《魯迅全集》相比,這兩個版本雖然修訂仔細,注釋翔實,卻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全集”。因為它們在內容上是不全的,并沒有把魯迅的翻譯包括進去——或許竟認為翻譯可以不計也未可知。比較而言,上述“孤島”版《魯迅全集》二十卷至少在凸顯魯迅著述業績的特色方面是“全”的,前十卷為魯迅自創文字,后十卷則是翻譯。后來再出就拆開了,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出十卷本《魯迅全集》和十卷本《魯迅譯文集》。但這樣“拆”著出顯然很成問題,據說尼克松來訪時,周恩來要送《魯迅全集》做禮物,卻找不出一套“全”的,最后只好把最早的那套“孤島”版找出修訂重排一回,這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二十卷本。由于印數不多,現在也很難找到或找全了吧。到了前年又一套二十卷本——《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王世家、止庵編,人民出版社二○○九年版)出版,在“求全”的意義上,“魯迅全集”的編輯、校訂總算跨出新的一步,不僅可知魯迅著譯全貌,亦可了解伴隨其生平的工作歷程,其版本學和文獻學意義皆不言而喻。就中,為過去版本所隱去而不太被重視的占半數的翻譯,無疑又為今后的魯迅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至少可以知道,迄今為止魯迅的翻譯文本還缺乏作為研究結果的必要的注釋(而在此意義上,既往對包括魯迅“硬譯”在內的翻譯的批評大抵可以無視,因為它們缺乏作為批評基礎的文本探討這一前提)。這是今天重提魯迅與外文書關系的意義所在。可以說,如果魯迅不讀外文書,便不會有遠遠超過他本人創作而占“全集”半數的翻譯文本,至于魯迅對外文書的閱讀和翻譯實踐對他自己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則是更深層次的問題。
總之,魯迅的半數業績,可以從他占總量半數的外文藏書和他的“多看外國書”獲得相應的答案。
二、日文書及其意義
在魯迅的外文藏書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日文書占了大半,據上面提到的“藏書目錄”,“日文計九百九十三種,俄文計七十七種,西文計七百五十四種”。所謂“西文”是指德、法、英和其他語種,加上俄文的,共有八百三十一種,按百分比計算,日文書與其他語種的比例為54%對46%。日文是魯迅最為擅長的外語,所獲外文信息的大半也是來自日文,因此,日文書之于魯迅的意義不言而喻。
去年,國內和在日本的一些學者提出一項研究計劃,以北京魯迅博物館“藏書目錄”為依據,展開“魯迅日文藏書研究”,也便是意識到了日文書在“魯迅”當中的重要。
然而,還有另外一種情況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不見于“藏書目錄”而事實上魯迅又閱讀過并且在“魯迅”當中留下痕跡的那些書籍。這意味著魯迅實際看到的書籍比他留下來的“所藏”要多。這種情形在日文書方面尤其突出。據中島長文先生調查統計,有“確證”的魯迅“目睹日本書”有一千三百二十六種(中島長文編,刊《魯迅目睹書目——日本書之部》,宇治市木幡御藏山,私版三百部,一九八六年)。這一研究成果表明,魯迅實際看到的日文書較之“藏書目錄”的九百九十三種多出三百三十三種,超出率高達33.5%。中島長文先生的這部力作完成于二十五年前,而依近年來筆者查閱所獲之管見,還有不少“日本書”并沒被包括到“魯迅目睹書目”當中,尤其是明治時代的出版物。僅舉幾個例子在這里。
其一,“大日本加藤弘之《物競論》”(《周作人日記》一九○二年“正月卅日”,西歷三月九日),此系魯迅留學臨行前送給周作人的楊蔭杭譯本,最初連載于《譯書匯編》一九○一年第四期、第五期、第八期,而周氏兄弟所見“洋裝”本,當是譯書匯編社一九○一年出版的單行本之第一版或第二版。問題在于有不少研究者認為這個譯本源自加藤弘之的《人權新說》,誤矣,其真正底本為同一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即《強者之權利之競爭》(《強者ノ權利ノ競爭》,日本哲學書院一八九三年版)。
其二,“澀江保《波蘭衰亡戰史》”(出處同上)。這本得自魯迅的書,令周作人不斷反復“閱”,而且“讀竟不覺三嘆”(三月十九日)。該書系東京譯書匯編社一九○一年版漢譯單行本,原書為東京博文館“萬國戰史”叢書全二十四冊中之第十編,出版于明治二十八(一八九五)年七月,顯然是周氏兄弟早期的一個關鍵詞——“波瀾”——的來源之一。而另一個關鍵詞“印度”亦可找到出處,即同一套“萬國戰史”中的第十二編《印度蠶食戰史》,它雖不見于周作人日記,卻也是當時學子所廣泛閱讀的出版物。據《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實藤恵秀監修,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輯,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年版),該書亦有杭州譯林館一九○二年出版的單行本。
還有一本是《累卵東洋》。原書『累卵の東洋』,系大橋乙羽所作政治小說,在當時風靡一時,有博文館和東京堂兩種單行本,都在一八九八年出版。“印書館愛善社”一九○一年五月出版漢譯本,譯者“憂亞子”。周作人在魯迅去日本后不久購得此書,又花了很長時間斷斷續續閱讀,并且認為譯得很糟,在日記中有告誡自己今后譯書當以此為戒的話。
以上三個例子,既不包括在北京魯博“藏書目錄”中,也不見于《魯迅目睹書目》,而又是周氏兄弟實際上閱讀過的書籍。可以據此推測,魯迅在其留學前、留學中和留學后所閱讀的日文書目要遠遠大于目前所知道的范圍——雖然誠如中島長文先生所言,要想像后來有“書賬”的時代那樣“復原”其留學時期所閱書目是相當困難的。不過也并非全無辦法,除了接下來將要談到的先學們由魯迅留學時代的文本中來探討的基本“硬”辦法之外,新的嘗試也會帶來新的收獲。例如,正在京都大學留學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雅娟最近就做了一項“很笨”卻又富有實際意義的工作,那就是在《周作人日記》里把那些日文書目一個一個找出來。從李同學所列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四年的書目來看,這一期間周作人所閱日文書大約有一千四百八十種。筆者以為,截止到一九二三年他們兄弟失和以前的這一段,周作人所閱日文書中相當大一部分是不妨作為潛在的“魯迅目睹書目”來預設的。
其次,上述三例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清末學子的一般讀書狀況和在所謂“西學東漸”背景下的知識傳播路徑。在“中西”這個大框架下探討近代新知,一般來說“大方向”沒錯,但僅僅靠一個大框架也難免淺嘗輒止或脫離具體歷史過程。事實上對于包括周氏兄弟在內的那一代讀書人來說,留學之前讀到的“西學”,大多還是漢譯的日文書,而留學以后則逐漸轉向直接借助日文來閱讀;從內容上來說,有些是“西書”日譯進而再到漢譯,有些則是經由日本“濾化”過的西學,亦如上面所列三種,《物競論》和《累卵東洋》是日本人汲取西學后的原創,涉及“波瀾”和“印度”的兩種則是對西學的整理和譯述。這種知識格局和傳播路徑,至少在魯迅留學那個時代,自始至終幾乎沒發生過什么改變,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詞匯研究者就承載近代知識概念的詞匯所發表的意見,那就是“西學來自東方”,西學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轉道日本而來的(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中華書局二○一○年版)。
那么對于魯迅來說“日本書”意味著什么?答曰,是他獲取新知亦即廣義“西學”的一條主要通道。而對于旨在探求“魯迅”當中“中西文化”的現在的研究者來說,則是一道必須要履行的從魯迅那里跨向“西學”的“手續”。少了這道“手續”,所謂“西學東漸”的歷史將缺少具體環節。這是探討魯迅與日本書之關系的另一層意義所在。
三、關于澀江保日譯本《支那人氣質》
有朋友曾經問,魯迅讀了、也收藏了那么多日文書,為什么就非得這本不可?回答是,就像您書架上插的那些書,甭管多少冊,最終對您能有決定性影響的可能就那么幾本,甚至只一本,或者竟一本也沒有——這與“交人”沒什么不同。能像《支那人氣質》那樣在“魯迅”當中留下大量影響“確證”的日本書實在并不多見,為什么不是它呢?
這是一個“西書”日譯,再到漢譯的典型的例子。原書為阿瑟·亨德森·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所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八九○年初版于上海(筆者在哈佛大學圖書館曾確認這一版本),然而并沒引起中國的注意,倒是在西方讀者中獲得很大反響,遂有一八九四年紐約佛萊明公司的“修訂插圖”版,即“REVISED,WITH ILLUSTRATIONS”。這是第二版,原書上有“SECOND EDITION”的字樣,后來這個版本流傳世界——也許正是由于這個緣故,一些學者以為該版是“第一版”,這是不對的。兩年以后,日本明治二十九年即一八九六年,東京博文館出版了澀江保以紐約版為底本的日譯本,書名《支那人氣質》。一九○三年上海作新社根據澀江保日譯本翻譯出版漢譯本,書名《支那人之氣質》(準確地說,是封面、封二所標書名,目錄、正文首頁、尾頁書名沒有“之”字,與日譯本書名相同)。從英文原書到日譯本,再到漢譯本,這一“自西向東”的過程歷時十年,如上所述,中國非直取于西,而轉借于東。
此后百年,以上三種版本幾乎沒在中國留下痕跡,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關于“史密斯”和他的這本書才又熱鬧起來。據筆者所見,到目前為止,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譯本不下十七種版本。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跨世紀的版本“大遷徙”?這與魯迅學者張夢陽先生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的一項研究有關。他率先提出了“史密斯與魯迅”的關系,并著手探討史密斯的這本書對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影響(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年刊》,一九八○年;北京魯博《魯迅研究資料十一》,一九八三年),又與他人合譯史密斯紐約版原書,還寫了體現其系統研究的《譯后評析》附于書后(《中國人氣質》,甘肅省敦煌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毫無疑問,這項研究是開創性的。首先,它帶出了一大批文本成果,除了譯自史密斯原書的各種中譯本之外,最重要的是一九○三年作新社漢譯本的發現(劉禾:《跨語際實踐》,三聯書店二○○二年版)和對其加以整理校注出版(黃興濤校注:《中國人的氣質》,中華書局二○○六年版。順附一句,作為一個校注本,在“書名”上有遺憾,應該取原名《支那人之氣質》才符合歷史事實);其次,帶動了后續研究,也開啟了一種研究范式,那就是無形中構制了一個“史密斯與魯迅”=“西方與東方”的思考框架,后來的研究者都自覺不自覺地在這一框架內展開思路,文本操作囿于“英漢”之間不說,諸如“一個外國傳教士,一個中國啟蒙者……”(孫郁:《魯迅與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斯密思的書……恰巧是魯迅國民性思想的主要來源”(劉禾,同上)之類表述都是很常見的,就連上面提到的“校注本”也沒標出這個譯本的準確來源——即現在已經知道的澀江保譯本——而只在封面上標示“〔美〕明恩溥(Arthur H. Smith)著”。前面說過,“西學東漸”“大方向”正確,但僅以此去“套”,就不一定符合魯迅的實際。張夢陽先生當時就已經意識到魯迅讀的“當然是澀江保的日譯本,而非英文原版”(同上,一九九五年),但由于沒找到日譯本,才沒能進一步展開研究。
這是筆者重視澀江保《支那人氣質》這個日譯本及其出自這個譯本的作新社漢譯本的理由。日譯本與原書的最大不同還不僅僅是語言轉換,更主要的是它承載了原書所不具備的內容:二十一張圖片、譯成中文總字數超過三萬字的五百四十七條眉批、四百零三條夾注和尾注都是原書沒有的,它已經是“另一種東西”,這些與本文合在一起才構成魯迅與“西學”的具體關聯。日譯本及其譯者研究、與魯迅文本的比較研究以及該版本的“日譯漢”是筆者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項工作。至于作新社漢譯本,則以為不能排除魯迅目睹的可能性,但這需要另外撰文討論了。
四、關于魯迅的“進化論”
在學讀書時由劉柏青先生的《魯迅與日本文學》(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開悟中國現代文學還有“日本”這一門,當從伊藤虎丸等先生的書中得知留學時代的“魯迅”身上有那么鮮明的“歐洲”和“尼采”(請參閱《魯迅與日本人》,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年版;《魯迅與終末論》,三聯書店二○○八年版)真是大吃一驚,再讀北岡正子先生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何乃英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以及日文《野草》雜志一九七二到一九九五年的二十四回連載),簡直是給“震了”,完全不同于只囿于“古漢語”境界的那種解讀,呈現著一個在傳統文獻中所看不到的既豐富廣泛而又深刻的“近代”——反過來說,也都是文本作者一點一滴采摘、咀嚼、吟味、融會到自己的意識和文章里來的。眾多先學類似上述的工作,揭示出留學時代的“周樹人”如何生成為后來“魯迅”的具體過程和必要條件。“日本書”在這一環節的出現并非有意為之——竹內好甚至認為魯迅拒絕并排斥了日本的“近代”——而是客觀研究發現的“偶然”事實。
曾幾何時,自己也在不知不覺當中加入到這“找”的行列。先在“明治時代”,在“日本書”中尋找梁啟超乃至魯迅那一代人的“思想資源”,進而檢討他們如何整合、運用這些資源,生成為自身的主體意識。關于魯迅的“進化論”研究也是這方面的課題之一。
首先遇到的問題是魯迅的“進化論”到底來自哪里?一般標準的回答是“來自嚴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承認“部分來自日本”,但有多少來自日本卻并不了然。就目前的階段性結論而言,作為“知識”的進化論主要來自日本,而且之于嚴復的關系是一個進一步擴充知識體系、深化理解的過程,筆者將這一過程概括為從“天演”到“進化”。有關這一研究的綜合報告,將見于明年出版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關于翻譯概念在中國的展開之研究》。其結論支撐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中島長文先生的研究,他以魯迅的《人之歷史》(一九○七年)為例,指出“材源”來自《天演論》的僅有兩處,其余有五十七處皆來自日本的進化論(《藍本〈人之歷史〉》,《滋賀大國文》,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另一個是筆者關于丘淺次郎的研究,在將其文本與魯迅文本進行比較之后的“實證”結論是,除進化論知識本身之外,兩者的“問題發想”、運用素材甚至寫作風格都具有相當大的近似性。“丘淺次郎”的“斷片”散見于各個時期的“魯迅”當中(《丘淺次郎與魯迅》,佛教大學《文學部論集》,二○○三、二○○四年)。順附一句,私以為,翻譯除外,在很多情況下,魯迅文本中提到的人或書籍,大抵還都與他有某種“距離”,那些“只言片語”少提或者竟不提的,可能反倒離他更近,挑眼前的說,“安岡秀夫”、“《支那人氣質》”和“丘淺次郎”可以拿來做代表。“丘淺次郎”是消失在“魯迅”身影下的——從未提到過。
五、“吃人”及其他……
已經沒有篇幅了,卻還有那么多“日本書”沒有講完。最近完成了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東京富山房一九○七年版)的翻譯,目前正在為這項歷時四年的工作寫導讀。除了“國民性”一般問題外,可以具體到魯迅“吃人”意向的創出與這本書及其同時代話語的關聯。還有那本在題材上頗顯“游移”的《故事新編》,其實也沒出當時的出版物——當然也是日本書,但這要另找機會再談了。
總之,探討“魯迅”當中的“日本書”問題,其根本意義在于揭示在“被近代化”的過程中,主體是如何容受并且重構這一“近代”的。魯迅提供的不是一個“被殖民化”的例子,而是一個主體重構的例子——如果他能代表“中國近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