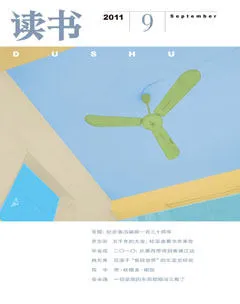認真對待達瑪斯卡
一
在當今世界比較法領域,米爾伊安·R.達瑪斯卡(Mirjan R. Damaka)無疑是一朵奇葩,一位前無古人甚至可能后無來者的傳奇人物。這或許與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和學術背景有關:達瑪斯卡一九三一年十月出生于一個居住在斯洛文尼亞的克羅地亞家庭,在南斯拉夫就讀本科、研究生,獲得法學學士、博士學位,后任法學教授,其間還曾在法院工作,擔任過克羅地亞議會刑事司法改革委員會主席。此外,他還曾求學并任教于盧森堡國際比較法學院。不惑之年,方遠渡大洋,任教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耶魯大學。六十多歲后,又投身于國際刑事法律的實踐與研究。然而,達瑪斯卡眾所周知的大師地位根本上奠基于其難望項背的學術成就。二○○九年,達瑪斯卡已年屆七十八歲退休,美國比較法學會舉行隆重典禮,授予達瑪斯卡終身成就獎,時任會長的西蒙·C.塞繆尼德斯(Symeon C. Symeonides)稱贊道:“達瑪斯卡無論在美國之內還是之外,無論對比較法還是一般法律都做出了非同尋常的終身貢獻。他形塑了我們當下關于比較法的觀念,其學術理論有著巨大影響與開創性,沒有任何在世的比較法學者像他那樣,學術見解構成五次專題研討會的主題。”同樣,耶魯大學法學院在二○○八年專門為達瑪斯卡舉辦學術研討會,時任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哈羅德·考赫(Harold Hongju Koh)教授在致辭中也流露出對達瑪斯卡的敬意,他說:“達瑪斯卡是一個永不停歇的攀登者,是法律程序類型學的國際象棋大師,是鏈接不同法律文化的知識橋梁,總之,在一個全球化不斷推進的時代,達瑪斯卡理論觀點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
達瑪斯卡并不是一個知識構造褊狹且意識形態色彩鮮明的學者。一方面,在學術研究中,他總是自詡為法學僑民,力圖站在新、舊大陸之間的大西洋中間島嶼上觀察現實。在一個英美中心主義立場似乎難以撼動的年代,達瑪斯卡的觀點能夠跨越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得到重視——或作為思想原點予以認可、或作為批評對象展開駁斥,這當然是其深邃理論洞察力與超凡學術影響力的集中表現,但更直接體現了其基于個人體驗對諸多法系的深度把握。另一方面,達瑪斯卡在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上也力圖維持一種“公允”立場,既不偏從控方,也非傾向辯方,他視犯罪控制為制度的“本我”,人權保障為制度之“超我”,認為健康的刑事訴訟制度不能讓任何一方過度強大。應將犯罪控制裝置文明化,但不應設置過度的障礙。事實上,達瑪斯卡骨子里便有一種不服從傳統的反思意識,喜歡發出點不同凡響的聲音,且這種話語并非刻意而為,而是有著厚重的經驗與理論基礎。
與西方學者對達瑪斯卡理論的高度重視不同,在中國,雖然已經譯介了其標志性的兩本著作(《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與《漂移的證據法》),并且將其散見于刊物的證據法論文匯集成冊(《比較法視野中的證據制度》),但他的理論還是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冷遇。這可從訴訟法學特別是比較訴訟法學著述的引證得以窺探,很多學者,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學者很少引述達瑪斯卡,遑論將其作為影響自己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達瑪斯卡關于歐美刑事訴訟的新類型劃分,還是其關于法律移植的重要見解,似乎都并未成為中國學人觀照西方制度、考慮如何改革的重要歸依。在我看來,這一現象無疑透露出悖謬與反諷的意味。悖謬在于,我們一方面不斷強調要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尤其是英美對抗制),另一方面卻又對達瑪斯卡這樣對法律移植問題有著深刻洞見的西方學者熟視無睹。反諷則表現為,在西方學者普遍認真對待達瑪斯卡時,我們卻似乎無動于衷。
二
盡管達瑪斯卡寫作了十三本書、超過九十篇的論文,但其特立獨行的見解集中體現在《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與《漂移的證據法》兩本著作中。前一著作中,不滿于傳統的對抗制與職權制二元程序類型模式,達瑪斯卡引入權力組織結構與政府目的兩個宏觀政治性影響因素,從而提煉出讓人耳目一新的程序類型模式。后一著作中,達瑪斯卡系統指出了支撐英美證據制度的三個基礎性要素,爾后論析這三根支柱均已出現不同程度的崩塌,從而致使證據法如同無根的浮萍漂向遠方。
《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可以說是達瑪斯卡在比較程序法領域的巔峰之作。事實上,早在該書出版的十一年前,達瑪斯卡就曾寫過一篇與該書觀點有關聯的長篇論文:《權力結構與比較刑事程序》(Structures of Authority and Compatative Criminal Proc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