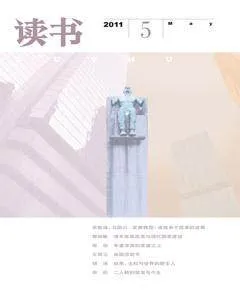黃炎培在辛亥
百年前的一九一一年我國爆發(fā)辛亥革命,結(jié)束兩千多年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成為上世紀(jì)影響我國歷史進(jìn)程的最重大事件之一。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時的一九六一年北京等地安排了有關(guān)的紀(jì)念活動。在我手頭保存著當(dāng)年紀(jì)念活動的有關(guān)資料:由與辛亥革命密切有關(guān)的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和國務(wù)院總理周恩來共同牽頭,沈鈞儒、陳叔通、程潛、張治中、邵力子、蔡廷鍇、蔣光鼐、張奚若、吳玉章、李書城、熊克武、李六如等,以及帶兵驅(qū)逐宣統(tǒng)皇帝的西北軍舊將鹿鐘麟將軍、民國教育總長朱啟鈐等共約百人聚集一堂,而坐在董老和周總理身旁的辛亥老人中為首的即是我的父親黃炎培。
一、虎口余生
父黃炎培,一八七八年生于上海浦東川沙內(nèi)史第我家老宅(十五年之后宋慶齡等宋氏姐弟陸續(xù)在此宅出生,胡適亦曾在此宅借居)。父十三歲喪母,十七歲失父,家道中落。受過私塾教育又中了舉人的黃炎培一九○一年考入南洋公學(xué)(今上海交大)蔡元培為總教習(xí)的特班,與李叔同、邵力子、章士釗等人同學(xué)。一年多后參與了對學(xué)閥的罷課學(xué)潮,離校回到浦東。
黃炎培回到家鄉(xiāng),正好廢科舉、興學(xué)堂之風(fēng)開啟,清政府公布高等中小學(xué)章程,命令各省把書院改辦學(xué)堂。經(jīng)歷了學(xué)潮洗禮,年方二十四歲的黃炎培抱定辦學(xué)的決心,“要救中國,只有辦學(xué)堂”(黃炎培:《川沙公立小學(xué)校史最初的一頁》,載《川沙縣縣志》,7頁),開始了他幾十年不渝的辦學(xué)歷程。當(dāng)時川沙縣有個觀瀾書院,黃與張訪梅、陸逸如等友人欲將其改造為學(xué)校,一番策劃后先上書川沙廳,又在寒冬冒風(fēng)雪坐船到南京上書兩江總督張之洞,終于在黃等人不領(lǐng)薪水、自理膳食等條件下批準(zhǔn)由黃任學(xué)堂總理。一九○三年初川沙小學(xué)開辦。不久,黃又在家鄉(xiāng)辦起開群女學(xué)。
辦學(xué)初年,黃全家依靠他當(dāng)年投書書院所得獎金之余維持了年余。除管理學(xué)校并親自授課外,黃覺得還應(yīng)多做些發(fā)動群眾的啟蒙工作,于是每逢假日約上好友,帶著學(xué)生,扛上黑板,拿上板凳,來到鄰里,來到城墻上,教民眾識字算術(shù),或舉行演講會。川沙城墻建于明朝,古風(fēng)猶在,系當(dāng)?shù)赜斡[勝地,黃在此演講,指貶時弊,抨擊列強,吸引來眾人。于是將活動擴(kuò)至鄰縣南匯。一九○三年夏,黃與好友張訪梅、顧次英等來到南匯重鎮(zhèn)新場演說,百里之內(nèi),舟車云集,空前轟動。當(dāng)時震驚全國的“《蘇報》案”剛發(fā)生,《蘇報》因刊載鄒容的《革命軍》遭清政府查封,章太炎、鄒容下獄,各地捉拿革命黨,空氣十分緊張。六月十八日黃第一次講演,二十三日第二場講演正在進(jìn)行,南匯知縣戴運寅接痞棍密報說黃炎培等人演說誹謗皇太后,即派兵抓捕了黃等四人,并貼出告示:“照得革命一黨,本縣已有拿獲,起得軍火無數(shù)。”夸大上綱以圖邀功,為此速電稟兩江總督及江蘇巡撫,前者回電令“就地正法”,后者回電令“解省訊辦”,二者令歧,戴知縣再電請示,來回耽誤了三天時間。其間南匯青年展開營救,找到上海基督教總牧師步惠廉,同時那位出資辦川沙小學(xué)的浦東房地產(chǎn)商楊斯盛拿出五百元交步惠廉,請來美國律師佑尼干。兩位洋人直奔縣衙找到戴,在督撫會銜電令“就地正法”午時三刻到達(dá)之前的半個小時,保釋出黃等四人,并徑直踏上赴上海汽輪,又連夜離滬,乘坐“西伯利亞輪”駛出吳淞口前往日本。虎口余生下的四青年,在茫茫海上漂蕩,在船上黃等改名以銘志,黃炎培原號楚南,改為韌之。韌字的含義是刀,是牛皮。要殺敵,要堅忍。
這一新場鎮(zhèn)風(fēng)波在上海引起巨大反響,章士釗主辦的《國民日報》等媒體連篇累牘報道。上海新戲舞臺上將之搬上舞臺,說二十五歲年輕的革命黨人黃炎培,被清廷抓去險些殺頭云云。黃炎培的名字連同這場風(fēng)波一起在上海傳播開來。
二、入同盟會
一九○四年春黃炎培返國,繼續(xù)他的辦學(xué)事業(yè)。在上海南市竹行弄辦東城女學(xué),又協(xié)助在日本期間結(jié)識的劉季平(劉三)創(chuàng)建麗澤學(xué)院。
一九○五年二月鄒容在獄中病死,黃炎培受蔡元培委托,負(fù)責(zé)處理鄒喪事。為這樣一位被清廷視作大敵的獄中要犯治喪,要冒很大的政治風(fēng)險,但黃毅然接受。黃聯(lián)絡(luò)劉季平,動員劉捐出自家宅旁土地作為鄒容墓地,把鄒遺體先安葬下來,整樁事情辦得十分得體利落,但鑒于當(dāng)時政治環(huán)境,未能修建鄒容紀(jì)念塔。
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蔡元培被指派為上海分部負(fù)責(zé)人。一個月后蔡召黃來到在上海西昌壽里六十二號自己家,夜深人靜時蔡嚴(yán)肅地對黃說:我們中國的前途極危,你知道么?黃肅目相答知道。蔡又說:要救中國,唯有革命,你同意么?黃點頭答是,于是蔡介紹了新成立的同盟會,問黃愿參加否,黃起身正立,莊嚴(yán)地說:“刀下余生,只求于國有利,一切唯先生之命是從,當(dāng)然愿意參加。”次日深夜,黃再次來到蔡家,蔡拿出同盟會宣誓書:“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quán)。”黃莊嚴(yán)地舉手宣誓,從此成為同盟會會員了。
一九○六年政治空氣漸趨寬松,六月因《蘇報》案入獄的章太炎出獄,蔡元培與黃炎培前往迎接,把章送往中國公學(xué),又怕清廷節(jié)外生枝而立即把章送到開往日本的輪船上。章到日本后成為同盟會機(jī)關(guān)報《民報》主筆,寫出一系列犀利的討清文章。在忙于迎送安排章太炎的同時,黃重新啟動建造鄒容紀(jì)念塔事。黃求助老友楊斯盛承接建塔工程,由楊接手得以完成,其間策劃、組織、安排、實施,一系列工作都由黃操持,二十七八歲的黃得以歷練。七月三日,鄒容紀(jì)念塔落成,舉行了隆重的紀(jì)念儀式,各界人士紛紛前往,在紀(jì)念塔前紀(jì)念這位反清義士,蔡元培致詞,此成為上海乃至全國的頭號新聞。而成就此事之捐地者乃劉季平,造塔者乃楊斯盛,動員及組織策劃且串聯(lián)而成者乃黃炎培。
同年九月,蔡元培要赴德國留學(xué)而去北京等候派遣,請黃接手自己同盟會上海分部負(fù)責(zé)人的職務(wù)。蔡把同盟會上海分部會員共四十九人的名冊、電碼和文書交給黃,每一會員名字后面都有兩個字的商號名稱作代,其中有黃花崗起義組織者趙伯先(商號“震康”)、后來被陳其美殺害的光復(fù)會領(lǐng)袖陶成章(商號“濟(jì)世”)、后來密謀炸死清廷出國考察五大臣的安徽桐城人士吳樾,名冊上還有黃早已熟悉的章士釗、柳亞子、俞子夷等,有些人之前黃并不知其已加入同盟會。除同盟會會員名冊等機(jī)密文件外,還有更為機(jī)密的國民教育會暗殺團(tuán)名單和光復(fù)會文件等,黃把這些密件藏在線裝詩韻去聲九泰蔡字韻頁的折頁中,即使被查也難找到。
黃接手同盟會上海分部后全力以赴。當(dāng)時的上海已是全國商業(yè)、貿(mào)易、金融中心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中心。各地同盟會員常來上海,或路過轉(zhuǎn)赴各地。作為同盟會上海地區(qū)當(dāng)家人,黃的工作相當(dāng)繁雜,要送往迎來,安排食宿,傳遞信息,布置工作,且都是在清廷統(tǒng)治下秘密進(jìn)行,黃在上海陸續(xù)積累了一些人脈,所以事情安排得當(dāng)。黃晚年時還記得,曾接待廖仲愷先生從日歸來。一次云南來電,四位干崖土司女青年要赴法留學(xué),從昆明來到上海,黃與較為同情中國革命的法租界關(guān)系很熟,于是將她們安頓在法租界。一日,法租界總巡麥蘭請黃速去,黃猶豫而由身旁的楊斯盛代黃去,麥蘭見黃本人未來而不置可否。次日黃去見麥蘭,麥告孫中山昨路過上海,兵艦停在吳淞口想要見黃卻未得,現(xiàn)已離滬,那日柳亞子、陳陶遺、高元梅等人坐了小劃子見了孫中山。
辛亥之后黃見到了孫中山。孫卸職后住在上海閉門寫《孫文學(xué)說》,召黃晤談,請黃對其未完成的著作提意見,中午孫偕宋慶齡與黃共進(jìn)午餐。
三、社會組織
武昌起義爆發(fā),各地紛紛響應(yīng),先后獨立,但總體上社會秩序并未大亂,重要原因是我國尤其是江南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經(jīng)濟(jì)與社會的運轉(zhuǎn)已經(jīng)基本依托于逐步發(fā)展起來的地方社會組織。而在上海,在江蘇,黃炎培都積極涉足了當(dāng)?shù)氐纳鐣M織。如同黃走上革命黨人道路是憂國憂民使然,涉足社會組織亦是,尤其從事教育,黃必然涉入。
一九○二年開始興學(xué)辦教的黃炎培首先接觸到張謇為首的江南教育界人士。張謇出身于務(wù)農(nóng)兼經(jīng)商的底層人家,十五歲即中秀才,但系因其祖上無秀才身份而冒充他人弟,“冒籍”參考,因而五年之后的一八七三年才得歸原籍獲得承認(rèn),經(jīng)歷了多年坎坷的幕僚生活后大器晚成,四十一歲時考中狀元。但張并不熱衷于仕途,面對列強入侵,國力衰落,尤其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戰(zhàn)敗于日本之后,憂國憂民的張走上實業(yè)救國之路。張先在南通辦起大生紗廠,后又辦起通海墾牧公司,經(jīng)營水運的大生輪船公司,進(jìn)而創(chuàng)辦資生鐵廠,又有染織廠、面粉廠、油廠等系列企業(yè),以及創(chuàng)辦南通淮海實業(yè)銀行、印書局、電話公司等。幾乎與黃炎培起步辦學(xué)的同時,一九○二年張開始籌辦南通師范學(xué)校。張謇的活動不止于南通,上海、南京進(jìn)而江蘇全省各地均是他活躍的地方。一九○五年底,張在上海籌設(shè)江蘇學(xué)務(wù)總會,后改名為江蘇教育總會,張謇任會長,集中了包括黃炎培在內(nèi)還有袁希洛、沈恩孚、姚子讓、吳馨、林康侯、龔杰、方還、雷奮、曾樸等上海和江蘇的一批精英人士,或是新式學(xué)堂的負(fù)責(zé)人、或是報館的主持人,還有些則是民營企業(yè)的新式企業(yè)家。教育總會成了上海和江蘇的精英們匯集的大平臺,在此相識,交流經(jīng)驗,交換信息,互相支持,而其交流的內(nèi)涵和產(chǎn)生的影響力所及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教育界。黃炎培先是其中樞機(jī)構(gòu)的干事會七八個干事員之一,處理教育會日常事務(wù),解決各地反映上來的辦學(xué)問題,這一職務(wù)使他眼界大開,由浦東、上海,進(jìn)而到江蘇。當(dāng)時新學(xué)初起,體制不一、規(guī)章混亂,且官場弊端浸入學(xué)校,例如江蘇江陰南菁書院由省上委派的紳士領(lǐng)導(dǎo)無方,財務(wù)混亂。對此,黃炎培兩度赴江陰調(diào)查處理,提出全面整頓方案,獲兩江總督端方支持,最后將其改建成省屬高等學(xué)堂并附設(shè)南菁中學(xué)。
江蘇教育會不僅涉足教育,而且隨其威望日高,成員日多,更多地深入上海與江蘇的社會事務(wù)。如在江蘇與浙江發(fā)生的反對清廷將鐵路收歸國有的保路運動中,教育會首當(dāng)其沖,在全省的民眾抗議浪潮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從而在上海和江蘇贏得了更多的話語權(quán)。
黃炎培擔(dān)任干事員同時又升任常任調(diào)查員,常奔波于全省各地。一九○九至一九一一年,他足跡遍及全省六十三個縣中的四十七八個縣,達(dá)全省四分之三,積累了大量感性認(rèn)識,從而對當(dāng)時我國教育和社會狀況有切實的了解,為辛亥之后黃主持和推動江蘇省教育改革以至后來發(fā)起我國的職業(yè)教育奠定了基礎(chǔ)。
江蘇教育總會成立第二年,黃即牽頭成立了川沙分會。一九○六年黃炎培在楊斯盛鼎力支持下于浦東六里橋創(chuàng)辦起浦東中學(xué)、浦東小學(xué)。浦東中學(xué)后來名滿全國,與天津南開中學(xué)并列,稱作“南浦東,北南開”。中共一任總書記張聞天和國民黨的蔣經(jīng)國、蔣緯國等那個時代諸多名人都曾在該校就學(xué)。
影響了黃的另一位著名人士是李平書。李平書,一八五四年生,同樣長黃炎培一代,浦東高橋人,三十余歲時進(jìn)上海《字林滬報》,蜚聲文壇,一八九八年去廣東主政抗法,后回上海主持江南造船局,并任中國通商銀行總董。一九○五年李與黃炎培等人共同發(fā)起成立浦東同人會,集中了穆藕初、穆湘瑤兄弟等一批浦東籍實業(yè)家和社會活動家,修造了浦東大廈。在此基礎(chǔ)上,以李平書為首的一批實業(yè)家組織起上海工巡捐局,李平書擔(dān)任總董,黃炎培等擔(dān)任議董,逐漸發(fā)展成為地方經(jīng)濟(jì)活動的中樞機(jī)構(gòu),握有上海地區(qū)相當(dāng)?shù)墓ど淌聞?wù)權(quán)力。
從事地方自治活動充滿風(fēng)險。一九○八年初,黃炎培又一次遭難。黃在浦東中學(xué)的一次講演中抨擊了不良現(xiàn)象,被上告說黃“演說革命排滿”,同時引證一九○三年新場鎮(zhèn)案黃即有反清前科。江蘇提學(xué)使毛慶藩接到舉報后不敢怠慢,秘密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黃確有此傾向,欲治罪于黃。風(fēng)聲傳出,社會人士聞訊后紛紛起來為這位每月只領(lǐng)四十元大洋(當(dāng)時中學(xué)校長月薪一百元)的黃抱不平,上書反對辦黃。江蘇教育會更不示弱,上書兩江總督端方,以強硬口氣給當(dāng)局極大壓力。在社會與論下,端方和毛慶藩不想把事惹大,從而折中,撤銷了黃川沙廳視學(xué)一職,保留了浦東中學(xué)監(jiān)督的職務(wù)。
一九○九年,在江蘇教育會基礎(chǔ)上成立江蘇省咨議局,按江蘇八府三州劃分地區(qū),選出了一百二十名議員,其中十六位為常駐議員。結(jié)果,張謇出任議長,黃炎培被選為常駐議員。黃在省咨議局主要辦過兩件實事,編制預(yù)算和撤銷厘卡。之前的江蘇省行政尚無正規(guī)預(yù)算,交給省咨議局審議的是一筆徹頭徹尾的糊涂賬,無從審議,于是責(zé)成由姚子讓為正、黃炎培為副代為編制,限時交上。姚與黃接手后抓梳剔理,終于編制成像樣的省級財政預(yù)算表,當(dāng)時省里水路交通要道均設(shè)置厘卡,船只路過需交納厘捐,于是卡官們便敲船主竹杠,如向其行賄則可免交放行,這股愈演愈烈的風(fēng)氣肥了自己卻坑害了國家。于是在黃提議下,咨議局派出黃等議員分頭調(diào)查,調(diào)查結(jié)果反映行賄腐敗之風(fēng)確為嚴(yán)重,于是通過議案,裁撤厘卡,改由商人認(rèn)捐,定一九一一年實施,然而那年革命爆發(fā)了。
江蘇省咨議局成立之后,又成立了江蘇地方自治籌備處,黃炎培為自治籌備處參議。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江蘇尤其上海社會的日常運轉(zhuǎn),雖仍在清朝統(tǒng)治名義下,但實際的地方性權(quán)力已逐步發(fā)生轉(zhuǎn)移。在上海逐漸形成了政治事務(wù)由江蘇省咨議局和江蘇地方自治籌備處參與,教育文化事務(wù)由江蘇教育總會主持,經(jīng)濟(jì)事務(wù)則由上海工巡捐局掌握的政治自治、文教自治、經(jīng)濟(jì)自治的一派自治新局面。而黃炎培又分別是江蘇省咨議局的常駐議員、自治籌備處參議、江蘇教育會常任調(diào)查員、上海工巡捐局議董,交叉在政治、文教與經(jīng)濟(jì)三個領(lǐng)域的社會組織實則權(quán)力中樞之間,雖尚未獨領(lǐng)一方,但均系這些中樞的核心成員,時年黃僅三十歲。
雖然歷史上曾有革命與立憲之爭,在大講階級斗爭的年月里又好將人們貼上不同的標(biāo)簽,其時這些社會組織難逃“改良”之名而在不同程度上受貶,但事實證明正是這些社會組織,完成了權(quán)力的和平轉(zhuǎn)移進(jìn)而使社會的平穩(wěn)轉(zhuǎn)型和順利過渡。及至辛亥年間整個朝廷搖搖欲墜,對社會,對地方的控制力已處弱勢。恩格斯晚年提出“歷史合力”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697頁),是非常正確的觀點,無論是革命派還是改革派,都從不同角度,以不同途徑,削弱、震撼、打擊舊統(tǒng)治,為新時代鳴鑼開道,為歷史前進(jìn)做出自身貢獻(xiàn)。
四、辛亥槍聲
晚清最后年月里推動憲政,試圖改革,然而為時已遲,社會矛盾高度積累,導(dǎo)致反清事件接踵而來。
一九○○年,唐才常湖北起義,失敗。一九○三年,章太炎、鄒容“《蘇報》案”被捕;黃興在長沙密謀起義,未成。一九○五年,吳樾謀刺載澤等出國考察五大臣被殺。一九○六年,江西萍鄉(xiāng)黨人起義失敗;孫中山、黃興攻鎮(zhèn)南關(guān)不克。一九○七年,浙江紹興反清烈女秋瑾被殺;徐錫麟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后被殺;一九○八年,黃興等在云南河口起義,不成。一九一○年,汪精衛(wèi)謀刺載灃不成,被捕。一九一一年三月,黃興、趙聲組織廣州“黃花崗起義”。
一九○八年光緒、慈禧去世,幼年宣統(tǒng)繼位。此期間,張之洞死,袁世凱罷官,清廷“太子黨”皇族內(nèi)閣實施立憲和自治,但為時已晚。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農(nóng)歷,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以下日期均為農(nóng)歷),湖北新軍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yīng)。
如前所述,上海和江蘇的社會組織已成氣候,除張謇、李平書外,還有若干地方名人如復(fù)旦大學(xué)創(chuàng)始人馬良(相伯)、姚文枬(子讓)、沈恩孚等,尤其是趙鳳昌(竹君),在辛亥前的上海和之后南北議和過程中起到幕后策劃作用。趙鳳昌原任張之洞首席幕僚,后轉(zhuǎn)到體制外憑借張支持活躍于滬上,在諸多工商和社會事務(wù)中穿針引線。從張謇到李平書,從黃炎培到趙鳳昌,這些地方社會領(lǐng)袖雖政治意識不完全相同,但卻在推翻清廷、建立民國這一根本問題上持相同立場。辛亥前后他們時時聚會,據(jù)黃晚年回憶,在上海自然形成了幾個據(jù)點:教育總會是一處,工巡捐局是一處,望平街時報館樓上“息樓”是一處,趙鳳昌的家“惜陰堂”又是一處。而在這幾處之間奔走聯(lián)絡(luò)的正是黃炎培,一方面黃三十出頭最年輕,是同盟會上海負(fù)責(zé)人,又橫跨了文教、經(jīng)濟(jì)、政治幾個社會組織為其骨干。年紀(jì)最大的馬相伯老人時時召黃去徐家匯家,詢問大局走勢,早在南洋公學(xué)時,蔡元培就帶黃去馬老家學(xué)習(xí)拉丁文,相交多年。
武昌起義之聲傳來,二十四日趙鳳昌來電請黃去,商定趙提出的五點意見:“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種族偏見,以弭永久之競爭;發(fā)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縮減戰(zhàn)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fù);聯(lián)絡(luò)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吳歡:《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杰》,長江文藝出版社二○一○年版,3頁),作為處理南北爭議的原則。
為響應(yīng)武昌起義,黃與張、李、趙及陳其美等商議策劃上海起義。九月十三日上海民軍與商團(tuán)巡警在閘北起義,十四日攻下清軍大本營所在地江南制造局。十五日下午,江蘇的蘇、松、常、鎮(zhèn)、太五屬在設(shè)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召開會議,擁護(hù)起義,推舉黃炎培等赴蘇州動員江蘇巡撫程德全起義。
程德全,四川人,原為黑龍江省候補知縣,俠義正直。一九○○年帝俄侵略我國東北,程請赴前敵,將軍壽山命程與俄交涉,無果。俄國隔江發(fā)炮轟城,壽山自殺。之后程不時以身擋炮口,俄人受感而停止發(fā)炮。黑龍江人民為程感動,請求朝廷任命程為將軍。一九一○年程被調(diào)任江蘇省巡撫,接觸到黃炎培、張謇一班人,很是贊賞。程德全十四日起義,將他賞識的黃留在都督府,協(xié)助自己。
與有些地方殺滿排滿之風(fēng)不同,程德全在江蘇起事中堅持不殺傷一個滿人的原則,都督府發(fā)出六言告示:“照得民兵起義,同胞萬眾一心……旗滿視同一體,大家共享太平。”(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以下均同) 很是受到擁戴。
在都督府中,黃負(fù)責(zé)起草新官制和向舊衙門收取印信。黃被分派收取省提學(xué)使樊恭熙印信,當(dāng)時黃來到后樊十分恐慌,戰(zhàn)戰(zhàn)栗栗,黃受程諄囑,十分和藹地對樊講:“此舉出于全民公意。你如愿留蘇,就留下,給生活費。愿回原籍,當(dāng)送回籍川費。”樊表示愿回老家浙江,黃予辦理,毫無刁難。省里官員包括各知縣均照此處理,很得人心。
黃幾件事辦得四方滿意,于是程任命黃為民政司總務(wù)科長兼教育科長(當(dāng)時未設(shè)教育司),既是管家又主教育。當(dāng)時都督月工資五十元,司長三十元,科長二十元,都很低,在一派革新氣氛中黃欣然領(lǐng)命。
當(dāng)時大大小小會議極多,黃應(yīng)接不暇,因為眾人都希望有同盟會要員在場才夠格。上海“息樓”所在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貼滿海報,捷報到來,鼓掌歡呼!若傳來失利消息,被認(rèn)為受清廷指使,誣勝為敗,憤怒打碎玻璃窗。獨立聲、勝利聲震撼各地,清廷狂駭了。
十月十二日聯(lián)軍攻下南京,這時反清中心已從湖北轉(zhuǎn)到上海和江蘇,黃興等民軍首領(lǐng)都來到上海和南京。
十月十四日,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舉行全國共和聯(lián)合大會,公電孫中山回國主持大政,公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國名定為中華民國,決定五色國旗,紅、黃、藍(lán)、白、黑象征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
武昌起義不久清廷起用袁世凱,任其為湖廣總督,統(tǒng)兵進(jìn)駐天津。之后便開始戰(zhàn)與談兩方面較量。談判幕后很大程度上是由趙竹君、張謇、張一麟、黃炎培、馬相伯等穿針引線,已由近年發(fā)現(xiàn)的幾千封趙竹君信札證實。當(dāng)時稱之為“惜陰堂策劃”,趙等有廣泛的人脈,與南、北雙方高層都熟,從而“一手托兩家”。新發(fā)現(xiàn)的趙竹君的大量信札(見吳歡:《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杰》),證實了上世紀(jì)六十年代初黃炎培晚年時的回憶,黃說:“‘惜陰堂策劃‘從此開始……惜陰堂趙竹君等認(rèn)為:全國人心是一致要求獨立的,革命軍熱情、勇敢、犧牲精神都是有余的,可惜實力太不足……這種情況下,只有利用擁有實力的袁世凱去勸清廷,可能生效……沒幾時,汪精衛(wèi)被釋放了。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代表,民軍公舉伍廷芳為代表,雙方在上海進(jìn)行和談,這是表面文章。實際上袁世凱和清廷商定: 一、清帝讓位; 二、汪精衛(wèi)釋放; 三、提出清廷滿意的優(yōu)待條件。而袁世凱和民軍商定: 一、清廷讓位; 二、改建民國; 三、總統(tǒng)職位給予袁世凱。”
十一月六日,孫文先生從海外歸來。十一月十日,直、奉、魯、汴、鄂、湘、粵、桂、閩、晉、陜、滇、贛、皖、蜀、蘇、浙十七省代表集中南京,開臨時大總統(tǒng)選舉會,孫文當(dāng)選臨時大總統(tǒng),黎元洪當(dāng)選為副總統(tǒng)。確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舊歷,那天就是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
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公布優(yōu)待清室條件。孫文辭職,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tǒng)。
黃炎培在辛亥革命五十多年后回憶寫道:“辛亥革命,從廣義寫起來,接下去是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叛變,二次革命,抽刀斷水水更流,是無法劃斷的。辛亥年結(jié)束了。”
五、辛亥之后
辛亥革命結(jié)束了,但黃的事業(yè)剛開始。
袁世凱要黃入閣,黃不從,袁生氣說黃是“與官不做,遇事生風(fēng)”。黃不肯去中央做官,黃是要在地方做事。一九一二年,江蘇省都督程德全任命黃炎培為省教育廳長,已辦學(xué)十年,對我國教育有頗多思考的黃,毫不猶豫地上任,大刀闊斧推動江蘇省教育改革,推行他的五年教育計劃。
首先在各縣成立起一批小學(xué)。其次是中等學(xué)校,分五類:第一類為師范類共十所,在吳縣、上海、無錫、江寧、江都、清河、銅山、灌云、南通等地,還有一個女子師范也在南通;第二類為普通中學(xué)共十一所,在江寧、吳縣、華亭、太倉、武進(jìn)、丹徒、南通、江都、清河、銅山、東海等地;笫三類為農(nóng)業(yè)學(xué)校共五所,在江寧、吳縣、清河、吳淞(水產(chǎn))、滸墅關(guān)(女子蠶桑)等地;第四類為工業(yè)學(xué)校:江寧第一工業(yè)學(xué)校電機(jī)科、機(jī)械科,蘇州第二工業(yè)學(xué)校紡織科、色染科、土木科等;第五類為高等學(xué)校,設(shè)立南京高等師范,不久改為東南大學(xué)。可惜,隨一九一四年黃辭去省教育廳長職,這些計劃未能全部到位,但全省教育獲得空前發(fā)展,為以后江南經(jīng)濟(jì)發(fā)展,奠定了人才基礎(chǔ)。
辦這樣多學(xué)校經(jīng)費從哪兒來?黃上任先抓財稅改革,定每年全省教育經(jīng)費二百四十萬銀元,為保證這筆款項,規(guī)定省內(nèi)的竹木、屠宰、牙行等省稅全額專款劃歸做省教育經(jīng)費,從而在源頭上保證了教育經(jīng)費。
卸下省教育廳長職的黃炎培,并未停止他的辦學(xué)事業(yè),除上述所說南京高等師范、東南大學(xué)之外,黃又參與創(chuàng)建、改建、擴(kuò)建了多所大學(xué):暨南大學(xué)、上海財大、河海工程學(xué)院、同濟(jì)大學(xué)等。陳嘉庚出資要辦廈門大學(xué),寫信給黃請他籌備并出任廈大校長,黃答應(yīng)了老友參加籌辦卻未去任校長職。
一九一五年,黃赴美國參觀舊金山世界博覽會,考察美國教育,轉(zhuǎn)赴美二十六座城市,五十二所大、中、小學(xué)校。歸國后,一九一七年黃炎培聯(lián)合馬相伯、蔡元培、張元濟(jì)、伍廷方、嚴(yán)修、宋漢章、聶云臺、穆藕初、蔣夢麟、郭秉文等四十八人,發(fā)起中華職業(yè)教育社,開創(chuàng)我國的職業(yè)教育。次年創(chuàng)立中華職業(yè)學(xué)校,辦起中華鐵工場、木工場、機(jī)械工場、琺瑯工場。同時推廣職業(yè)指導(dǎo)、職業(yè)培訓(xùn),黃炎培提出“使無業(yè)者有業(yè),使有業(yè)者樂業(yè)”的教育理念,把職業(yè)教育推向鄉(xiāng)村,試辦昆山徐公橋等幾處鄉(xiāng)村教育試驗區(qū),又引向企業(yè)與榮毅仁父輩榮德生、榮宗敬合作,在榮氏廠里辦起職業(yè)培訓(xùn)班。雖說中華職教社僅是個社會團(tuán)體,但在職教社之下,既有學(xué)校,又有工廠,還有刊物,所以確是個涉足教育、經(jīng)濟(jì)、文化、傳媒等多方領(lǐng)域的非政府組織。由于發(fā)展迅速,常感資金不足,于是發(fā)行中華職教社債,得以融資。幾年后,職業(yè)教育在我國蔚成風(fēng)氣,到一九二六年全國職業(yè)學(xué)校達(dá)一千六百九十五所。中華職教社力量不斷擴(kuò)大,社員從一九一七年的一百八十六人增加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千五百二十八人。黃等人的苦苦追求,終獲初果。
物換星移,歲月流逝,辛亥元老陸續(xù)謝世:一九一四年黃興去世,一九二五年孫文去世,一九二六年張謇病逝,黃送上挽聯(lián):“物則棉鐵,地則江淮,蓋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遠(yuǎn)處著眼,近處著手,凡在后生,宜知勉矣!早歲文章,晚歲經(jīng)濟(jì),所謂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覺,尚何憾乎?”(《黃炎培日記》,未刊稿,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馬相伯老人九十九壽,之前相伯老人九十五壽和九十六壽時黃曾作詩相贈,此次黃贈上《百歲凱旋長句凡九十九言,為九十九齡馬相伯先生壽》:
撐霄徐匯雙窣堵,/扃云靈谷千楓樹。/高齡好游不遑處,/愛此山奇甲寰宇。/一星南極輝當(dāng)戶,/山半畫堂開,/酒暖春歸早。/片語發(fā)群蒙,/彼儒亦強矯。/我聞桂林山多患人少,/何以作人惟壽考?/相期明歲迎歸,/碧淞作灑黃墻桃。/百歲坊臨歇浦濤,/凱旋一柱擎天高。
(《黃炎培詩詞》,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100頁)
一九三四年,黃炎培率眾友重返惜陰堂,賀長己一輩的趙竹君八十壽,共憶二十余年前辛亥時光,尤對已侵占我東三省的日本極為憂慮,黃作詩道:
惜陰清 隱人海,/真靈相業(yè)山中在。/溯從庚子迄辛亥,/興亡夢覺驚風(fēng)采。/皤皤一老秦亭來,/盛年洱筆游蓬臺。/大堤鄣水溝江淮,/長髯風(fēng)雪日往回。/……/相看九五白眉翁,/此正壯年日月邁。/嗟哉東北多封狼,/荒荒山川阻且長。/諸公若定指揮策,/人慶無疆國有疆。
(《黃炎培詩集》,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74頁)
那是辛亥二十余年后辛亥元老重聚的一幕。無論辛亥二十余年后的一九三四年,還是五十年后的一九六一年,抑或今年的辛亥百年,人們不會忘卻歷史,并從回憶與紀(jì)念之中思考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