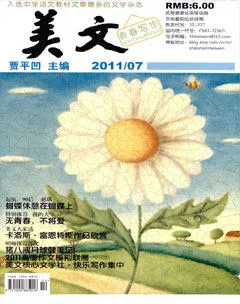思戀小島的孩子
永不長大的小島,是一個被用濫了的童話意象,我知道。但我還是會不由自主地去用它,尤其是當我寫例行公事的發言稿以及創作談時。高中時我最討厭的文體是書信,上了大學后我才知道比書信更討厭的是發言稿和創作談。因為這兩種東西寫出來都有種虛幻感,是寫給被人看、讀給別人聽的,我總感覺自己給它們安了一個面具,上面涂了我希望別人看到的微笑和痛苦。
我想,我是可以掙脫出文體的束縛,隨時隨地表達出自己真實的情感的。我希望活得像一個心直口快的孩子,但我天性不能。我顧慮了太多太多,而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是體貼還是虛偽。
而在擅長的文體中,有時候我仍然不知所措,在下一句的開端無所適從。往往心思一動,本來想要表達的意思似乎就變了樣。可能我的詞庫還太過貧乏,無論是講述還是描述都有一種力不從心之感。重復的意象,重復的角色,重復的故事,似乎鍵盤上的字母都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機械地按照一個不入流寫作者的蒼白想法噼噼啪啪地排列組合。
可我還是努力地表達著,期盼一大段一大篇世俗的文字后會出現一個小小的奇跡,一個小小的閃光。那么我便略為滿足了,就像在本以為沒有星星的城市夜空中,突然飄走了一片暗云,結果,一顆淡淡的白星就那樣突兀地閃現在夜空中,仿佛永恒的海平線上,浮現出陸地細長的輪廓。
人類都有表達自己的欲望,所以他們演講,著作,向上攀登。我不記得是誰說過類似的話,應該是個值得銘記的作家,可我光記住文字記不住作者的壞習慣從來沒改掉過。打小我就不認為那些封面上的名字和封面下的故事有什么聯系,因為一個生活于現實,一個存在于童話。直到我開始接觸非虛構類文學,我才漸漸記住了幾個在書店專欄書架上高頻率出現的名字。
到我十六歲的時候,我才醒悟到,無論多么虛構的文字,都是浮于現實之下的幻影,和現實有著雷打不動的聯系和相同的形狀。于是我開始真心實意地關注生活。可以說,那時候我走出了一座由層層書頁構筑的精致城堡。那城堡美麗夢幻,卻是一個極小的天地。盡管我能從高大透明的落地窗中看到城堡外的茫茫草色,遙遠的村莊,和山坡上的大樹風車,卻從來沒有走出去,觸摸到那綠意盎然下面的粗糙樹皮和滄桑土壤,或是坐在木屋外面,呼吸那觸手可及的充滿干草味道的炊煙。
因此,我十三歲開始寫作,以一部長篇童話為開端;到十六歲,別人說我的童話詩寫得比童話更為出色,這讓我有種哭笑不得之感,仿佛我走了三年的錯誤道路,可我依然熱愛著童話,并將這種熱愛以詩歌的格式表達;十七歲,我開始對散文認真,結果獲得了意想不到的贊賞,而我也越來越喜歡這種表達方式。我徘徊在童話的邊緣,回頭看著漸漸遠去的永不長大的小島,又遙望那越來越近的茫茫大陸,一點點靠近現實,卻又懷著一種畏懼之心。我坐在一只詩意的雙桅船上,從孩子的叢林駛向更廣闊的世界。
但我依然沒有切斷與小島的聯系,永遠不會,當我們之間隔著大海時,海浪來回游蕩,海鷗來回飛翔,傳達著我們的訊息;而等到海枯石爛之時,年老的我,將吃力地下到干枯的海底,穿梭在蒼白的海草之間,一步步走回那里。
并永遠守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