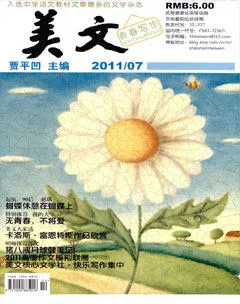其心許之 其劍贈之
張大文:1991年被評為全國模范教師并被授予國家級“人民教師”獎章。1992年被評為上海市特級教師。現為復旦大學附中特級教師,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兼職教授。已發表文學作品1000萬字左右。
在延陵季子看來,只要心里答應過了的事,就一定要答應到底,付諸實現,不折不扣地做到“心想事成”。在這里,最值得我們尊敬的是,在“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的時候,他就心領其意,并且“其心許之”;后來在離晉返國途中,在“天不知,地不知,徐君不知,我可以裝作不知,因為只有我心知”的情況下,特地轉道徐國,把這件事情的真相挑明,行禮如儀,直到其劍獻之而后已。——想到我們往往輕易對人口惠而實不至的情況,真正應該愧煞!
尤其要深思的是,就此事的來龍去脈中的“去脈”而言,已經可以隨著徐君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了,而延陵季子卻始終順著“來龍”走向自己既定的不變的“去脈”,其中必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在焉。
原來,在這幾天延陵季子離徐聘晉之時,徐國國君在朝拜楚王時已客死于楚了。也就是說,延陵季子要獻劍也無處可獻,因而完全可以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完全可以不是違背心意、欺騙心意的事了。但是,延陵季子偏偏要算作一件欺心偽心之事,不可饒恕,因此,必須“脫劍致之嗣君”。
這時,他的侍從插進來說此劍是吳國之寶,不宜隨便“贈送”。延陵季子卻抓住這個機會,辨證“贈”與“獻”的原則區別,反而更堅其意:贈是本來就想以物相送,獻是初無贈意,確實身處對方“不言而色欲之”的現場而作出即席反應;前者只是表面應酬,后者確是真心相許;前者是“要我送”,后者是“我要獻”;前者也許只是“禮尚往來”,后者卻是動機單純,不作“回報”之想;前者可能是儀式隆重的過眼煙云,后者卻有一對不宜察覺的懇請的眼睛時時浮現而揮之不去。——因此,這把寶劍是獻定了!不獻,就是自己變了心!
反過來說,有了獻劍的決心,盡管一路坎坷,也能如愿以償。在嗣君因“先君無命”而“不敢受劍”時,他終于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走出了一道通衢——走到徐君墓前,把劍掛在墓側的大樹上,讓天地作證,我不辜負當時不言而表的真正心意,完成了一樁純潔無暇的小事。——如果說把劍獻給活著的徐君還有無以辯白的私心雜念之嫌,那么,把劍獻在你的墳頭上,我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唯利是圖之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