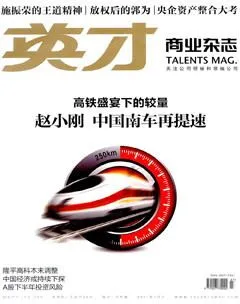到美國發展高鐵的兩大問題
我參加的第三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涉及內容很多,有人權、安全、國防、經濟方方面面,其中有一個企業家對話專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說,這個對話是這次所有對話里面的重頭戲,所以她很看重。
一開始是所有的部長都不參加,只是四個國家元首特別代表參加。中國就是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委員戴秉國,美國是財長蓋特納和希拉里。然后一邊六位企業家,后來臨時決定兩國的商務部長,就是駱家輝和陳德銘參加這個會議,一共18個人。地點在布萊爾宮,就是美國的國賓館。會議蓋特納主持,由王岐山、希拉里和戴秉國致辭。然后是逆時針順序發言,我是第四個。
發言的時候我說,現在中美企業互相投資差距很大,我是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據我了解,中國企業很多都愿意到美國去投資,但是對美國的政策大家都不清楚,有點擔心,所以怎么樣加強中美企業信息交流很重要。
在會前,我和陶氏公司的CEO,僅十幾分鐘,就聊到很多商機,說明我們這種溝通還是很少,這種形式的交流應該多一些。
接著我主要介紹了一下中國高鐵的發展,并對美國的高鐵發展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奧巴馬總統一年中多次提出要發展高鐵,但是最近也聽到一些有利和不利的消息,不利的消息是個別的州政府因為財政問題取消了高鐵的項目。同時,眾議院最近又通過一項法案,要縮減對高鐵的投入,因為美國政府也沒錢了,我說這是不好的消息。好的消息呢,就是我在對話的前一天,美國的交通運輸部長說要繼續對美國高速列車追加20億美元的投資,我說這個好像是個好消息。但我的問題是,現在美國政府有沒有一個具體的,就高鐵基本建設的一個推進計劃,如果有是什么內容,我想如果有了這個東西,我們來投資就更有信心了。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南車跟美國已經有幾十年的合作歷史了,前幾天還跟美國西屋公司簽了一個協議,要通過合作把美國西屋公司的產品介紹到中國來,另外,之前我們還和GE公司簽了戰略框架協議,在美國本土發展美國的高速列車。但問題是美國有一個Buy American(買美國貨)的法案,這個法案對吸引投資不是有利的,舉一個例子,這個法案要求產品必須60%的本地化,可高速列車在美國是一個剛剛才醞釀的產業,市場還沒形成就要搞本地化那必然導致成本大大提高,那么怎么參與市場競爭?怎么發展這個產業?20年前美國來中國開拓市場的時候,中國可沒有這個法案,都是買你的東西。等到中國的市場做起來了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就搞本地化了,這需要一個過程,而不是一開始就要到美國建廠。
現在奧巴馬提出來要回歸工業,回歸工業就應該中國企業去美國會受到歡迎,這是趨勢。
獨家高端領袖對話——中國高鐵很現實
關于盈利
《英才》:我們看到一組數據,一季度中國南車的凈利達到11.82億,增長是122%,但是同期鐵道部第一個季度虧損達到了37億,你怎么看待這組數據?
趙小剛:鐵道部每年的營業收入大概是7000- 8000億元,今年大概是8000多億元,從歷史上看它基本上處于一個盈虧平衡。中國的鐵路是一個公益事業,發達地區補貼欠發達地區,這里面有政治意圖,有戰略意圖,所以整個系統諸多爭論權威解答中國高鐵很現實只要維持能夠運轉,包括能夠更新換代就行了。
全世界各個國家鐵路都是政府補貼的,而中國鐵路最近十多年發展,政府基本上沒有補貼。如果講到每個季度的盈利情況,我覺得這對于8000多億元的營業收入來說,基本上是一個盈虧平衡的狀態,有時候盈利幾十億也很正常,這個不能說明問題。
《英才》:目前,京滬高鐵已經開始正式的試運行了,這條鐵路被爭議了21年,你覺得,目前的造價超過預算很多,速度也在往下降,從時速350公里降到300公里和250公里,這對你們未來的盈利構成影響嗎?
趙小剛:預算的確是增加了,10年前的概算應該是1公里1個億吧,就是1300多公里,1300多億吧,現在大概是2000億出頭,每公里不到1.5億。
我認為這是正常的,因為這么長時間土地價格漲了多少。
《英才》:其實一個高速鐵路要爭議21年才有今天這樣一個結果,而且即使這樣還是不斷地被爭議?
趙小剛:這么大的工程有不同的聲音說明中國很民主。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大項目沒有爭議的,埃菲爾鐵塔爭議了多少年,現在法國人才認可它,剛開始建的時候可能一大部分法國人都不同意。
我覺得中國發展高鐵是找到了一個經濟增長的,不同于發達國家所走過的路,另辟了一條蹊徑,如果這條路走成功了,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也是有示范性效應的。
關于速度
《英才》:你會不會覺得中國南車的發展速度,就像高鐵時速一樣越來越快?
趙小剛:發展速度快嗎?
《英才》:很多人覺得這是驚人的速度。
趙小剛:我們搞高速列車研究20年時間了,只不過是成果反映到這些年來,我們第一臺高速列車出來是1998年,當時是200公里的時速。1998年到現在多少年了,都13年了。但是歐洲像法國、德國,他們是上世紀80-90年代發展的,真的到穩定運行200多公里也用了十多年時間。日本最早1964年搞高速鐵路,他運行到270公里時也用了十多年的時間,而我們也了解了他們很多技術,何況這次又通過引進技術,應該說時間并不是很快的,我認為是正常的速度。
《英才》:現在鐵道部把速度降到時速300公里或300公里以下,會不會影響到未來的業績?因為你們都是按照高速去建廠,已經投入了這么多,會影響訂單嗎?
趙小剛:這個線路建設的標準是按350公里建設的,那么現在運行300公里,運行一兩年以后我預計他會把速度提上去。能開多少速度和你運行多少速度沒有一個必然的關系,就像你買寶馬,它能開時速200公里,但高速公路只能開時速120公里,那你為什么不買一個最高時速120公里的汽車,這樣不是更省錢嗎?就是說要有一定的余量,火車也一樣。
關于能耗
《英才》:有人說,如果時速達到350公里,動車的單位能耗是跟飛機一樣,這個有依據嗎?
趙小剛:肯定不是這么回事。在滬杭線上南車的C R H380A實測在時速為300公里時,人均百公里能耗僅為3.64度電,相當于客運飛機的1/12。但是速度越高,單位能耗確實是急速上升的,我個人的觀點是地表的交通工具,時速在200—350公里之間是比較好的,根據客流的需要開行時速200—300公里之間的,同時根據部分旅客對時間要求比較高,開行少量時速350—380公里的,這是可行的。因為我個人覺得超過1500公里范圍應該是民航發揮主力軍的作用,500-1500公里發揮高鐵的主力軍作用,這是不同的交通方式協調發展的問題。
關于安全
《英才》:可是像德國和日本,他們的技術也很不錯,為什么全世界只有法國、西班牙、中國,這三個國家運營350公里的?是因為不經濟呢還是出于安全性考慮?
趙小剛:不是安全,還是一個經濟性問題。在一個350公里的線路上面同時可以跑200公里,就像高速公路設計標準最高時速120公里,你跑80公里不一樣照跑。只是設計的時候,設計250的,那以后萬一要跑300,這個空間不就沒有了?還是要有發展的眼光,高鐵一搞都是上百年的使用期,到時候想要提速整個線路又不行了。
《英才》:像歐美這些國家有技術,也有錢,為什么不往高速發展呢?是什么制約他們?
趙小剛:這一次我在美國,也跟他們探討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同時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它的人民富裕程度也在很快的提升,以后也要變成一個發達國家,那么中國能走美國這條路嗎?肯定是不現實的。如果按照美國的那種人均耗能的標準,世界上再增加一倍的石油產量也不夠中國用,那肯定是不可持續發展的。但是美國發展的年代沒有高速鐵路,所以羅斯福新政,就搞高速公路,拉動美國經濟,再加上人口也相對比較少,雖然總量也不少,但跟中國比要少得多,這么多年已經形成了汽車文化。雖然后來發展了航空,但要改變這個汽車文化已經不是一個技術問題了,是一個文化問題。為什么美國發展高鐵爭議那么大?我認為是文化問題,當然也有利益集團的博弈問題,發展高鐵,對于一個發達國家已經形成的固有體系是沖擊。
中國是創造了一個新的客戶群體,當然與民航也有競爭,但也促進民航發展高鐵到不了的地方,比如支線飛機。
現在降速,也是給民航留一定空間,所以這是一個和諧發展的產物,并不是安全問題。
《英才》:其實速度跟安全沒有必然聯系。
趙小剛:沒有。
《英才》:但外界很容易將速度和安全連在一起。
趙小剛:當年我們從日本引進時速250公里的車,它的脫軌系數(重要的安全性指標,用加載到車輪的橫向作用力除以縱向作用力)是0.73,國際標準是小于0.8。簡單地說就是縱向作用力越大橫向作用力越小,越安全。后來,我們在引進的技術上開發300和350公里動車的時候,我們在時速300到350公里測試的脫軌系數是0.34,安全系數更好。等到380A這車,380公里時速測下來是0.1。這就引發了科學家的好奇,為什么速度越高,越安全?
所以下一步我們就要開發一個時速500公里的車,來做這個科學實驗。當然,這并不是實際運營。科學家想探測一個東西,地表高密度的空氣,通過氣流作用,對列車穩定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