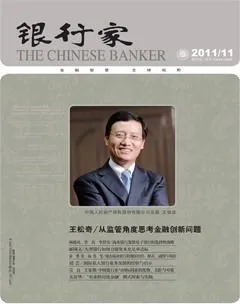從監管角度思考金融創新問題
2011-12-31 00:00:00王松奇
銀行家
2011年11期

王華慶博士在繁忙工作之余,筆耕不輟,已出版多部有份量的學術專著。前不久,他給我寄來了新著《金融創新理性的思考》(以下簡稱《思考》),我讀完后發現,這是一本內容扎實、邏輯縝密、新論迭出的學術力作。
在本輪金融危機中,全世界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美國的金融創新與危機的關系問題,很多研究者干脆將危機的最終原因歸因于金融創新,王華慶博士在《思考》一書中通過對金融創新定義的源流梳理以及對本次金融危機成因假說的全面介紹分析,明確提出,在本輪次貸危機中的美國金融創新是“過度金融創新”,是建立在衍生品工具創新基礎上的畸形金融創新,這種創新通過高杠桿率在危機的引發和傳染上發揮了作用,因為金融創新放大了流動性的易變性,但是,絕不能因此就把金融創新當成本輪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思考》指出:次貸危機有其復雜的深層次原因,并不是金融衍生品惹的禍,金融創新不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金融創新使貨幣金融因素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對金融危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不能簡單地把金融危機歸結到金融創新上,不能因為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就否認金融創新的價值,更不能因噎廢食,抑制和停止金融創新(《思考》第111頁)。在這里,我之所以引用華慶博士的話起因于10月26日上午我參加銀行業協會的年度銀行家高層論壇時發生的一件事。
10月26日的銀行家高層論壇有兩個討論模塊——(1)創新與轉型;……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