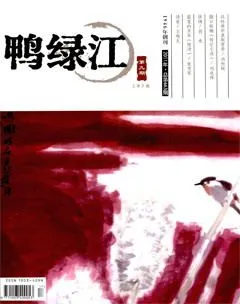從經典中汲取營養
每一個寫作者都面臨著文學師承問題,不論你師承什么樣的文學作品和作家,可遵循的規律只有一條:“取法乎上,得之其中”。我相信,大凡在創作中想有所成就的人,都是以經典以大師作為范本和老師的。汲取經典的乳汁是自己體魄健壯的基礎。據我所知,我周圍的好多作家都是先讀莫泊桑、契訶夫、梅里美這些短篇大師的作品而開始短篇小說的寫作的。他們用經典的火把來照亮自己的文學創作之路。當然,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的文學境況。而近幾年,通過讀當代的文學期刊也能成名,足以證明文學的“發展”是個硬道理。
我常常給我周圍的文學青年說,你們要讀福克納、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要讀卡夫卡、卡爾維洛、喬伊斯,要讀馬爾克斯、加繆。不是我輕視我們的文學傳統(《紅樓夢》我至少讀過三遍),我感慨的是,我們的文學傳統,為什么沒有按照《山海經》《聊齋志異》《西游記》的路子走下去?我讀小學的時候就不止一次地在故鄉的博物館里目睹過我們那兒出土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我記住的是青銅器上的紋飾,那些紋飾,大都是夸張變形的,而不是寫實的。夸張變形是現代藝術的精髓。也就是說,在兩千五六百年前,我們祖先的文化因子中就有了“現代意識”,而發展到如今,這些很有現代意味的藝術品怎么就被主流劃到圈外去了?敢問有多少文學期刊接受了荒誕不經的作品?接受了夸張變形的小說?
細細追究,現代主義也不是外國作家的專利。秦腔《游西湖》中的《鬼怨》一場將“鬼”表現得活靈活現。《劈山救母》中,人神完美結合融為一體。《竇娥冤》中,六月炎天,大雪紛飛。這些非現實主義的藝術在我們的舞臺上活躍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我們的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而翻開我們的文學期刊,每年又能刊發幾篇像魯爾福那樣寫生死兩界的荒誕作品,在我們的獲獎作品中又有多少篇什具有創新意識——不要說創新了,就是模仿非現實主義的作品也沒有。
我們的批評界和文藝官員逢會必講文學創新。究竟什么是新。我想,只要我們全面繼承世界文化的優秀遺產,只要敢于給自己封閉的圍墻打開一個豁口,文學創作的氣氛就會有所改變,從雜志上學習創作到雜志上發表,然后去某個機構領獎,這種局面就會有所改變。到那時,也許會有文學精品產生。假如用國家意識形態規定的一個視角去衡量我們的文學作品,去寫遵命文學,我們留給世人的只能是唱頌歌的“宣傳品”。藝術畢竟是藝術,好的藝術作品是形式和內容的完美統一,是具有思想深度的。
我也不止一次地給年輕的作家們說,你們不要一提起筆就寫大部頭的長篇,應從短篇小說開始練筆。據我的經驗,要經營好一個短篇,絕不是易事。短篇是不藏拙的文學樣式,一篇好的短篇里蘊藏著作者對這個世界、對人生、對人性深刻的理解,蘊藏著作者的藝術功力和聰明才智。在一部長篇或一部中篇中,作者可以不經意塞進去一把稻草一把棉絮,而短篇中,絕不允許有這樣的填充物。我雖然已經發表了200多個短篇,但依舊對短篇樂此不疲,原因就是,總覺得自己沒有達到一個高峰。假如自己運氣好,有一天能夠寫出《紀念愛米麗的玫瑰花》(福克納)、《印第安營地》(海明威)、《墻上的斑點》(伍爾芙)、《大教堂》(卡佛)、《立體幾何》(麥克尤恩)這樣的短篇,也就心安理得了。
有人擔憂,由于種種原因,中短篇小說的氣脈欲絕了。我想,沒有這種必要。只要人類不朽,不論什么樣的藝術就不會絕種。我相信,文學依然神圣。中短篇小說不會因為種種沖擊和讀者量的減少而消逝的。藝術作為一種宗教,總會有它的皈依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