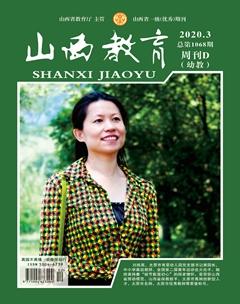突發疫情帶給幼兒園管理的啟示
王美玲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突發,打破了我們平日的安寧與規律,作為幼教人,經歷了此次加長版的假期,我們應該從疫情防控中汲取教訓、總結經驗,提升幼兒園面對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最大程度地保障幼兒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長!
一、善于借力,讓呵護更專業
疫情防控,讓我們再度審視幼兒園保健工作的重要性,幼兒園保健人員的數量是否充足、資質是否正規、業務能力是否嫻熟、是否有較高的職業敏感度、對師幼及家長的傳染病防控宣傳是否到位等,這些過硬的指標有些并非是幼兒園自身努力就能達到的,也需要婦幼保健院、疾控中心、衛生監督所、紅十字會等專業機構人員給予更多專業指導和監督。如:根據一年四季的季節特點和不同傳染病特征,幼兒園要主動邀請婦幼保健院或疾控中心的專家來園做專題講座,讓教職工和家長提高防控傳染病的意識,增長防控傳染病的技能和方法,做到“預防”先行一步;主動對接衛生監督所,對園所消毒燈的質量、說明以及消毒記錄進行現場指導;定期邀請紅十字會的人員對教職工進行應急救護培訓,實操心肺復蘇和繃帶包扎,危機時刻,每個人都可成為救護員,條件允許的還可以配備除顫儀。
二、常備物資,讓防控更及時
幼兒園是人員密集性場所,幼兒一日生活中進餐、盥洗、午休、游戲、集體教學等一系列活動基本上都在同一空間進行,因此,衛生消毒工作就需非常嚴格,同時,教師對幼兒的健康觀察和監測等都需要物資支持。尤其經歷了這場疫情,更讓我們深切感受到防控物資緊缺對生命健康的威脅,所以,幼兒園在日常管理中,就要備足、備齊日用防控物資,對幼兒的呵護才能夠更全面、更到位。為每個班級同時配備紅外線體溫槍和水銀體溫計,每天晨午檢用體溫槍為幼兒測體溫,遇到個別幼兒有發熱情況或有其它不適時,要使用水銀體溫計再次確認準確體溫;為每個班級配備醫用酒精棉球、84消毒液、消毒桶、專用抹布、防護手套等,并存放到專柜中,執行雙人雙鎖制度;為教職工配備醫用成人口罩,為幼兒配備醫用兒童口罩,出現傳染病,幼兒洗手建議由肥皂改用免洗手消毒液;為教職工分別配備手動噴壺和電動噴霧器,對公共區域地面進行消毒等。
三、關注生活,讓教育更接地
幼兒園的教育是全面的、啟蒙性的,一日生活皆課程。陶行知先生說:“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陳鶴琴先生說:“大自然、大社會就是活教材。”幼兒雖然年齡小、能力弱,但他們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各種事件充滿了好奇,如新冠肺炎疫情這種突發事件蘊藏著豐富的教育資源,如能抓住機會,適當引導,那就是活生生的教材,對幼兒的教育將會事半功倍,使其銘記終生。
一方面,幼兒園要對突發事件可能生成的主題教育內容進行全面預設,同時對幼兒感興趣的內容進行衍生拓展。我園和太原市育英幼兒園聯合推出的“線上學前學堂”就是一次很好的嘗試,一線教師用心錄制活動視頻,引導幼兒不斷探究疫情始末,帶領幼兒用游戲和運動驅走心理恐慌。我園針對幼兒出門不愿戴口罩的情況,在元宵節制作了“戴口罩的湯圓娃娃組合圖”。為表達對醫務人員的致敬,我們自制了幼兒愛看的三期原創主題電子繪本,幫助幼兒了解當災難來臨時,社會中各種充滿責任感的群體是如何“國有難、召必回”,沖鋒在前的。
另一方面,幼兒園要指導家長通過突發事件,增進幼兒社會認知,激發幼兒社會情感,引導幼兒社會行為,幫助幼兒社會化成長。家長在幼兒眼中,是重要的“他人”,幼兒在成長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對人、對己、對社會的認識、情感態度和行為,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的影響。尤其遇到諸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發事件,家長能否從國家的角度、社會的立場去負責任地表達看法?家長是否心系災區、熱心捐款、投身志愿服務?家長能否誠心感激醫護、公安、社區等人員并積極配合他們的工作?“你想讓孩子成為怎樣的人,那你就去做怎樣的人。”這是最樸實的家庭教育,家長的表現和反應都在幼兒的眼中,影響著他們社會關系的建立和社會責任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