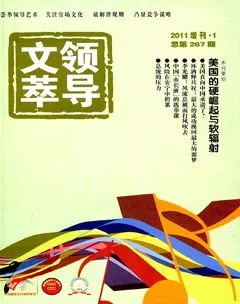出錯是一種本能
如果我告訴你,一個球拍加一個球,一共是1.10美元,球拍比球貴1美元,那么球是多少錢?這個問題顯然不需要很復雜的計算,難度就和小學生每天功課要演算的題目差不多。但在幾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心理學家謝恩·弗雷德里克讓普林斯頓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的學生來解答這個問題時,給了學生們足夠的時間算出答案,結果呢,50%普林斯頓的學生和56%密歇根的學生都答錯了。他們的答案是:球拍1美元,球0.1美元或10美分;而正確的答案是:球拍1.05美元,球0.05美元或5美分。
幾乎每個人第一次被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會脫口而出10美分的答案。不知道為什么,這個答案感覺上就像是正確的。乍一看,1.10美元的總價可以簡單地分成1美元和0.1美元,粗算一下,兩個量也正好相差1。所以對于我們的大腦來說,10美分的答案就好像是個“自然”的反應。人們下意識地努力作答,但是要答對還需要更大的努力。而用不同的問法來問這個問題,似乎就沒那么難了。如果我說,球拍和球一共1.10美元,球拍是1.05美元,球多少錢?這次你的本能就不會出錯了。
對于這個實驗,“理性選擇”顯然無法解釋,同樣也無法解釋過去十年來、心理學家和實驗經濟學家所做的上百個實驗。如果你想找到合理的解釋,那么必須得另辟蹊徑。而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的“兩個系統”的觀點,則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途徑。
卡尼曼認為在人類大腦這套裝置中有兩個系統,其中只有一個系統是理性的。這個理性的系統能夠有意識地根據邏輯處理信息,工作起來很慢,一步接著一步,而且只有依靠持續不斷的努力和全神貫注才能運作。
但是,在這個計算的大腦之下,還有另一個“本能”的大腦,它運作起來快速、自動、很難掌控。我們本能的大腦看到了1.10,于是就把這個數字分成了1和0.1,它一把抓住了重要的細節,很快地給出了答案,做事風格利落迅速,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分析。
卡尼曼,還有其他人開始逐漸把理性的幻覺從經濟學中拆離。1970年到1980年這10年中,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維斯基共同合作,研究在許多簡單的情況下,思維的本能是如何對信息的接收和使用產生影響的,并了解到聰明人如何漸漸偏離了經濟學家的理性理念。他們發現如何“框定”一個問題,或如何呈現一種情況,會對人們的處理方式產生戲劇性的影響。例如,告訴病人手術的成功率有90%,和告訴病人手術有10%的可能會失敗,這兩種告知方式會使病人做出不同的決定,前者更有可能使病人接受手術。同樣地,對相同的金額進行不同的描述,價值也會變得不一樣。假設你要買的CD是15美元,店員說再走兩分鐘到另一家店里,這張CD只賣10美元,你可以節省5美元。很多人都會努力省下這5美元,但是研究表明,如果同樣的人要買的是一件125美元的皮夾克時,他們就不介意省不省這5塊錢。從理性的角度來講,兩種情況下的5塊錢都是一樣的,然而本能的大腦卻并不同意,它認為一種情況中的5塊錢,比另一情況中的5塊錢更值錢。
總而言之,不是我們失去了理性,而是我們慣常的思維背離了理性。許多經濟學家喜歡把這種背離稱作為“反常狀態”,仿佛它們是對理性觀念的背棄,莫名其妙,叫人費解。但是進一步思考,也許我們思維的本能其實一點也不反常,或許在人類歷史上還具有非凡的意義。
(摘自《河北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