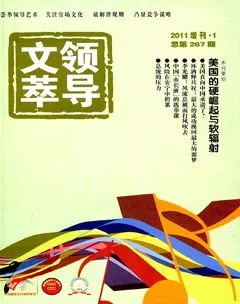葉永烈:應(yīng)有“比較領(lǐng)袖學(xué)”
不以后來論當(dāng)初
《瞭望東方周刊》:你的創(chuàng)作對象,既有黨史上的正面人物,也有備受爭議的反派,如《陳伯達(dá)傳》,發(fā)表后就引發(fā)了巨大爭議。為何要寫他們?
葉永烈: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有七個(gè)組,分別研究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任弼時(shí)、江澤民,其他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就沒有納入這個(gè)框架。我覺得衡量一個(gè)歷史人物,只要他對歷史的影響大,就值得研究。
比如李鑫,在幾乎所有粉碎“四人幫”材料中都沒有提及。其實(shí)在粉碎“四人幫”這件事上,他的功勞非常大。當(dāng)時(shí)他騎著自行車去給華國鋒通風(fēng)報(bào)信,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qiáng)”。不提他的原因是因?yàn)樗强瞪拿貢笥址噶艘恍╁e(cuò)誤。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這類人物肯定很難寫。
葉永烈:是的。我寫陳伯達(dá)之前,關(guān)于他的介紹只有1000多字。我看《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國人寫德國納粹的歷史,美國政府提供了大約兩噸的資料。而中國人寫自己的歷史,卻會遇到很多障礙。
我對中國當(dāng)代重大政治題材的創(chuàng)作堅(jiān)持一個(gè)原則:“兩館一主”。“兩館”——圖書館與檔案館,“一主”——以采訪為主。
這是被逼出來的。當(dāng)我開始查資料時(shí),發(fā)現(xiàn)檔案館對作家設(shè)置了重重障礙。要找重要人物資料,中央檔案館是最理想的去處,可是到那里去查資料,都需要領(lǐng)導(dǎo)簽字。即使順利查到資料,之后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還必須經(jīng)過審查同意才能發(fā)表。
一些檔案只有中共黨史專家有查閱資格,還有諸多限制。不同級別的黨史專家的查閱范圍不同,并且只能查閱他們研究的部分。在這樣查閱資料困難的情況下,我只能另尋出路,被逼著去找親歷歷史的當(dāng)事人了解情況。
采訪的時(shí)候我是一定要錄音的,因?yàn)榕鹿P記記得不全面。我用的錄音設(shè)備從飯盒大小的“紅燈牌”錄音機(jī)到現(xiàn)在的錄音筆,僅磁帶就錄了1000多盤。這幾年逐漸電子化了,我用電腦把磁帶都轉(zhuǎn)換成數(shù)字文件,全部保存。
《瞭望東方周刊》:寫正面人物和事件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嗎?
葉永烈:會。同樣是領(lǐng)導(dǎo)人,奧巴馬觀看襲擊拉登的視頻時(shí)坐在角落里,中間是美國的將軍。而中共一大會址紀(jì)念館的蠟像,毛澤東站在最中間,其他代表坐在周圍。事實(shí)上當(dāng)時(shí)主持會議的是張國燾,毛澤東是記錄員。
中共二大紀(jì)念館的畫像就更匪夷所思了:李大釗坐在共產(chǎn)國際代表旁邊,陳獨(dú)秀站在李大釗后面。怎么會讓陳獨(dú)秀站在李大釗后面呢?陳獨(dú)秀當(dāng)時(shí)的地位比李大釗高,歲數(shù)也是陳比李年長十歲。
我始終堅(jiān)持“不能以后來論當(dāng)初”,歷史記錄,就應(yīng)還原親歷者當(dāng)時(shí)的樣子。
核心觀點(diǎn)與中央保持一致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這樣的話,難免觸碰到很多“敏感地帶”,你如何應(yīng)對可能帶來的風(fēng)險(xiǎn)?
葉永烈:比如寫《江青傳》時(shí),各種細(xì)節(jié)必須通過事件當(dāng)事人的回顧來印證。對于抓捕江青有各種說法,甚至有人說江青當(dāng)時(shí)一屁股坐在地上耍無賴。我采訪了張耀祠(時(shí)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wèi)團(tuán)團(tuán)長),聽他談了這個(gè)過程,必須是第一手資料,我才敢寫。像心理活動(dòng),毛澤東和江青的對話等等,這些沒有出處的內(nèi)容是絕對不寫的。
我走這條路非常小心謹(jǐn)慎,因?yàn)閷v史負(fù)責(zé),所以沒有出過大問題。現(xiàn)在關(guān)于“文革”的書管理得很嚴(yán),我的182萬字的《“四人幫”興亡》還是可以出版,也沒有很大的修改,說明我寫的歷史是經(jīng)得起考驗(yàn)的。
《瞭望東方周刊》:史實(shí)的把握以外,還有史觀的問題。你說過,要“史實(shí)準(zhǔn)確,觀點(diǎn)正確”。怎樣理解觀點(diǎn)正確?
葉永烈:在我的紀(jì)實(shí)文學(xué)中,核心觀點(diǎn)一定會和中央的決策保持高度一致。
有關(guān)中共中央黨史的重要文件我都非常認(rèn)真地研究,最重要的是《建國后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還有《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在這些問題上與中央看法保持一致,這樣比較準(zhǔn)確。
另外,我只敘不論的方法,也不太容易出問題。有港媒說“葉永烈的書是只述不論”,我就是這樣的,我認(rèn)為讀者自己會評價(jià)。寫這種紀(jì)實(shí)文章,評論是很難的。香港關(guān)于這種作品,就喜歡用二三手材料,都沒有第一手事實(shí),也可以說多半是評論。我不會那樣。
獨(dú)家來自“知名度高、透明度差”
《瞭望東方周刊》:你如何選擇創(chuàng)作對象?比如,為何寫了陳伯達(dá),未寫周恩來?
葉永烈:我寫的都是獨(dú)家性的,尤其注意那些知名度高、透明度差,又能折射一段中國當(dāng)代重要?dú)v史的人物,而這些人物多是過去沒人寫過或?qū)懙脺\、寫得少的。
陳伯達(dá)身上確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比如中共中央《關(guān)于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總路線的建議》,在當(dāng)時(shí)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xiàn)。我采訪陳伯達(dá)時(shí),他偶然說了一句,“當(dāng)時(shí)主席要我寫這篇文章,他說,我要的是張燮林式,不要莊則棟式。”陳伯達(dá)當(dāng)時(shí)不懂,后來他請教別人后才知道,張、莊二人打乒乓球,張燮林是削球手,而莊則棟是短平快,所以主席的意思是,不要去駁蘇共,而是正面闡述自己的觀點(diǎn)。后來陳伯達(dá)寫了以后,毛澤東一字不改就同意了。這篇重要的文獻(xiàn)都查得到,但具體是怎么來的,很少有人知道。
《瞭望東方周刊》:但你也寫了蔣介石、毛澤東這些焦點(diǎn)人物,寫他們時(shí),如何做到與眾不同呢?
葉永烈:《毛澤東與蔣介石》1993年出版時(shí),我就提出蔣介石的三大功勞:一是領(lǐng)導(dǎo)北伐,二是抗日領(lǐng)袖,三是退守臺灣后,對臺灣經(jīng)濟(jì)起飛做貢獻(xiàn),還堅(jiān)持一個(gè)中國。這樣的評價(jià)超越了當(dāng)時(shí)的社會認(rèn)識。當(dāng)時(shí)大陸對蔣介石的評價(jià)多為負(fù)面,對我的書有很多人批評,說美化蔣介石,特別是2005年紀(jì)念抗戰(zhàn)勝利50周年時(shí)《解放軍報(bào)》上的一篇文章,批評相當(dāng)尖銳。
書里提到,西安事變發(fā)生的時(shí)候,毛澤東高興地說“審判蔣介石”。我們一直回避這個(gè)問題,說毛澤東主張和平解決,其實(shí)是周恩來到達(dá)西安之后,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才提出來和平解決。
出版的“藝術(shù)”
《瞭望東方周刊》:《紅色三部曲》前兩本都很順利出版了,到了第三本《毛澤東與蔣介石》審查的時(shí)候卡住了,后來是如何通過審查的?
葉永烈:剛開始審查沒有通過,原因之一是開頭引用了尼克松在《領(lǐng)袖們》中對毛蔣二人的比較:“在過去的半個(gè)世紀(jì)里,中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和蔣介石這三個(gè)人的歷史。”審查人員認(rèn)為:“怎么能用一個(gè)美國總統(tǒng)的話來作為中國政治紀(jì)實(shí)文學(xué)的開篇語呢?”
原因之二是,書中寫了一個(gè)場景:毛澤東與蔣介石在下棋,毛澤東不斷地抽煙,像土豆倒在沙發(fā)里,蔣介石正襟危坐。兩個(gè)人的形象對比,也是審核機(jī)構(gòu)無法接受的。
但最關(guān)鍵的還是因?yàn)椋?dāng)時(shí)認(rèn)為蔣介石是什么人,毛澤東是什么人,怎么可以將二者進(jìn)行比較?
到上世紀(jì)90年代初,我的一位編輯朋友建議將書名改為《國共風(fēng)云》。這樣改一改,就可以出了,而且后來果然出了。后來有機(jī)會再版的時(shí)候,我改回原來的《毛澤東與蔣介石》,現(xiàn)在有“比較文學(xué)”,也應(yīng)該有“比較領(lǐng)袖學(xué)”。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