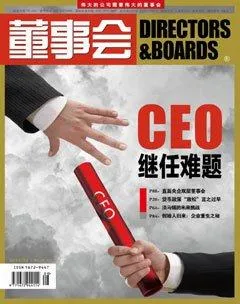角色錯位矛盾重重
為國企董事會減負
話題背景:
國企董事會建設是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的重點也是難點,在推進董事會建設深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部分國企董事會負擔過重就是其一。
不止一位地方大型國企的負責人告訴本刊,按照企業章程與國資委的監管要求,公司需要董事會議決的事情實在太多,董事會會議頻率每月多次仍不敷所需,導致董事會成員疲于應對。
無獨有偶,早在2011年5月舉行的第6屆金圓桌論壇上,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總結央企董事會試點的得失時,首先提及的就是部分公司董事會負擔過重的問題。
國企董事會負擔過重,難免導致決策質量下降甚至行為越權失范,潛在危害不容小覷。在國企改革攻堅和經濟社會轉型等內外部條件約束下,減負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愈發顯得重要。
國企董事會負擔過重,其本質是公司治理架構問題重重,董事會越來越多地承擔了股東會、董事會、黨委、經營層的職能
針對國企董事會建設,坊間有這樣的比喻:主管部門好比政治局,董事會好比人大,經營層好比政府,監事會類似政協。就筆者切身擔任過董事會秘書工作經歷來看,國企董事會負擔過重有其深層次原因,為國企董事會減負任重道遠。
國資委職責不清
《公司法》規定:國有獨資公司不設股東會,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行使股東會職權。從國資委這幾年來具體運作方式和開展的一系列對國有企業的監管活動看,國資委更多地是將自己定位為國有企業“董事會”,監管國有企業的具體運行,國資委與國有企業董事會職能高度重疊。例如,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選擇任命、業績考核;公開招聘國有企業副總經理;中央國資委在央企啟動了培養技能人才成長機制,等等。可以看出,國資委對國有企業事務的管理已經非常具體,超越出資者職能。國資委的人員絕大多數都是長期的黨政工作背景,形成一個政績導向的政府組織文化,而不是一個所有者利益導向的投資組織文化。
對企業進行監督和日常管理,不是通過選聘、激勵、監督約束經理階層來對企業的日常運作進行管理,原本董事會應該是公司核心決策機構,事實上干了經理層的活,自然造成董事會負擔過重。
黨政分工不明確
中國國有企業的董事會建設,還涉及到黨管干部原則和黨委發揮治理核心作用、以及《公司法》與《黨章》的關系定位等問題。中國國有企業的董事會建設,也不是任國有企業自身所能為之的事,它既涉及政府同級黨委、政府及其國資委的主體角色界定和職能關系劃分問題,又涉及同級政府與其國資委等主體間相互關系的設定問題。相關法律及章程規定過于寬泛,黨委(組)書記、法定代表人,在企業管理上究竟是何崗位、崗位職責如何描述?干部與人才如何界定、怎樣管理?黨委會、董事會權責如何確定?等等問題無不增添了董事會上的疑難與困惑。
同時,因為這種關系,董事會作為決策機構必然擔負起過多的職責,如協調好與出資機構(國有股東的關系),協調好與同級政府、上級政府的關系,協調好與同級黨委、上級黨委的關系,國企董事負擔可想而知。
董事會和經營層高度重疊
首先國企董事會,內部董事居多,董事會成員通常都兼任經營層的高管職位,董事會成員既承擔了決策機構角色,也承擔了企業經營角色;獨立董事不獨立,基本上來自政府、高校、科研單位,屬于體制內的專家,股東會、董事會、經營會、總裁辦公會權責界定不清,會議權限、議題重復。從表面上看是董事會頻率過高,其本質是公司治理架構問題重重。
其次母子集團公司領導嚴重“雙向進入,交叉任職”。表現為:一方面,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分別兼任集團重要子公司的董事長;另一方面,重要子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則分別兼任集團的副總經理、董事。這種錯綜復雜的任職管理體系,不僅擾亂了一切經營運作秩序,而且也使得母子兩級公司的董事會、黨委和經理層的功能越發失效和失靈。
董事會越來越承擔了股東會、董事會、黨委、經營層的職能,其負擔只能越來越重。
董監事會職能交叉
推動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以來,我國在公司治理框架構建上先后借鑒了二元制模式的監事會制度和一元制模式的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制度,改制后的國企中也形成了雙重監督機構并存的公司治理模式。兩會都要對公司的管理層進行監督,而監督的重點又同樣是財務報告。
而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之間的關系協調問題均未作出明確說明,從多數企業的實踐看,監事會和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在定位上不夠清晰,職能難以嚴格區分,在公司財務監督、內控審查等方面存在沖突。更為嚴重的是,企業出了問題,彼此推脫,互相埋怨,造成名義上人人有責、實際上無人負責的尷尬局面。例如將“提議聘請或更換外部審計師”等職責賦予了審計委員會,在監事會存在情況下,本身就是一種資源重復配置和浪費,同時也增加了董事會職能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