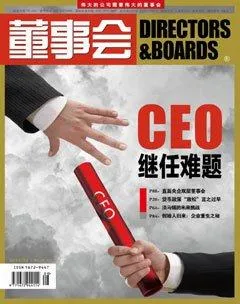次級債毒酒開戒
銀行發行次級債最大的風險點在于。開了戒后就必須年復一年地靠此種形式維持和延續銀行資產規模不斷增長的需求
趕在2011年上半年最后一天的前一天,中國乃至全球最大的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成功發行了380億元次級債,將全部用于補充該行的附屬資本。至此,加上半月前中國建設銀行發布將在近兩年內發行800億元次級債的計劃,以及中國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業已完成的分別發行320億元和500億元次級債的舉動,中國四大銀行一個不落地都飲下或將暢飲次級債的“美酒”,總數達到2000億元。
在四大銀行看來,2000億元的次級債是迎來了一場及時雨,而非背上了“高利債”。但這個看來龐大的數字,對中國四大銀行巨頭擁有的接近45萬多億元的總資產或者3萬多億元的股東權益來說,不過是薄酒一杯。事實上,這個不可持續的融資工具,更似一杯讓人飲鴆止渴的毒酒。
開戒易斷癮難
2010年四大銀行中,除農行于7月實行IPO,在內地和香港上市融資約221億美元(折人民幣約1450億元),補足了核心資本外,工行、中行、建行通過發行可轉債或公開配股的方式,實現股本融資合計1667億元。應該說,2010年的上市融資或配股融資(包括發行可轉債)都是必要的,畢竟這三大行距離其首次公開上市融資已經有5-6年的時間了。但這幾大銀行的掌門人似乎在2010年配股融資后都曾高調地表示,在近3年內將不會再向資本市場融資。遺憾的是,去年的話言猶在耳,今年上半年卻看到了用發行次級債融資的一幕大戲。
在筆者看來,這或許有點飲鴆止渴或吸食興奮劑的味道,一旦上了癮,是收不了手、斷不了根的。其最大的風險點在于:一是開了戒后就必須年復一年地靠此種形式維持和延續銀行資產規模不斷增長的需求;二是成本開銷會越來越大;三是隨著巴塞爾資本協議Ⅲ和中國銀監會關于資本充足率監管新政的實施,對2010年底前發行的不合格的二級資本工具(實際就是指銀行間相互發行、購買的次級債),以其在2012年年末可計入二級資本的余額為基數,從2013年起的10年內逐年減少10%,到2022年1月1日開始將不再計入二級資本,這將迫使幾大銀行另行想轍,而就近期看,這個轍在境內是不好想的。有的銀行已經開始在境外(如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或許這是一個路子。但香港和其他境外地區有多大的人民幣債券容量呢?很顯然,除非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加速,否則遠水解不了近渴,而且“物以稀為貴”,債券價格肯定會節節攀高。另外,“僧多粥少”一搶,說不定又會有其他的亂子或調控措施蹦出來。
對發行次級債這種所謂的附屬資本工具,或者說二級資本工具,并非從2010年開始,而是在2005年前后就有了。早些年發行的次級債,當時銀監會并沒有限制總額,也沒有訂出規則,因此各大銀行相互之間都是你發行的我買,我發行的你買,期限有5年期的,也有10年期。有些第一輪5年期的債券已于2010年到期,故銀行為了不減少二級資本,不得已要繼續發行并加量。但在銀監會于2010年作出新規定,明確銀行相互之間發行的次級債不能納入二級附屬資本計量后,這條路就很難再走了。2011年5、6月間,中行、農行、工行相繼發行的總額達1200億元的次級債,中行的320億元、農行的500億元都是15年期,實行固定利率,利率均為5.3%(高于當時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205個基點);而工行于6月29日發行的380億元次級債,期限卻進一步拉長為20年,相應地將固定利率提高到5.56%(比其時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高出231個基點)。或許這是市場預計到了央行可能還會有加息的調控通脹預期政策出臺,5.56%的定期利率相對于從7月7日起升高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5%而言,只高出206個基點。與中行、農行發行時的高于基準利率205個基點幾乎完全相當。但工行的次級債是20年期,比中行、農行的15年期多整整5年,說明工行的這個發行價格還是相當合算的。當然,要是與2010年及前兩年發行的價格比較,那就高得很多了。如果在2009、2010年一次把經批準的發債計劃完成,就不知要省下多少發債成本了。
轉型不要次級債
話又得說回來,市場上對幾大銀行似乎有點自食其言的批評,筆者認為是不夠公正的。因為銀行在去年配股融資后一再聲明,如現行監管政策不調整,銀行可以三年內不再融資。但正是從2010年下半年起,國內外對資本充足率的監管政策都相繼調整了,先是巴塞爾資本協議Ⅲ提出的既加量又提質的標準,后來是銀監會的高于《巴Ⅲ》的中國版《巴Ⅲ》及四大監管工具約束等,這些都是幾大銀行及其他上市銀行不曾預計到的新政策、新形勢、新要求。因此,如果四大銀行要想保持資本的穩定,并對促進經濟的發展繼續發揮應有的作用,就應該從監管方面和銀行經營方面各自推出一些相較于以往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對監管方面來說,不能為了減輕自己的監管責任,不斷地對資本充足率和其他監管工具層層加碼,向商業銀行發出越來越密集和越來越大聲的“緊箍咒”。而對被監管的商業銀行而言,則不能追求資產規模越大越好,更不能追求什么指標都要成為全球第一。因為很多事情都是有其自身的規律性,“物極必反”,“滿招損,謙受益”。
商業銀行應該從自身的條件出發,更多更好更早地走內涵式的科學發展道路,而不能再依靠外部市場和企求股東的不斷施舍、救助而把自己抬到“大而不能倒”、“大而好得利”的地位上去。事實上對幾大銀行來說,發行數百億元甚至上千億元的次級債,充其量能提高大銀行不到1個百分點的資本充足率,維持不到半年或1年就會重新口干舌燥。因此,大型銀行的轉型之路絕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應從今年開始果斷轉身,哪怕把現有的速度調整放緩一點也沒有多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