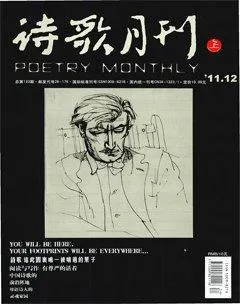藍馬:“前文化”.非非主義.幸福學
胡亮按:二○○八年四月十日,成都慧恩書院,筆者拜訪了藍馬先生。藍馬,本名王世剛,一九五六年生于四川西昌,一九八六年與周倫佑等開創非非主義詩派,并被譽為該派的“理論祭司”,一九九七年皈依佛門。主要文論有《前文化導言》、《語言作品中的語言事件及其集合》等,主要詩作有《世的界》、《凸與凹》等,目前致力于整理《藍馬文集》,已出版《痛苦與幸福》分冊。雖然有人認為藍馬“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王潮《變構語言的努力:“非非”語言意識淺析》),但是學者李振聲卻指出,“藍馬是‘非非’詩群中無可爭議的,最富有想象力的理論家”(《季節輪換:“第三代”詩敘論》)。下面,是筆者與藍馬半個下午加半個晚上的對話,其時,慧恩書院主人蒲紅江、牛慧祥斷續在座。
胡亮:一切異稟者的童年都是不可忽視的:在巨大的、無往而不在的時代性雷同之中,一定有一些白得嚇人的光只眷顧了角落里的那一個人。這個人后來之所以非如此不可,是因為他在掉隊的時候踩上了一塊別人看不見的西瓜皮。他拒絕著、但又不得不承受那悄悄生長的暗瘤。你的童年時代必定遭遇了某些非同尋常的生活體驗或者閱讀體驗,這些體驗是否在最黑暗的土層之中,埋下了日后必將長成參天大樹的一顆果核?
藍馬:你說得對,是有一些“非同尋常”的體驗。首當其沖的是大約兩歲多發生的一件事。我家在西昌,小時候父母常不在身邊,我和姐姐交給一個保姆帶。保姆喜歡女孩,不喜歡男孩。出門玩耍,保姆把姐姐背在身上,而我呢,牽著衣襟緊跟其后。我們來到東河邊,紅色的河灘上有一個偷偷開放的“自由市場”:一塊塊方布鋪在地上,擺放著一些七零八碎的物件。在一個地攤上,我被一枚“紅寶石”吸引。石頭是雞心狀的,發著瑩瑩潤潤的小光輝,紅里透白,白里滲紅,形狀、質地和韻味奇妙無比,引起了我內在的強烈震動。用現在的語言來描述,應當這樣說:當時我生命中發生了一場突然而劇烈的變化。也許從外表看,我只是驚呆了;但在內里,那場變化活生生地活在生命之中,從此不再離去。這種情形難以表達。有時我說一個新生命在自己生命中誕生了,——這樣說很接近原始感受,但似乎會被認為不合適,因為生命已經存在,怎么能說生命中又有生命誕生呢?所以后來和現在,我只好說生命中隱藏的某個領域被激活了,這被激活的東西一直活著:我隨時可以知道、體會、調動、掂量、把玩和受用它,就是沒法描述它!這個變化如此真實,但是“無言”。當時只有兩歲,教育還沒怎么開始,尚未污染上太多語言,因而整個變化是最干凈的,“凈裸裸的變化”!實際上我當時也不知道什么地攤不地攤、寶石不寶石、光潤不光潤,一切都是沒有語言標記過的,一切都是“凈裸裸的事實”;而且連“事實”也沒有,只是“凈裸裸的××”;甚至連“凈裸裸”也沒有,只有那些那些……總之,沒有語言,照樣能看、能聽、能意識、能儲存所有感受,而且是“凈裸裸”地全盤收入生命。長大之后,我嘗試用“后學會的語言”來描述,才發現無論怎樣也只能說到外表的外表、周圍的周圍,卻不能說出“本身”。這個本身完全沒有辦法訴諸語言和文字。我想,其他人可能也有類似的變化發生,有類似的狀態達成。只不過,也許我對發生的事情更加在意,也許我比別人更少一些干擾,才幸運地保留下那些活生生的經驗。想想看,兩歲左右,父母常不在身邊,保姆又常不管我,這是多好的成長生態啊:像一株植物,一個人靜悄悄地成長,沒有人來絮絮叨叨地告訴我這是什么那是什么,沒有人來要求我讀這個背那個……在這樣“凈裸裸”的成長生態中,我常常獨自調閱“紅寶石事件”,就像在心中過電影一樣,每當我再次“看見”紅寶石,生命中的那個領域便被激活,任我一個人靜悄悄、完整整品玩。這種時候,感覺很爽、很舒服、很滋潤、很受用。那個被激活的東西超越了體內體外的界限:它無形無相,但可以被自己覺知,也可以被自己攪動,還可以被自己掂來掂去。真思維已接近被引出。現在,可以說,那是一樁精神事實,甚至可以說:那是精神實體之所在。后來,類似的經歷還很多,成為我生命中的寶貴財富,促成了前文化理論的產生,促成了我與佛學的不解之緣。正是對這些事件以及這些事件激起的生命反應的長期反復體悟,形成了我生命中一條很特別的風景線—非文化的智能活動線。這條與我的生命成長相伴相隨的生命智能活動線的存在和對其產生的認識與把握,是我后來提出前文化理論的深刻源泉。作為文明人,伴隨我們成長的還有另外一條線:由文化知識積累形成的一條文化性的智能活動線。在這條線上,鞏固和積累著一系列“可以說清”、“可以訴諸語言文字的東西”:知識體系,——對外部世界進行功利化操作的知識體系!我想,這就是你所說的“時代性雷同”:同時代的人,被灌輸進去的知識體系大體接近;即便是不同時代的人,在這條線上,雖然輸入的內容有異,但性質卻相同。它們所能形成的是文化性/知識性智能活動,是可以言說的智能活動。我的理解,人類正常的智能活動,至少有以上兩條主線。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一些人在成長中,漸漸變得只注意到文化性的智能活動這一塊了,他們只在這條線上搞積累、做講究了,以至后來完全忘記了生命中曾經有過的另一塊領域——非文化、前文化、超文化——的存在,讓這個精彩領域長期處于“撂荒”狀態。我的不同在于:我一直沒有放棄兩條線中的任何一條;在我不能表達的時候,兩條線在生命內部涇渭分明;我想表達出兩條線的差異,于是終于建立了前文化理論框架。
胡亮:我已經看見了一種思想的奇妙起源;我曾經感受過類似的追溯。哥倫比亞傳記作家達·薩爾迪瓦爾在《歸根之旅——加西亞·馬爾克斯傳》中對馬爾克斯的童年作了更加細致、同樣驚奇的打撈,他幾乎找到了《百年孤獨》、《枯枝敗葉》和《霍亂時期的愛情》中一切情節的因由,哪怕是最不可思議的情節,包括香蕉園中暗含魔法的寂靜、坐著細亞麻布床單升了天的美人兒雷梅苔絲!一切在更早的時候都有跡可循。那么你的后來呢?
藍馬:后來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時我還小,沒有資格加入;但作為擁有幼小、干凈心靈的旁觀者,我在那時吸收了豐富的“凈裸裸的刺激”。一九七○年到七二年,是我的初中時代。我把作文寫成了詩,得到了老師表揚,使我對詩有了最初的愛好。七三年以后當了四年“知青”,放牛、抽煙、做農活。我在“春燕”牌煙盒上就寫一首《春燕》,在“山花”牌煙盒上就寫一首《山花》。《春燕》是一連串抒情式的強烈呼喚,現在看可以說是對愛情的召見。《山花》詠嘆生長在牛蹄印里的一朵小花:她永遠看不見朝霞,也看不見夕陽,只能承受正午烈日的烘烤。招生制度改革第一年,我考入西昌衛校讀書,先學解剖和生理,再學病理、臨床和藥物之類。老師講到“眼球”時說:眼球之所以能夠感光,是因為視網膜上有兩種細胞,一種感明光,一種感暗光,感明光的細胞可以區分色彩,感暗光的細胞則不能,紅、黃、藍到了黃昏就沒有色彩,只剩下灰度,因為這時候感明光的細胞不起作用了。講者無心,聽者有意。當我聽到這里,立即感受到一場巨大的崩潰:在這之前習得的整個世界觀瞬間崩塌。當時想,要是視網膜多一種,或者少一種細胞,我們能看到的與現在所看到的肯定不一樣。世界是假的!我覺得一切都要重新思考。想想看,我們的視網膜細胞是夠的嗎?推而廣之,五官夠嗎?四肢夠嗎?這當中,一個血肉模糊而又十分強烈的狀態在生命中起伏涌動。我意識到“客觀世界”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感官功能決定的。某些動物的某些功能肯定超過人類,它們的“客觀世界”與我們的“客觀世界”肯定不一樣。崩潰之后,生命剩下一片空白!奇妙的是,這種空白與紅寶石激活的那個領域是相通的。那時候已經改革開放,我一方面接受各種進來的思想,另一方面獨自困惑。我開始試著命名在我生命里活生生動來動去的這一塊無法言說的智能領域。我把它確定為一個思維領域,一個不使用語言、概念和邏輯的非文化、前文化和超文化的思維領域。這種思維與學醫完全不同。學醫需要背醫書、跟蹤最新的醫學定論:靠記憶就可以作一個好醫生。這是一種運用現成知識的思維,而不是發現性的乃至創造性的思維。而發現性、創造性的思維在哪里呢?就在我長期關注的那個智能領域里。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先于語言而存在的真思維。其“思維成果”需要向人介紹時,才需要使用語言。在創立非非之前,我已經把這種能夠發現未知事物的創造性思維明確界定為前文化思維,意指:其一,先于文化存在;其二,能夠創造文化;其三,它本身具有超文化的特性,因而它本身永恒不會被文化化。你看,前文化并不是反文化。前文化的提出一是厘清了文化創造的來源,二是為文明人想要從文化之中解脫出來提供了一個美妙歸宿。八四、八五年前后,我提出這些思想,開始動員周倫佑一起搞詩派。
胡亮:我曾經毫無根據地認為:前文化是非非主義一切理論的源頭。這個觀點終于在你這里得到了證實。一九八六年,非非主義橫空出世。二十余年來,非非主義在外部壓力和內部裂變的雙重撕扯之下逶迤行進。然而,歷史的真相遠不是清晰可辨。在關于非非主義緣起的問題上,周倫佑和楊黎甚至相互開除,而你一直保持沉默。具有領袖情結的周倫佑一直以非非主義開派宗師自居,并且得到現行大多數詩歌史的支持。你對此有何看法?換言之,我想知道到底誰是非非主義最初的命名者。
藍馬:最初,周倫佑反對我的觀點:怎么可能存在無語言的思維?他的年齡大一些,已有所學,身上“固有的”東西很多。像我這樣給他講“無語言思維”、“先于語言的思維”,你可以想見,他不假思索就開始反對。我也反問他:創造語言需不需要思維?他沒有回答。從后來的情況看,他似乎還是接受了我的觀點。就這樣,我動員他一起搞流派,不是一次兩次,而是三番五次。當然,每次都免不了向他推銷我的前文化。結果,他對前文化的了解有所增加。但除了認識上的距離,他那里還有一個障礙:他堅持認為寫詩是個人之事,無需搞流派。當時,他正忙于編一本《第三浪潮詩選》,主要選發朦朧詩,這本書最終沒有出版,因為就在他編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改變主意想要搞流派了。那是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傍晚,他突然來找我,當晚就住在我家。他對我說:“看來是應該搞流派,因為朱鷹也有這樣的看法;就依你說的那些,把其中有關詩歌的部分寫出來。”我察覺到他的態度有變化,暗喜,但是朱鷹究竟怎么說服他的,至今仍是謎,——當然,不排除另外一個重大因素,那就是當年三月的一次談話;在那次談話中,我提到三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稱“對馬克思主義也可突破和爭鳴”。當時他很不屑,我說這是個信號,他就不再爭辯了;這次談話可能消除了他的政治壓力。于是我們開始討論流派名稱。那晚我們圍繞已基本成型的前文化理論,提出了很多名稱。一邊提,一邊掂量和商議。開始提的幾個要么寬了,要么窄了,都不合適。例如“直覺主義”,我就認為一是國外有人用過,二是與所要推出的內容不太相交——除了贊美“直覺”。這樣來去推敲,提出的都被槍斃。陋室里漸漸有了無可奈何的氣氛,這時他說,“干脆就叫‘前文化主義’算了”,言下已想作罷。我說:“這個名稱太干了,太硬了。”稍后,我說,“干脆不要在意義上繞了”一我感到從意義對位的角度已經計窮,難有結果。我的建議脫口之后,他說:“我正在想‘非非’兩個字。”我一聽,哇,沒有意義;又具有無窮的意義,聽起來相當空靈飄逸,連聲說道:“就用這個,就用這個!”我很激動,當即在筆記本上寫下日期,因為我清楚這一天意味著什么。而他呢,不那么激動。名稱就這樣確定了。緊接著明確了分工:我把前文化理論寫出,同時寫一批詩,他回去也寫一篇文章,
一他說他也有一些想法了,同時寫一批詩,并對外組稿。當晚,我們還商量了印刷與集資等具體問題,約定的時間很快來到,從聯絡中我們相互印證對方已經完成任務,于是前去成都印刷。在火車上,我們交叉“審讀”對方稿件。結果,他并沒有完成自攬寫宣言的任務。后來,他提議把我的文章的第五部分(原標題就是《前文化與非非主義》)抽出作為《非非主義宣言》。所以,《非非》創刊號上,《前文化導言》就只剩下了四個部分(原本六部分,第六部分也被抽出寫進《非非主義詩歌方法》)。如果你先讀《前文化導言》,再讀《非非主義宣言》,三讀《非非主義詩歌方法》,就會感覺氣脈貫通。回到命名問題,可以這樣說:先有孩子,共同命名。
通過前面的敘述,你也能粗略地感覺到,一開始就已注定裂變。那是一次臨時而被動的聚集:全體參與者事前并沒有統一的思想和主張,事后也未能達成深刻的共識。首批參與非非的人當中,事先聽說過前文化相關內容的只有周倫佑、劉濤和吉木狼格。其余的,有的在印刷廠里才看見相關表述;大多數是《非非》印出后才讀到——楊黎就在一些文章中稱:直到二期出刊后才讀我的文章。這種集結沒有達到具有支撐一個流派健康發展的純度。這一點你定能從非非諸君各自的申辯意味乃至抱怨意味的文章中看出。取向不一,去向各異,只不過大家的道路在這里碰巧有了一個閃光的交叉點。歷史就是這樣的,它不可能等待一切都完美無瑕了才啟動它的某項精彩,歷史是粗獷放達的……現在回頭看,經過時間的沉淀——時間/讓一切/得以展開//時間是一種/真正的實驗//時間/它讓一切/不得不/展開//時間/誰都/看不見/誰都/管不住//但時間/卻成了/試金石/躲不開——經過歷史的演變,現在可以套用普希金的韻味這樣來描繪——朋友/當一把種子/放在你手里/你不知道/它們究竟/是什么//請不要疑惑/不要煩惱/不要擔心//請把它們/播種在/時間里/給它們無數/春夏秋冬/讓它們各自/演變/而那演變出來的/東西/你一眼就能/看得/很清——我想,大家已能把問題看得很清了:在非非這面旗幟下,包裹著作為流派、作為群體、作為刊物、作為品牌,甚或作為工具的非非。先說作為流派的非非。非非是一個理論建樹偉岸而創作跟進滯后的流派。究其原因,一是理論先行:如前所述,基本理論出現于《非非》創刊之前,大多數作者并不知道這個理論。二是選稿本身并沒有尊從流派標準:《非非》創刊號急于借助良好的“時間窗口”,顧不上對作品加以苛求,因而推出的是一個好理論和若干好詩的拼盤。好理論加好詩,兩者之間缺乏流派性的必然性,或者說缺乏流派的統一性。這就有了不好的開頭。三是還存在一些詩外因素,致使沒有在踐行流派宗旨上做出更多努力。四是像這樣理論先行的個案,如果有一個健康、正常的發育、發展期,也許還能有成熟、豐收的一天,然而非非沒有這樣一個時期。這樣,作為流派的非非,事實上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非非詩歌稿件集》出版后就提前休眠,甚至可以說夭折了。當然,并不是自稱流派就是流派。作為流派,必須具備幾個要件:一是要有一個相對獨立的本體論;二是要有一個與本體論有機適應的獨立的方法論;三是要有一種與本體論、方法論相匹配的獨特的創作原則/創作方式,四是要拿出能夠印證前述三者的作品。比如超現實主義,其本體論是潛意識論——力比多能量在“本我”與“超我”的沖突與對決中,壓抑形成的無意識的動機領域和障礙性的動力領域;其方法論是宣泄論——通過宣泄釋放掉被壓抑的能量;其創作原則/創作方式是自動寫作論——創作時完全不考慮主題、意義、語法,只管自動進行,以便讓被壓抑的能量越過障礙,通過“變形”與“偽裝”盡可能通透地宣泄出來;其作品此處不贅述。非非主義作為流派也是如此。其本體論是前文化——我們生命之中一個非文化、前文化和超文化的智能活動領域,一個精彩的先驗智慧領域;在文明人這里,是一個被文化化掩蓋著,因而讓當事個體也將其迷失在自己生命里的智能活動領域;其方法論是還原論——文明人身心運行全都被文化化了,知覺、意識、思維、生命運作狀態都被文化化了,必須通過還原,才能讓主體重新發現前文化領域,并讓生命恢復到、回歸到自己最為絕妙的先驗宿命中;其創作原則/創作方式是超語義寫作——越過語義障礙,透穿文明人類已有的文化人格,去激活先驗的本來智能,實現生命個體之間前文化領域的溝通與呼喚,相當于禪宗的“以心印心”、“以心傳心”。當然,我這里要印的,是那顆非文化、前文化、超文化的心;要傳的,也是那顆非文化、前文化、超文化的心……你看,使非非能夠稱得上流派的幾個要件已經具備:前文化論+還原論+超語義論,這不僅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且是有別于當時所有流派的一個獨立自足的整體。剩下的問題就是作品。作品不是沒有,而是太少,不太成熟,難以被廣泛接受。再說作為群體的非非。非非旗下集聚了一批優秀詩人,這些詩人原本就寫詩。有的已有一些比較明確的創作主張,比如楊黎;有的并沒有什么太明確的主張,卻有一些朦朧而強烈的傾向和風格,比如劉濤、何小竹;有的此前已是一方風云人物,比如把大學生詩派運作得風車斗轉的尚仲敏;有的是詩壇老將,比如寫過《孤松》、《彈花匠的兒子》,在《星星》詩刊做過編輯的周倫佑。這是原初群體。后來,這個群體又在“各滾雪球二十里”的基礎上形成了繼生性的效應群體。這個效應群體,體現的不是觀念認同和流派特征,而是關系聯絡和情感特征。盡管這是一個十分松散的群體,但在初期,即使詩歌主張有嚴重不同,我們還是彼此包涵,透著近乎所有初始事物都具有的那么一點質樸與和諧。所以,無論是理論文章還是詩歌作品,我們都沒有嚴格按照流派標準來選擇、評判和采用,而是按照人際平衡的原則用稿,體現了相當程度的兼容性;事實上,這樣做對于流派性是一種抵消、沖淡和混淆。應當注意到,后來恰好正是群體而不是流派發生了裂變。對于流派,可以用產生、發展、停滯、過時、休眠、復活、延伸、演變之類的詞來描述,但不能用“裂變”。流派高度抽象,是一個相對統一、完整和獨立的“理論·實踐”體系,如何“裂”?如何“變”?你可以斷章取義地挖出一些東西來拼湊成“自己的”的體系,也只能算是搞出一個寄生體系,不能說母體裂變了,對吧?某些人一點也不依據原有理論體系,創造出另外一個體系,也只能說搞出了一個新流派,對吧?至于有人將原有理論加以歪曲篡改,弄出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那也不能叫裂變啊!至于作為刊物的非非,是楊黎提出來的。他說“老周把非非辦成了《非非》”,“辦成了一個刊物”。他指的是老周的復刊。周的復刊幾乎把當時活躍的青年詩人“一網打盡”,不管人家的詩歌主張如何,全攬在非非旗下。復刊后,老周之所做大抵如此:無論是紙質媒介還是電子媒介,搞的全是作為刊物的《非非》,而不是作為流派的非非。這個《非非》,我想評論界以及詩歌史無論如何都不會把它看作流派的,對吧?這是542247dd93ca19f803face417da337d1一種典型的好玩啊,給非非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難怪有人批評非非胡鬧。當然,如果不把《非非》當作流派看,就不是胡鬧了——個刊物,無論發表什么,都無所謂——如果當流派,就不能不說是在胡鬧。作出如是判斷并不難。在《非非主義宣言》——包括發表在《非非》創刊號和詩歌報、深圳青年報《詩歌大展》上的兩個版本中,關于非非主義詩派都有一系列宗旨性的界定,表明了流派非非的特定內涵和標準:“非非,乃前文化思維之對象、形式、內容、方法、過程、途徑、結果的總的原則性的稱謂。也是對宇宙的本來面目的‘本質性描述’。非非,不是‘不是’的。……將事物與人的精神作‘前文化還原’之后,這宇宙所擁有的一切無一不是非非。……將一切作前文化還原之后,語義和文化喪失,被文化(語義界定)之網膨脹起來的意識屏幕像孤帆一樣遠遠離去,這世間只剩下飄來飄去的直覺,而在直覺面前一切皆非非,直覺亦非非;宇宙之謎被還原……非非藝術,就是在遺傳工程學以外,對人類生命智慧的根本性變革負責!對保證文化指導下的人類不喪失文化外的開拓潛力和創造化潛力負責!對人類擁有的,無法用實證科學考察證明的前文化的‘基因突變’負責!”由此足見,前文化是非非之本,前文化還原是非非之根,相對于“語義化束縛”去爭取人類精神的解脫與自由,是非非努力的旨趣與方向。至于作為品牌與作為工具的非非,我們就不去談了。
你說“周倫佑和楊黎甚至相互開除”,這可能是一種誤解,又不是什么組織,開除個什么?應該說是觀點上有不同、有爭議、有指責。至于“一直保持沉默”的問題,我在這里交個底。非非的本意是要刺激人們覺悟,讓自己的精神/靈魂擺脫整個“是”的界、“非”的界,擺脫文化化的自我異化和自我分裂,這才是我理想中干干凈凈、純純粹粹的非非。然而,在現實中,它卻筋筋絆絆地被纏繞在密密麻麻的是非中,我不能奈何。我只想一點點展開非非本身,但是得看因緣啊。因緣具足時,就展開一點;因緣不足,就什么也不說。就此,我只想說這么幾句:是非是是非,非非是非非,是非非非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非非。
胡亮:你所寫下的一系列“前文化思維”理論文章,今天讀來,仍然閃爍著一塵不染的新鮮和一往無前的凜冽,就像盤古斧頭上的刃口。這些文章都帶有碎片和斷想的性質,具有言猶未盡、欲說還休的特點;對此,讀者每每產生“又讀到了其中一小部分”的感慨。“大象無形”,我們仍然在拼貼、在縫補,我現在想知道的是:是否在寫作之初,你就已經成竹在胸,然而時間倉促,你只能首先以一部分枝葉示人?目前,全書是否已經定稿?
藍馬:“碎片”?“斷想”?從讀者角度看也許確實如此。事實上,我的那套思想體系可以使用標準的學術語碼來表達,但是標準的學術語碼在我這里通不過。我追求的是一種詩化表達,把那些成熟而清晰的思想寫成一個作品,一個藝術品。這是其一。其二,我所把握的,所要介紹給大家的,像一個新大陸,沒有人開發過;對我來說覺悟已經存在,但是怎么把整個覺悟翻譯給大家,怎么在當前的語碼系統中找到翻譯媒介,是一個具體問題。一點一點地翻譯,一點一點地介紹,有一個過程。《前文化導言》僅僅提出了基本線條和框架,后來我陸續完成了一系列文章,都是介紹同一個“新大陸”,可能有時較為倉促,但是每一次表達,焦點、角度、重心都不一樣,都試圖成就一個單獨的作品。寫詩不能雷同,理論建設也應如此。具體的寫作樣式常常帶有偶發性,比如《語言作品中的語言事件及其集合》,采用了法典的表達方式:定義和相互攪擾的定義,這與當時單位上組織普法考試有關;《新文化誕生的前兆——唯文化、反文化、超文化》,有點像日記體,因為該文直接源于我的日記——這篇文章談及人與文化的三種關系:唯文化是一種蒙昧,反文化是一種困惑,超文化才是我推薦的姿態。這些文章雖然在形式感上相異,但思想上相承。前文化理論已經成文的有十幾萬字,差一點出版,最后被取消。有關前文化的思想日記就更多了,還沒有整理。當然,工作還沒有最后做完。按照我的想法,前文化思維還應該向應用研究延伸,向心理學、教育學和文化病理學延伸。
胡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語言和思想的毛荒地上,你都完成了屬于你自己的“創世紀”。如果請你只用三句話概括你的基本觀點,你會選擇哪些詞?
藍馬:前文化是一種先驗領域,是原初智慧。它是真思維,其他都是假思維。這個領域是所有真正的創造活動之所在,是所有文明文化的源泉。這個領域是人類生命心身的真正家園,是最原初的、也是最終極的歸宿,所以也是人類真正的幸福之所在。另外我要多說一句:前文化也可作為現代文明人通往佛國凈土的一條方便路徑。
胡亮:你的思想是否受到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羅蘭’巴特呢?還有德里達和羅布一格里耶?許多人認為,如果是一種巧合,就太不可思議了!
藍馬:我個人沒有受他們影響。我在《非非主義第二號宣言》中使用了“所指”和“能指”這類術語,并不知道是羅蘭’巴特的術語,我當時沒有,現在也沒有接觸過羅蘭’巴特。“所指”和“能指”這對術語當時已經十分流行。我主張超語義,需要參照物。借用流行術語可以讓人知道我所要表達的觀點:這是一種翻譯和傳遞。超語義,就是要突破“能指”和“所指”的咬合,在“能指”、“所指”形成的語言流傳統功能之外實驗附加一些新的功能。禪宗有語: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當時自覺不自覺地想要做的就是:立了文字,直指人心。
胡亮:“前文化思維”理論據說被認為是“把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是誰的觀點?你認可這個觀點嗎?
藍馬:這個評價出自成都某紡織專科學校的一位老師的自然來信,收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六日,是我的第一封讀者來信,全文如下:“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和啟示,激動人心,人類對自己的認識又探了一步。認識的范圍又拓寬了,在此基礎上,將會興起許多新的課題。思想的怪胎一旦受孕,必將生生繁衍不可遏止。”我對這個老師的觀點是認可的。因為當時人們所知道的思維,只是我說的文化思維,是遵守邏輯和語法的思維,對思維的了解就停留在這個水平,現在也還有相當部分人停留在這個水平。前文化思維的提出,讓理解者看到一個更深、更精彩、更具創造性的智能領域,完全可以說“把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當然,對此佛學早就涉及,只是當時我們不知道,所以現在應該這樣講:人類在過去進入過這個領域,只是角度不一樣,到達的境界不一樣,“起用”和“指歸”有差異。在我這里,前文化是一種思維活動,佛學則涉及“了生脫死”等更高更深層次,我的表達則更適合現代人理解,——雖然仍得不到許多人理解。離開西昌以后,許多資料都散佚了……那封信可能早已在火里,變成光明了。而我自己,對付著起伏變幻的外部世界,也在不斷舍棄、不斷放下……
胡亮:對你的激流勇退,我是贊賞的。但是,這一事實讓那些剩下來的人變成了“代表”。你作為“非非主義理論奠基人”的地位正在三人成虎式的歷史書寫中逐漸變得可疑。對此你有何看法?
藍馬:沒有辯解和爭論的必要。“歷史”只與“藍馬”有關,與我無關。我關心的是自己的東西有沒有進展,不是在外部,而是在生命內部有沒有進展。在此基礎上,我想要我的思想讓人真正受用,這才最重要!盡管如此,我也并非處心積慮,而是隨緣。并不去強推,能有什么樣的因緣,就做到什幺樣的程度。別的相關人呢?我講個比喻:有個車夫,送來好水到工地。人們一哄而上,取走了插在車上的幌子、招牌和標簽,可是沒有取走一滴水。這不是很可惜嗎?要是同時把水也取走該有多好!渴了有喝的,那才是真正的受用啊!光拿個名稱,能解渴嗎?能滋養生命嗎?送水人是希望你喝到水呀!
胡亮:這種豁達可以與老一輩的學者構成呼應,比如錢鐘書;楊絳就曾經談到,有一次,他在電話里對一個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在物質化的當下,世風日益浮躁,人心每趨功利,不免讓人產生今昔之嘆。我關心的下一個問題是:非非主義詩學曾經面臨了來自政治學的質疑,或者說,非非主義的審視者在來路不明的詩學迷霧中嗅出了似是而非的政治學氣味。這是不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藍馬:肯定是一個誤會。我個人所做的一切,是一種純粹的思想和詩歌探索,是對人生之謎的探索。我沒有任何其他企圖。愛國、愛人,是一個詩人的基本義務。并且,你看,我所展示和推廣的那些思想,本身就超越國家、民族、宗教與文化差異,它們是純粹人本的。有人往政治上掛,那是另有用心。
胡亮:非非的意義需要在非常寬的范圍之內來總結,比如語言學和思想史,但是我更關心作為詩歌流派的非非主義。時至今日,經過時間的汰洗,《冷風景》、《自由方塊》、《頭像》、《世的界》等作品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你認為非非主義留下了哪些足以傳世的作品?又有哪些作品最能體現所謂的“非非生機”?——你知道,事實上我問的是兩個問題;在這兩個問題的夾縫里,還隱藏著這樣一個問題:那些最能體現所謂的“非非生機”的作品是否恰好正是足以傳世的作品?
藍馬:如果非非只有一種宗旨:前文化,那么最能體現宗旨的作品就是《世的界》,——雖然今天看來,這件作品仍然有許多雜質。楊黎和周倫佑都有各自的追求,如果他們的詩學觀點也作為“混沌事實的非非”的組成部分,《冷風景》是楊黎比較典型的作品,強調白話中的“語感”;《自由方塊》和《頭像》則體現了周倫佑的特色,體現所謂“變構理論”、“紅色寫作”。這是一個比較溫和的表述:非非主義“一花三葉”——紅白藍。至于傳世,需要時間檢驗。我的詩受眾特別少,或者說共鳴太少。因為我的實驗對人們的閱讀習慣構成了挑戰,會遇到已經混合在人們血肉骨髓里的文化人格的抵制。但是,也有人很喜歡,能接受,這使我深感欣慰。我對非非詩的期待是語言之花:就是語言的空殼、語義上的空集合,不是傳達語義,而是促成你那里發生“直接欣賞”,或者采用語言“棒喝”,兩者都力l訇直指人心,力圖實現以心傳心,以心印心。比如《凸與凹》,在一些笨拙樸實的廢話之中突然來一句“喔皮恩”、“我們埃斯”之類,有十分特別的效果和十分強烈的實驗性。李震在其文章中就感慨說,“無論怎樣,我們確實被‘皮恩’了一下”。想想看,他如何被“皮恩”了一下?事實上,就是洞穿了他的文化鐵甲,讓他瞬間得以“返照”式體會到自己的先驗人格,體悟到自己生命中非文化、前文化、超文化領域的存在。這就叫做禪機啊,稍縱即逝的禪機!他被“皮恩”了一下,這意味著他感受到了凌厲機鋒,如果他接下這個機鋒,那么他與我之間就有一個“印心”發生。真的,現在回頭看,我當時的努力就是力圖洞穿人們生命中的文化壁壘,促成人們回頭一瞥,嘗試尋找一種藝術形式去激活人們的非文化、前文化和超文化的生命領域,讓人們得以透穿自己的文化心,自己見到自己的本心,自己見到自己的非文化之心、前文化之心、超文化之心。也就是說,當時我做了一些超語義實驗。自始至終我都認為:如果非非要成為一個流派,必須有區別于其他流派的特點。我認為只有在前文化的向度上,只有立足于前文化還原和超語義實驗,才能區別于其他流派而真正獲得流派的資格。所以,不管超語義實驗成功與否、被接受與否,它都是非非作為獨立流派的命脈所在。離開這種特質,就不能說是非非詩。因為你不能隨便拿一些詩來貼上標簽,就硬說是非非詩。當然,我并不是說,不搞超語義實驗的就不是好詩,只是說不搞超語義實驗就不合適叫非非詩。非非詩就是要表達用語言無法表達的東西,還是那句老話:“在所有應該沉默的地方,堅持一片喧嚷。”
胡亮:一九八九年,《非非》復刊,后來周倫佑提出了“紅色寫作”和“體制外寫作”,一批新的詩人比如蔣藍、雨田、袁勇、孟原等陸續加盟。周倫佑據此把—九八九年之后的非非主義稱為后非非主義。我的理解,后非非主義實際上就是非非非主義,你認為呢?
藍馬:所謂《非非》復刊,前面已經講到過,它只是一個刊物而已,表現的不是流派訴求。名稱不重要,“后非非”、“超非非”,都可以,關鍵在于是否有相應的內容。詩界不打假,但詩界并不是不懂什么叫“名不符實”。昨天我遇到一個賣松子的,有人嘗丁一口說:“都哈口了,什么時候的啊?”那小攤販理直氣壯而又故作誠懇地說:“新鮮的呢!今年的呢!”“今年的?”問話人若有所思,“不對,現在還沒到秋天呢,哪里會有松子?”猜猜看,小販怎么回答,——他心平氣和地說:“肯定是今年的,是今年一月炒熟的,二零零八年出品。”你看小販也不簡單啊,說起話來滴水不漏,可他賣的的確實是陳貨。我也嘗了一口,真哈口啊,也許是一九九八年就從樹上收下來的呢,但他卻說是“二零零八年出品”!所以,嘗嘗才是重要的。至于后非非是不是非非,你們嘗嘗再說吧。
胡亮:我瀏覽了你的新著《痛苦與幸福》,你認為“幸福本有,痛苦本無”、“除了自己能讓自己痛苦外,沒有人能讓你痛苦”、“任何痛苦的后面,必然有至少一個錯誤的想法”、“痛苦非本心,本心無痛苦”、“本然則幸福,使然則痛苦”。你是否認為,一個人之所以痛苦,乃是因為他處于一種文化狀態而非前文化狀態;換言之,你的幸福學理論是否仍然脫胎于你的前文化思維?與你的前期文章相比,你的文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奇崛入平常,這是什么原因所致?
藍馬:對,是這樣,這本書是前文化理論最新的應用成果。按照前文化理論,我提出了“幸福本有,痛苦本無”這樣一條幸福學基本原理。根據這一原理:文明人的痛苦,大多來源于文化,具體講,來源于生命的文化化。文化對人的作用可以深入血肉骨髓,改變和扭曲生命內在的運行,讓生命失去本真狀態。這是痛苦的根源。而前文化領域的存在,前文化還原的可能,恰恰為文明人提示了真正的幸福之路。因為前文化還原,能夠讓生命內部那些被扭曲的運行恢復到本然狀態,可以還生命一個其樂融融的本來面目:一個擁有天下最原版、最生態、最真正的幸福源泉的本來面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就試圖建立文化病理學。你知道生命的基本特征就是對刺激做出反應,對吧?但是對文明人而言,存在著大量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復雜的文化刺激,而這些文化刺激將在文明人的生命深處激起同樣強烈、同樣復雜的文化反應,這些盤根錯節、層出不窮的文化反應活生生鑲嵌在人們的生命運行中,是痛苦機制的真相之所在啊。幸福在哪里?在前文化里啊!前文化在哪里?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啊!我們的生命如果被文化反應堆滿,被無時不在的文化反應纏繞、牽制、扭曲著,怎么會有幸福?不在自己里面拆除這些業已存在的反應機制,哪里又能找到幸福?因為痛苦的根源機制已經大量地安裝在“自己里”了,而人們還在爭先恐后地往“自己里”安裝更多、更新的東西。真正的幸福源泉完全在“自己里”,人們卻不停地在天涯海角、五湖四海來回奔波、上下折騰……
這與語言也有很大關聯。人們掌控語言,也被語言掌控。所有文明人,他們的靈與肉,幾乎全被語言深度套牢。這就是為什么前文化理論的實驗場和應用場一開始就選擇了詩歌領域;因為詩人比別人更敏感于語言及其作用。說到這里,你看,我們當初搞流派,從根子上、從目標上,都是有人本訴求的。如果一種流派性的探索,并不包含人本訴求,那么最多只能說是在搞怪。
現在文明人的幸福學生態極其糟糕。識字、算術、務農、經商、從政,甚至殺菌、減肥、家務,都有人教,就是沒有人教幸福。海洋、地質、太空,細菌、病毒、原子,都有獨立的學科,就是沒有幸福學。不僅如此,傳播痛苦因子的東西卻充斥著我們的環境,直接教導人們如何痛苦……需要建立幸福學,《痛苦與幸福》就是一個嘗試。這本書一稿而成,沒作什么修改——不是用不著修改,而是精力時間分配不過來;為了盡可能通俗易懂,文風發生了很大變化,我不喜歡這種寫法。我已經這樣了,有人說還應該稀釋。媽呀,沒辦法了,按照以前的寫法,這本書也就幾萬字。
胡亮:下一步有什么寫作計劃?
藍馬:“痛苦與幸福”,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又是很難解決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我甚至計劃每年寫一本書,運用前文化,同時借鑒已有的哲學、宗教、醫學,聚焦于痛苦之上,建立一門專門的學問。《痛苦與幸福》只是一個匆匆忙忙的開始。當然,計劃僅僅是計劃,我現在已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我對自己最后的也是最現實的要求是: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詩寫已經基本停止,有一些東西放在那里,但我的感覺已沒那么強烈了口
胡亮:作為一個詩人,你已經沉默;作為一個佛教徒,你歸于更大的沉默。這是恐懼的后果,還是修行的結果?
藍馬:沉默是必然的,是順理成章的;因為沉默是對是非的沉默,不是對非非的沉默。非非這一塊,咱無法沉默,為什么呢?——咱不說話語權,說話語權就會有人爭,因為人人都有權發言。咱說話語力吧,非非的實際話語力、深度話語力和無窮話語力在哪里?在我這里啊l誰能把非非的事說到痛苦與幸福的那邊去?誰能把非非的事說到佛國凈土上去?非非本來甚至是可以派生出非非經濟學的,怎么個派生法?光爭話語權是沒有用的,得有足夠的話語力。話語力的背后是什么?你到底是否真正知道非非。真懂了,就有足夠的話語力了,講出來的東西就能對人有好處了……另外,在我這里,詩的內在環境與外在環境都在變,與我本意不再契合。事實上,在皈依佛教之前,我已經跋涉到了其邊緣。按照佛教的說法,我是“過去世就修過了”的,一一佛學中有“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說法,我對前文化領域的把握說明:“言語道斷”我早就做到了;“心行處滅”當時沒有做,當時做的是“心行處用”啊。從這個意義講,皈依佛門在我完全屬于必然,甚至可以說,皈依之前很久很久,我就在佛門之內了。當初那些探索性的詩,可以理解為我在不知道禪宗的情況下,對交流禪宗體驗的嘗試和呼喚,是一種尋求共鳴、尋求以心印心的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