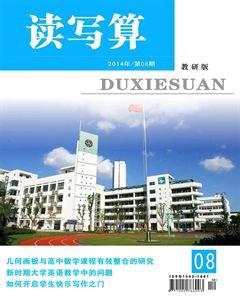如何在英語教學中挖掘學生的潛力
種云芳
摘 要:潛力是潛在的能力和力量,內在的沒有發揮出來的力量或能力。現代腦生理學的研究證實,人的大腦具有巨大的學習潛能。大腦儲存知識的能力使我們目瞪口呆,一般人只使用了其思維能力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我們能迫使自己的大腦達到一半的工作能力,我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學會數十所大學的課程。雖然人的學習潛力是巨大的,但這一潛力需要積極開發,才能使潛力變成實際的能力。
關鍵詞:潛力;挖掘;知識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08-368-01
工作已經十多年了,我一直做著和很多其他教師一樣的工作,那就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備課、授課上,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備教材上,目光放在學生身上的時間并不是很多。到底學生自身有多大的潛力,怎樣去主動地挖掘學生的潛力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認真琢磨過。這學期我要求每個學生每周背誦一篇英語高考作文的范文,我自己親自檢查督促。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很多學生的學習潛力就像一個礦藏一樣值得我們去關注,深挖。
一個高中的班主任曾經問過班里學生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在初中很多學生的英語都學得不錯,到了高中就差很多呢?學生的回答是初中單詞都記得非常牢,有助于讀懂句子和閱讀理解。而到了高中之后,單詞很多都沒有記住,句子都讀不懂,更談不上對大量閱讀的理解了。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雖然我們知道初中教師和高中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要求不一樣:初中很多情況下是教師在學生后面攆著追著學生去學習,學生的自主性學習相對較弱。而高中教師更多的是希望學生自己能夠自主學習,所有跟在學生后面監督其學習的情況非常少。按道理說高中學生學習的氛圍應該是更加寬松的,有更多的時間由他們自己安排,自己應該知道自己學習的目標、方向和動力。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很多學生到了高中仍然沒有學會自己安排時間,大量本應自己安排的時間就在無所事事中被浪費掉了。究其原因我們發現懶惰情緒有不可推脫的責任。
我們都知道每個人身上所蘊藏的潛力都是不可估量的。只有想方設法將其挖掘出來才能更好地利用這些潛力。但因為懶惰,很多人別說是挖掘潛在的能力,就連最基本的潛力也沒有真正利用。所以在我看來懶惰才是阻礙我們利用、挖掘潛力最大的障礙。因此學生如果能戰勝自身的懶惰,那么每個人都將有很大的作為。但是很遺憾,很多學生自己并沒有感覺到自己的懶惰,那是因為他們自己過的很舒適,目標模糊,方向也不是很明確。針對這樣的情況,老師適時地拉學生一把,或者適時地做一些督促,激起學生的斗志,讓學生點燃自身的熱情。我們的目的是點燃學生自己奮斗的熱情。只要有了學習,或者奮斗的激情和熱情,其余剩下的事情我想學生自己會探索,尋找,發現維持這樣的激情和熱情,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就會知道自己怎么做。就拿這學期我要求學生背誦英語高考作文來說,剛開始很多學生沒有嘗到甜頭,總是認為英語老師和他們過不去——因為他們的英語基礎不好的原因。或者持有這樣的觀點:背誦那些對提高他們的英語成績沒有多大的聯系,還浪費他們寶貴的學習時間。因此大多數學生都是被動地去背誦,去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和任務。后來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我們遇到了相關的句子,很多學生因為經過了背誦,相關的句子都能夠達到脫口而出。慢慢地很多學生轉變了看法。開始變被動為主動。有些學生,尤其是英語基礎較弱的學生竟然發現他們經過努力也能背誦過英語文章。這是以前他們沒有預料到的。他們沒有預料到自己身上竟然也能發生讓他們預料之外的事情----他們身上竟然也有這樣的潛力。對于這樣的情況很多學生也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他們自己也感到了懶惰阻礙了他們進步的腳步。學生自己也想進步,他們也希望借助一些力量,讓自己走得更遠,收獲更多。所以學生自身的潛力我認為必要的時候還是要借助外力來幫助其挖掘。
有很多學生在英語學習方面因為基礎弱的原因,心理上非常不自信――總認為自己英語不行,并且把這樣的認識通過心理暗示遷移到學習的其它學科上。逐漸地就變得不自信,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學習的興趣。因此我認為我們的教學,把目光不要緊緊盯在學習成績上,更多地應該從課本中走出來,把精力放在課本知識與學生實際認知水平的鏈接點上。通俗地說就是讓學生在日常的學習中享受學習帶來的樂趣。
作為一個高中生,其英語學習潛力是巨大的,但這一潛力需要積極開發,才能使潛力變成實際的能力。那么怎樣開發學生的學習潛能呢?
1、要樹立遠大志向。古人講“非志無以成學”、“志不強者智不達”。所謂立志就是激勵自己走向一條進取的、迎難而上的、智慧的人生之路。人有了志向,就會變得勤快,就會對自己嚴格要求,就會克服前進路上的任何困難,他的聰明才智才會發揮出來。
2、要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健康的身體、充沛的精力、愉快的心情可使人的智力機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反之,人的智力活動就會受到壓抑。可見身心健康是開發潛能的基礎。要提高身體健康水平,可以從飲食、睡眠、鍛煉三方面進行調整。要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需要涵養自己的性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
3、培養良好的心理品質。心理品質包括道德品質、意志品質、自信心、責任心等。有一位心理學工作者對1850年到1950年間的301位科學家進行研究,發現這些人不但智力水平高,而且在青少年時期就表現得十分堅強,有獨立性,這些人充滿自信心,有百折不撓的堅持精神。可見,培養良好的心理品質對開發人的學習潛能作用重大。
現在社會上流行一個詞叫“接地氣”,比如某個受歡迎的接地氣的專家。作為教師,我們每個人也應該思考:如何通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探索讓自己成為一個接地氣的教師。只有這樣我們才會用平行的視角觀察學生,用心發現學生。也才會尋找到一些適合學生認知水平的接地氣的方法來鼓勵學生不斷地自我發現,自我肯定,自我探索。學生的潛力也不斷地在自我肯定中得到挖掘。所以我們應該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尋找方法,給學生提供挖掘潛力的機會和平臺,讓學生的自信在挖掘潛力和學習過程中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