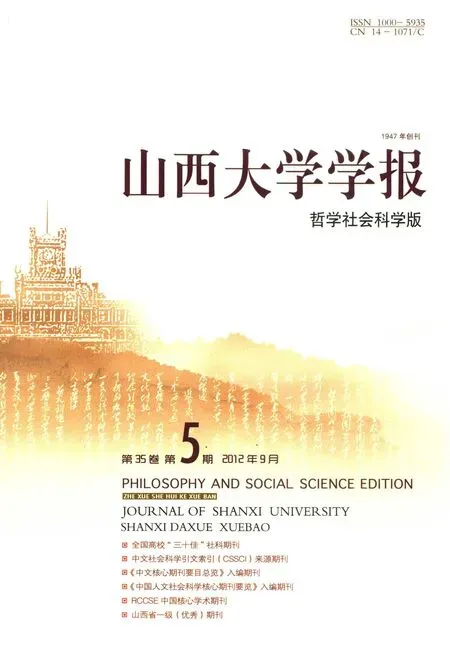漢藏同源假說與古音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漢藏同源的譜系關系及其研究方法討論
張民權
(中國傳媒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24)
漢藏同源假說與古音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漢藏同源的譜系關系及其研究方法討論
張民權
(中國傳媒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24)
漢藏同源是一個未經(jīng)證實的假說,其同源的歷史范圍及其譜系關系,迄今為止,仍是一個聚訟不決的話題,學界還沒有一個令各方都能接受的研究成果,因此,漢藏同源說基本上還處于有待科學證明的過程之中。而其中研究方法至關重要,基本詞匯的確定,同源詞的擇取和音系的比較構擬,都不能簡單地從想象出發(fā)。文章就漢藏親屬語言的譜系關系及其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和檢討。
漢藏同源;譜系關系;時空差異;研究方法
漢藏同源及其譜系關系是個非常復雜的歷史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未經(jīng)證實的假說。在這個假說基礎上進行漢語上古音系的構擬,必然要面臨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和阻力。從目前一些比較構擬的研究成果看,并不是很成功,其中問題很多。主要原因在于對漢藏語系及其性質還沒有認識清楚,在同源詞的比較上缺乏一個嚴格的語音對應規(guī)則,在音系構擬上嚴重脫離漢語事實而乞靈于外部比較,因此,關于漢藏同源及其比較構擬問題有必要作一番檢討,正本清源,勢在必行,以推進漢語上古音研究的健康發(fā)展。
我們認為,如果真的要從漢藏親屬語言出發(fā)去研究漢語上古音,首要的工作是將漢藏親屬語言的譜系關系及其歷史范圍弄明白,包括漢族與周邊民族的歷史接觸等,然后才談得上同源詞的歷史比較與上古音系的構擬。
這項巨大的工程,至少包含了三個相關方面的研究工作:
Ⅰ.具有親屬關系的語言調查工作,在國內往往表現(xiàn)為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調查描寫;
Ⅱ.漢語譜系關系的研究工作;
Ⅲ.從漢語的親屬語言出發(fā),通過同源詞的比較構擬漢語的上古音系。
第一項研究工作,就國內研究來說,我們的民族語言學的專家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績斐然,這從近年來少數(shù)民族語言志的編輯出版可以看出來,其次是相關的研究著作的出版。這些研究成為以下兩項研究工作的基礎,沒有民族語言的調查描寫就無從討論譜系關系和上古音的比較構擬。
第二項研究工作雖然有百年之久,但至今為止,中外歷史語言學家并沒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各家異詞,所有的假設都是猜想,由于歷史比較的基礎工作沒有做好,漢語在那遙遠的時代,究竟與哪些語言具有發(fā)生學的同源關系,仍是一個想象中的神話傳說。
第三項工作,可以說毫無進展。一些中外學者從假設的親屬語言如漢藏語系出發(fā),比較構擬出一套復雜的上古音體系,既脫離漢語事實,又不符合親屬語言的音系特點,有些不倫不類,有損漢語的純潔性,也扭曲了歷史比較法的原則精神。
我們并不否認這些學者的探索精神,面對不足,需要的是在古音觀念和研究方法上加以反思和檢討。
漢語上古音研究,經(jīng)過清代學者前赴后繼的努力和近現(xiàn)代前輩學者的開掘,在古韻部類的劃分上已日趨完善,但在古聲母研究方面,仍留有許多研究和討論的空間,無論是在上古漢語聲母系統(tǒng)還是音系構擬上,學術界都未能取得比較一致的看法,而分歧點主要集中在單聲母還是復聲母及其音型結構上。半個世紀以來,人們試圖從親屬語言同源詞的比較構擬中來解決這些分歧,但不是很成功,其中問題甚多。
學術要傳承要發(fā)展,就必須做到觀念更新和研究方法的改進。對于漢語上古音研究,一方面我們要繼承傳統(tǒng)古音學的成果,努力發(fā)掘其中合理和精華的部分;另一方面,又要在觀念和方法上不斷改進,以解決傳統(tǒng)古音學不能解決的問題,進一步推進上古音研究,但如果完全拋棄乃至斷言傳統(tǒng)音韻學的研究方法不適應做上古音系研究,那就非常錯誤。自高本漢以后,很多中外學者矻矻探索,為漢語上古音系的構擬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成為我們的研究基礎。當前,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漢藏同源說與復輔音聲母的“比較構擬”,似乎成為當下的學術“主流”,大有非我莫屬之勢。①我們注意到,少數(shù)中外學者曾持有這種看法。如梅祖麟批評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研究說:上古音基本上是中古的格局,聲母部分和韻尾部分沒有復輔音,不適于做漢藏比較的構擬研究;藏文有種種復聲母,有豐富的輔音前綴和后綴,如用王力音系,“我們簡直不知如何作比較”[1]。我們認為,梅氏此說是非常錯誤的,在漢語上古音與漢藏同源的性質關系還沒有弄清楚以前,而把假設當成最后的結果。然而漢藏語系的歷史比較研究起步較晚,其歷史比較法的理論還沒有完善,有關研究實際上還處于探索階段,離我們期待的目標仍有很遠,無論是在觀念還是在研究方法上仍有反思檢討之必要,借用一位民族語專家的話說就是:“漢藏語歷史比較的方法確有許多問題需要檢討。”[2]
需要引起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是:
(1)漢藏諸語言真的同源嗎?(2)同源發(fā)生的時代及其歷史范圍又是什么?(3)漢藏語分化以后各自發(fā)展演變的方向如何?(4)歷史語言的比較法則及其適用范圍;(5)具有同源關系的基本詞匯我們現(xiàn)在究竟能確認多少?等等。
如今,關于漢藏歷史同源問題,似乎成為民族關系史和民族語言的學者喜歡援引的一個話題。然而,殊不知,族源關系與語源關系并不是一回事,關于漢藏語系歷史同源問題,迄今為止,仍是一個未經(jīng)證實的假說,而并非一般人所說的得到“公認”,實際上反思和質疑的聲音一直不斷。證明族源關系似乎比證明語源關系要容易得多,因為前者可以借助地下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乃至文化學、人類學和生物遺傳學原理,而語源關系卻要靠語言文字,如果其中某個民族沒有文字記錄的歷史文獻,又缺乏一定數(shù)量的共同詞根,要證明兩者的語源關系,尤其是那遙遠的語源關系,就要面臨方方面面的阻力和艱難。
下面,就其中一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淺陋之處,企望于方家教正。
一 漢藏語同源的歷史范圍及其譜系關系問題
(一)漢藏語同源的歷史范圍問題
根據(jù)漢藏同源理論而進行漢語上古音的比較研究,首要的前提是必須明確“漢藏同源”的歷史時間,即在何時這些親屬語言具有發(fā)生學的關系,而后何時分化再形成了哪些語族語支,然后我們才可以進行漢語上古音系的研究工作。
然而,到目前為止,那些利用漢藏同源理論進行漢語上古音“比較構擬”的著作,很少對此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或者是閃爍其詞,語焉不詳;盡管在這些著述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諸如“原始漢藏語”、“原始漢臺語”等描述,但始終是一個天才的想象,如果以此為前提進行上古音研究,是非常不科學的。按照雅洪托夫的表述:“上古漢語從藏緬語中分化出來的年代是公元前25或 35世紀。”[3]83據(jù)歷史學家翦伯贊《中外歷史年表》的考證,公元前25世紀是中國炎黃時代,距離我們約 4600 年。[4]1-3至于公元前 35 世紀,那只能是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時代。包擬古出于謹慎,認為其下限在“公元前2000年的前后幾個世紀之間”[5]53,這個時間點大致在堯舜之后夏啟之前。然而,不管采用哪家說法,漢藏同源的假設時間至少在5000年前的史前時代,一般認為是六至七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不過這些都是推測,還沒有足夠的事實依據(jù)讓我們能夠接受。
(二)漢藏語系的譜系范圍問題
其次,“漢藏語系”的譜系范圍包括哪些“親屬語言”,似乎也是一個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混沌,小到中國境內的一些少數(shù)民族語言諸如藏、緬、傣、苗、瑤等,大到境外東南亞各國之語言,諸說紛紜,莫衷一是。一般的看法是,漢語跟藏緬、侗臺、苗瑤三大語族組成漢藏語系,這是李方桂先生的觀點,馬學良先生主編的《漢藏語概論》的篇章結構即是如此。但有人認為侗臺、苗瑤語跟漢語沒有發(fā)生學的關系,它們之間只是語言接觸與借貸關系,相反,漢語與南島語關系更密切,應當與南島語一起另立為澳泰語系,這是美國學者白保羅的觀點。后來有人干脆提出漢語與南島語同源論,這也是法國學者沙加爾的主張,似乎為國內一些學者所接受,諸如邢公畹、鄭張尚芳和潘悟云等都將他們的比較范圍擴大到了南島語系。然而這種假說立即就遭到了很多中外學者的質疑,馬提索夫、蒲立本和李壬癸等都有批評文章(參見孫宏開、江荻 1999[6],王士元 2005[7])。同時,反對漢語與藏緬語同源說的也大有人在,如法國學者沙加爾就是。[8]345,514這種認識分歧和富有爭議的背后,本身就說明“漢藏語系”是一個未知數(shù),而這種龐大的語系在還沒有得到科學論證以前,匆忙進行古漢語音系研究,可能會走向一條很危險的道路。
除了以上觀點以外,還有兩個著名的觀點:一是蒲立本等歐洲學者所認為的漢語(漢藏)與印歐語系同源,不僅有考古學上的證據(jù),還有音系學和形態(tài)學乃至同源詞的證據(jù)[9]228。此外俄羅斯學者斯塔羅斯金等學者認為,應當建立一個獨立的“漢藏——高加索”超級語系,也就是說漢語與北高加索和葉尼塞語具有同源發(fā)生學的關系,而且也有考古和語言學的證據(jù)[10]372。今天處于西伯利亞的葉尼塞語的族群一般認為是古代匈奴的后裔,匈奴語實際上就是后來的阿爾泰語系,歷史上的契丹語與蒙古語等都是它的后裔。照此推論,漢語與阿爾泰語系也是同源關系。不過蒲立本認為,匈奴人的語言實際上屬于印歐語系,這樣,他的觀點與斯塔羅斯金的看法可以互相印證。
如果綜合上述各家觀點,漢語的“祖先”在遠古時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家族,幾乎跟地球上所有毗鄰或發(fā)生過接觸的語言都有親屬關系。然而,無論是漢藏語系說,還是漢語——南島語系說,抑或漢語——印歐語系說、漢語——北高加索——葉尼塞語言聯(lián)盟,都沒有一個可以互相說服對方的理由,更沒有一個令各方都能夠接受的同源詞或核心詞匯表。如果站在爭論各方對立的立場看,各家之說均不能成立,矛盾和漏洞甚多。這些爭議的文章編輯在一本名曰《漢語的祖先》的論文集中,讀者可以參閱。①此書由王士元主編,發(fā)表于1995年美國《中國語言學報》論叢之八,2005年由李葆嘉等人翻譯,中華書局出版發(fā)行。標記中的頁碼為中譯本的頁碼。從這些文章中,各家觀點針鋒相對,借用白一平的話說就是:“一些語言學家認為確鑿無疑的假設,卻被另一些語言學家視為胡言亂語而不屑一顧。”[11]116我們應該感謝王士元先生和李葆嘉先生,為我們編譯了這部叢書,使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關于漢語親屬語言的譜系關系實際上是沒有定論,各派觀點都有,而絕不是一些人所認為的“漢藏親屬語言關系”非常清楚。
如果掩蓋或漠視這些是非爭議,從一個不確定的“漢藏語系”出發(fā),來進行漢語上古音的比較構擬,其結論的可靠性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二 親屬語言的內部差異問題
鄭張尚芳先生和潘悟云先生等都主張建立一個廣泛同源聯(lián)系的超級語系,名曰“華澳語系”,可是他們未曾想過,在這棵龐大的譜系樹中,漢語的根結點又在哪里?究竟能確定多少同源詞?其內部差異又是如何協(xié)調的?
也就是說,既然“漢藏語系”有如此龐大的親屬語言,我們研究的時候是否考慮過它們之間的差別?是否對其中每一支語屬都進行過歷史研究?
比如說,假設漢語與藏語被證明有某個同源詞,其語音形態(tài)等在其他語言中,諸如緬語、侗臺語、苗瑤語、孟高棉語和印度尼西亞馬來語等,是否也是這樣成系統(tǒng)的比較對應關系?事實上不可能如此,從現(xiàn)在發(fā)表或出版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材料看,完全可以說明這一點,例如在《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中有“親屬關系”的藏、緬、苗、瑤、壯等民族語詞匯中,如果從中抽取“天”“地”“山”“河”“牛”“羊”“雞”“鴨”等基本詞匯進行比較,你會發(fā)現(xiàn),語音形式差別非常大。當然你也可以解釋,這是后來語音變化的結果,但是,如果你不能從歷時上解釋這些共時的差異,歷史比較法就失去了意義。
確定同源詞是建立語言親屬關系的前提。按照歷史比較法的原則,同源詞的比較是建立在嚴整的語音對應規(guī)律上。其比較的范圍一般包括形態(tài)、語音和詞匯三方面,但是與印歐語系不同,漢語與藏緬諸語支的比較有相當?shù)碾y度,有的沒有形態(tài),語音結構形式差別甚大。所以在沒有形態(tài)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在語音詞義的比較上嚴格要求,也就是嚴整地有系統(tǒng)地比較。然而遺憾的是,很多人并沒有嚴格按照歷史比較法的原則去做。
即使是同一種語系或語支,其內部差異也是非常大。下面以戴慶廈和黃布凡等先生的藏緬語研究為例,他們都是民族語言學的權威專家,其研究結論可靠,值得信賴。
根據(jù)他們的研究,藏緬語內部差異很大,其同源詞的比率僅有20%左右,甚至更低。例如在《漢藏語概論》中,黃布凡先生以羌語為例,選取1 500個詞語進行比較,羌語支內部同源詞的比率從10%以上到20%不等,而與藏、緬、彝、景頗語的比率均在10% 以下。[12]355如羌語(峨口)同各語言的比較:
卻域(新龍)16%,木雅14%,扎壩12%,嘉戎12%,普米(九龍)16%,道孚13%,爾蘇(九龍)17%,貴瓊10%,藏語(書面)7%,彝語9%,納西9%,景頗6%
這些數(shù)據(jù)還可以在另外一部權威性的教科書中得到印證,由社科院民族語言研究所編寫的《藏緬語語音和詞匯》一書,選取了1 000個左右的詞語、52個語言點進行調查取樣,詳細描寫其音韻特點。其結論是:
“根據(jù)我們對材料進行初步分析,在1 000個左右常用詞中,多數(shù)語言彼此都有同源關系的詞將近200個,占所列常用詞的五分之一左右。”“有一部分詞,在某一語支內部是一致同源的,但與其他語支則看不出同源關系,也有一部分詞,某一兩個語支有同源關系,而其他語支則看不出同源關系……例如,藏語支內部比較一致,而與藏緬語族其他語言比較則看不出明顯同源關系。”[13]2-3
以上還只是藏緬語內部,如果再將這1 000個詞匯放到壯語、苗語、瑤語以及南島語系中進行比較,其“同源關系”的比率不知還會有多少。如果漠視這些差異,我們漢語上古音的比較構擬將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
因此,要建立和證明漢藏親屬語言關系,首要的工作是在親屬語言內部進行比較,確立一定數(shù)量的同源詞,而后是語族與語族之間的比較,如藏語與苗瑤語等,然后再擴大到整個“華澳”語系,最后才是漢語與諸語族的比較,找出其對應規(guī)則,歸納其同源形式。把這些工作做好以后,才是漢語上古音系的比較構擬。如果不考慮語族語支之間的差異,親屬語言同源詞的比較就會變得隨心所欲,毫無原則可言。
三 論證方法上的音系構擬與詞語擇對問題
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我國的民族語言學專家學者在親屬語言的譜系關系的建立,以及親屬語言的調查描寫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有些問題不能回避,有的是一般性問題,無傷大雅;有的則是方法論上的原則性問題,必須認真對待。
(一)是否可行:通過漢語上古音的構擬來確立親屬語言的同源關系?
由于各語族語支之間存在較大的語音差別,人們采用了以漢語古音構擬來尋找同源關系的辦法,以折中于各語系之間的差別。這樣做是否切實可行,令人懷疑。例如倪大白先生就對李方桂漢臺同源觀點提出過類似的懷疑和批評,曰:“漢語與壯侗語究竟是什么關系?是同一語系中的親屬語言嗎?迄今為止,我們還是很難找到漢語、壯侗語之間真正有對應關系的同源詞。”[14]922并委婉地指出,依靠構擬上古音來解決漢臺語之間的關系,“會不會仍然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胡同呢”?因為從構擬的漢語古音出發(fā),很容易誘導人們去挑選那些語音相似的詞語,而排斥那些語音不相似的同義詞,從而陷入循環(huán)論證的境地。
誠然,從構擬的漢語古音出發(fā)去尋找同源詞,其好處在于有個方向性,可以避免一些無頭緒的盲找,但是,如果構擬的上古音系存在嚴重缺陷,那尋找出來的“同源詞”就難以建立。尋找出來的至多是一些語音相似的詞,正如倪先生所指出的,“正好缺少了最主要的一環(huán),即同源詞”[14]921。
觀看一些中外學者有關研究文章,其所參照的漢語古音體系不外乎這樣幾家:高本漢、李方桂以及鄭張尚芳和潘悟云等構擬的古音體系,此外,蒲立本和斯塔羅斯金等又有自己的一套構擬。其中李方桂的古音構擬影響最大,它揉進了雅洪托夫和蒲立本等人的音系觀點,例如二等韻的介音問題、來母、喻四的性質和復輔音的S-詞頭問題,其音系構擬多為海內外學者(如龔煌城、李壬癸、丁邦新、梅祖麟、邢公畹等)廣泛采用,用來進行漢藏語系的比較論證。而鄭張和潘氏的音系構擬,雖以李方桂和包擬古等構擬為基礎,卻摻雜了許多個人大膽的想象:藏緬語的面孔,南島語的眼睛鼻子,漢語的衣冠,等等。
但是,一些中外學者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大多沒有經(jīng)過嚴格的論證,其構擬的基礎雖曰親屬語言比較,其實是循環(huán)論證。或抓住漢語諧聲異讀的個別例子而加以推理,不惜犧牲系統(tǒng)而遷就個別例外,“根據(jù)不足,未免冒險”[15],在論證上缺乏應有的說服力。
例如,鄭張(2005)[16]442和潘悟云(2005)[17]242為了回答白保羅和沙加爾對漢語與侗臺語同源關系的質疑,舉了兩個這樣的例子:(1)侗臺語的“鳥”mok對應漢語的“鶩”*mooɡ,同時藏語的“鳥”bja對應漢語的“鳧”*ba;(2)漢語的“翼”*b·l?g對應侗臺語的“翅膀”pik。這是比較構擬中兩個非常典型的錯誤,“鳥”是通名,而“鶩”“鳧”(野鴨)是專名,既然鳥可以對應野鴨,也可以對應野雞(雉)野鵝(雁)乃至孔雀和禿鷲之類等等,滉漾無涘矣!也不思慮:既然漢語、藏語、侗臺語歷史同源,為什么“鳥”的語音形式差別如此之大?而“翼”字的古音構擬更是讓人匪夷所思。

這里我們再引述白一平批評白保羅的一段話:
使用構擬形式比較之時極易出現(xiàn)循環(huán)論證,因為很難決定究竟使用哪一個構擬形式為宜。白保羅(1972)詞表中列出的都表示one的三個不同的藏緬語詞根:*it,*kat,*(ɡ -)tyik。如果就詞源而言,*it似乎與上古漢語“一”*?jit/k更明顯配對。但在統(tǒng)計學檢測中,僅僅是因為*it貌似同源就挑選*it而排斥其他兩個,這本身已在循環(huán)論證。[11]144-145
白一平指出的這種循環(huán)論證,在漢藏親屬語言的比較論證中帶有很大的普遍性。科學的比較法應當是排除主觀先見,以充分的語言事實比較而后建立同源關系。但這樣做確實很難,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無需為尊者諱,總結以往研究中的經(jīng)驗教訓,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研究。
(二)是否偏執(zhí):無原則地遷就親屬語言而進行古音構擬?
以藏語為例,我們知道漢語與藏語在語音形式上差別很大,藏語有豐富的復輔音聲母及復輔音后綴,而漢語沒有。漢語有聲調,而藏語沒有聲調(現(xiàn)代藏語某些方言的聲調是后來產生的)。中古漢語聲母有送氣不送氣對立,有清濁對立,而藏語沒有,等等。按理說,如果兩種語言的語音性質差別這么大,是無法同源,也是無法比較的。要么就有兩種假設:第一,藏語在上古時代也同漢語一樣,聲母是單輔音,有清濁對立的,有四聲變化,等等;第二,漢語在上古時代也像藏語一樣,有豐富的形態(tài)變化和豐富的復輔音聲母等。
但是,無論采用哪一種假設都必須經(jīng)過嚴格的論證,包括歷史事實與語言事實的論證。從目前學術界的研究狀況看,人們沒有采用第一種假設,因為無法說明藏語復雜的語音形態(tài)后來是怎樣產生的。于是,人們更愿意采用第二種假設,上古漢語也像藏語一樣,有豐富的形態(tài)變化和復雜的復輔音聲母系統(tǒng),漢語的聲調是后來產生的,等等;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一些中外學者為漢語上古音構擬了一套復雜的復輔音系統(tǒng),成為證明同源關系的重要參考。于是,這套復雜的古音構擬,后來被一些研究漢藏親屬語言關系和研究漢語古音的學者所采用,并加以發(fā)揮。
但是,即使我們采用第二種假設,仍然有很多問題難以解決。如果上古漢語有豐富的形態(tài)和復輔音結構等,那么,這些語音特征又是在什么時候消失的?從秦漢時期的漢語對音看,至少還看不出有復輔音結構,《詩經(jīng)》用韻四聲分押的界限還是比較清晰,說明《詩經(jīng)》時代(公元前10-6世紀)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又漢語是分析型語言,沒有形態(tài)變化,這些從商代的甲骨文中就表現(xiàn)出來了。所謂形態(tài)變化,往往表現(xiàn)為某個詞語的語音屈折變化,如藏語的動詞就有現(xiàn)在時、未來時、過去時、命令式、自動與使動等多種時態(tài)、語態(tài)的語音屈折變化。如“完成”一詞,就有六種語音變化形式:
使動:sɡrub(現(xiàn)在時)bsɡrub(未來時)bsɡrubs(過去時)sɡrubs(命令式)
自動:?ɡrub(現(xiàn)在時)?ɡrub(未來時)ɡrub(過去時)[18]
如果我們承認甲骨文是分析型語言,那么,我們就必須承認當時的漢語不會有古藏語那樣的語音形態(tài)變化。同理,《詩經(jīng)》為詩歌作品,句式整齊,富有韻律,如果漢語有語音屈折的形態(tài)變化,怎么能夠形成整齊的音節(jié)及其韻律?如《關雎》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這些詞語如有繁復的復輔音結構加上形態(tài)變化,古人如何歌詠?可能我們的研究者還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的語言事實,漢語詩歌作品押韻方式及其韻律特征與藏緬語等少數(shù)民族(包括蒙語、滿語)不一樣,這是漢語的獨特之處。
如此看來,漢語自商代甲骨文至周秦兩漢以來,既談不上與藏緬語有發(fā)生學的關系,更談不上像藏語那樣有豐富的復輔音結構形式。
我們認為,無論是研究漢藏同源關系還是構擬上古音,都離不開對漢語史的考察。撇開漢語歷史事實不顧,一味乞靈于外部比較構擬,恐怕是一條永遠走不通的路。
下面是潘悟云先生的一段相關言論,頗有驚人之處。引述大意如下:
藏語與漢語的同源關系最為清楚。在能夠與漢語進行歷史比較的語言中,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語與上古漢語最為接近。
藏文有豐富的形態(tài)變化。在語音形式上,藏文有豐富的輔音前綴,諸如 b-、d-、ɡ-等塞音前綴,l-、r-等流音前綴,最重要的是有咝音和鼻音前綴;有豐富的輔音韻尾:-b、-d、-ɡ、-m、-n、-?、-r、-l、-s 等; 藏文沒有聲調,有次要音節(jié),在原始藏緬語中還有小舌塞音,等等。……
藏文的這些音韻特點,都在漢語上古音的構擬中得到反映。[19]140
以上都是潘先生的原話,為行文簡便文字上略有調整而已,讀者可以對照。然而就第一段文字而言,“同源關系最為清楚”、“與上古漢語最為接近”,潘書始終沒有向我們提供任何的史實依據(jù)。拿一個未經(jīng)證實的假說來構擬漢語上古音系,其研究的風險不言而喻。這點姑且不說,后面一句話最耐人尋思:“藏文的這些音韻特點,都在漢語上古音的構擬中得到反映。”這句話如果作通俗的解釋就是:凡是藏文所具有的聲韻特征在漢語上古音的構擬中也應當有。這種說法實在讓人不敢茍同,就好比在孔子今天的后裔中,假如有人臉上長了胎痣,或者是駢枝,難道2500年前的孔子也一定會有胎痣或駢枝?
翻閱潘先生著作,確實是這樣構擬的。并且,藏文中沒有的音韻特點也參考“華澳”語系統(tǒng)統(tǒng)給用上。如是,上古漢語就成了多重雜交的混血兒怪胎!
我們知道,藏文只是公元七八世紀的文獻,而漢語與藏語同源的時間按照雅洪托夫的說法至少也在5000年以上。這其間就沒有“變異”?實際上,觀察他們的研究,用的還不都是藏文材料,而更多的是現(xiàn)代藏語材料。
退一步說,就算你全部用藏文或藏語材料,漢語與藏語之間的同源關系詞又會有多少?且證明了多少?前面以黃布凡和戴慶廈等先生的研究為例,藏緬語族內部的同源詞還不到20%,有的甚至更低,在10%以下,由此推論,漢語與藏語之間的同源詞恐怕就屈指可數(shù)了。如此,我們憑什么可以說:“藏語與漢語的同源關系最為清楚”?
四 比較構擬與漢語上古音的歷史層次問題
既然是比較構擬,就必須考慮漢藏同源的時空差異和古音的歷史層次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構擬的漢語古音是哪個歷史時段的?一般地,我們所說的漢語上古音是指周秦時代的語音,此時有豐富的文獻可征,如《詩經(jīng)》和漢字諧聲等。而夏商時期文字材料缺乏,只好闕疑。至于更古的炎黃時期乃至六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的語音,那是無法知曉的事情。雖然發(fā)掘出很多古人類文化遺址,如大汶口文化遺址、仰韶文化遺址、良渚文化遺址、紅山文化遺址等,出土了大量的歷史文物,但只能說明當時人類的生產活動,無法說明其語言情況尤其是語音情況。而人們心目中所向往的所謂“漢藏語同源”也是在仰韶文化時期,即新石器時代。然而語音研究必須以文字記錄的歷史文獻為依據(jù),實事求是,這是樸學的一個基本精神。否則,毫無意義可言。
語音發(fā)展有歷史層次,周秦語音不同于漢魏語音,漢魏語音不同于隋唐語音,同理,原始漢語或夏商漢語與周秦漢語也一定有所不同。區(qū)分語音的歷史層次及其地域范圍是傳統(tǒng)古音學的精髓,也是我們必須遵循的一條準則。然而,近年來我們的一些研究卻與此漸行漸遠,在漢藏語系的歷史范圍還沒有確定的情況下,動輒以現(xiàn)代親屬語言的比較為前提,構擬上古漢語音系;在漢語“古音”層次還沒有梳理清楚的情況下,又大談特談所謂“原始漢語”或“原始漢藏語”的語音。在他們構擬的“古音”中沒有一個明確的歷史時限,上下幾千年,跨越幾個歷史層次。
下面不妨引述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的觀點,其說很有代表性。其曰:
明清時代研究上古音的學者主要依據(jù)《詩經(jīng)》葉韻,所以長期以來“上古音”的常規(guī)意義是指先秦兩周時期的語音。但是現(xiàn)在我們的研究范圍則要大得多,上至原始漢語,下至三國(甚至像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里所主張的最晚到五胡亂華之前——原注),都可以納入上古音系的研究范圍。……這樣從史前到魏甚至西晉,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遠古——原始漢語,指史前期的遠古漢語。
前古——上古前期,指約當殷商的前上古漢語。
上古——上古中期,指約當兩周的上古漢語。
次古——上古晚期,指約當漢魏的次上古漢語。
他解釋說:“‘原始漢語’是參照了從親屬語比較所得的原始漢藏語形式來修改上古漢語形式所得的結果,它是‘前古’漢語的某種重擬式。‘前古’漢語則以諧聲、通假作為主要根據(jù),重點是復聲母系統(tǒng)的研究;‘上古’漢語各種根據(jù)最為充分,自然是上古音研究的主體;‘次古’漢語則有梵漢對譯、古漢越語、古漢朝語等對音材料相比證。”[20]5-6
仔細推敲上段文字,其邏輯關系是非常混亂的:從其描述中,我們知道“原始漢語”的上位概念還有個“原始漢藏語形式”,然后再由上位概念下推下位概念,然而不是從“前古”上推,而是從下面的“上古”上推合圍。既然“原始漢語”不清楚,而“原始漢藏語”豈不成了天外來物?可惜的是,鄭張先生雖劃分了四個歷史層次,但各歷史層次之間的語音有無區(qū)別呢?他沒有說,也無法說清楚。
“原始漢藏語”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時間概念,恐怕連鄭張先生本人也不清楚。僅憑現(xiàn)在的親屬語比較,就能得出原始漢藏語形式?這本身就值得懷疑。我們認為,任何侈談“原始語”的建立與研究,借用梅耶的話說,都只是一種天才的想象,[21]16-17①梅耶指出,任何構擬都不能得出曾經(jīng)說過的“共同語”。并批評施萊歇爾以構擬的原始印歐語寫作《山羊與馬》的寓言,“是一種天才的大膽”和“一個嚴重的錯誤”。缺乏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語言事實以及科學的論證。
首先,是研究觀念上的錯誤,違背語音變化發(fā)展的時地觀。從“原始漢藏語”到今日漢語或親屬語言,時間跨度至少也有5 000年,這期間,難道漢語和“親屬語”的語音就沒有時地變化?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都知道,宋代吳棫朱熹研究古音,不懂得古音的歷史層次,將《詩經(jīng)》音與唐宋音混淆在一起,上下兩千年,所謂古音可以通可以轉。這種古音通轉葉音說曾受到明清學者陳第、顧炎武等猛烈抨擊。陳第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顧炎武說:
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辭賦日繁,而后名之韻。至宋周颙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于古,至東京益甚。(《音學五音序》)
這是一段很經(jīng)典的論述,現(xiàn)代學者不能不讀,不能不知!顧炎武將漢語古音的時限及其流變表述得非常清楚,無需再作闡釋。
傳統(tǒng)古音學最經(jīng)典的理論可表述為:語音是發(fā)展變化的,在變化過程中會形成歷史的層次和方言地域的差別。我們可以概括為“語音變化時地說”。本來,研究漢語語音史必須樹立語音變化發(fā)展觀,這是一個基本的素養(yǎng)。以靜止的眼光看待漢語與藏語5 000年的歷史變化,認識觀念的偏差必然要導致研究結論的錯誤。
第二,關于原始漢語語音的求證。鄭張先生一方面說,以“原始漢藏語形式來修改上古漢語形式”,一方面又說:“甲骨文以前的漢語雖沒有文獻可據(jù),但可用上古音結合漢藏各語言同源詞比較來重建其原始形式,這樣所得的擬音可稱‘原始漢語’或‘遠古期漢語’。”[20]33但問題是,一個人不能同時跨進兩條河流。第一,原始漢藏語形式是什么,你必須先研究清楚;第二,你必須先完成上古音研究,爾后才能夠“結合漢藏各語言同源詞比較”加以推導。即使你已經(jīng)把上古音構擬出來了,還要看你論證過程中的邏輯程序、音系構擬是否合理。因為你的上古音系構擬的基礎是親屬語言的比較,然后你又用這種比較的結果再進行“結合”,推導出原始漢語,這種循環(huán)往復的論證過程,本身就邏輯程序混亂,且于情理不通。更何況“漢藏語系”是個不確定的假說,其同源關系詞比率有多少,迄今為止,始終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事情,如此,“漢藏各語言同源詞”,就成為一個虛擬的語言符號了。
根據(jù)歷史比較法的理論,親屬語言的比較,只能反映彼此之間的語音聯(lián)系和區(qū)別特征,但是要重建原始語言的語音系統(tǒng)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什么?因為語音詞匯是變化發(fā)展的,今天親屬語言的某個詞語不可能就是5 000年前的“原始漢藏語”。
根據(jù)歷史比較法則:假設某些詞語是漢藏語的同源詞,我們就必須設法證明并且“能合理解釋漢語與藏緬語從原始漢藏語演變的過程”;可惜,“這樣的基本認識,似乎在一些著作中全然缺乏。”[22]3
[1]梅祖麟.漢藏語的“歲、越”、“還(旋)、圜”及其相關問題[M]//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387-388.
[2]吳安其.關于歷史語言學的幾個問題[J].民族語文,1998(4):10-19.
[3]雅洪托夫.語言年代學和漢藏語系[M]//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4]翦伯贊.中外歷史年表[M].北京:中華書局,1961.
[5]包擬古.原始漢語與漢藏語[M].潘悟云,馮 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6]孫宏開,江 荻.漢藏語言系屬之爭及其源流[J].當代語言學,1999(2):17-32.
[7]王士元.漢語的祖先[M].李葆嘉,主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
[8]沙加爾.關于漢語祖先的若干評論[M]//[美]王士元.漢語的祖先.李葆嘉,主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
[9]蒲立本.漢語的歷史和史前關系[M]//[美]王士元.漢語的祖先.李葆嘉,主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
[10]斯塔羅斯金.上古漢詞匯:歷史的透視[M]//[美]王士元.漢語的祖先.李葆嘉,主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
[11]白一平.親緣性強于偶然性:古漢語與藏緬語的概率比較[M]//[美]王士元.漢語的祖先.李葆嘉,主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
[12]黃布凡.羌語支[M]//漢藏語概論: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13]藏緬語編寫組.藏緬語語音和詞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14]倪大白.壯侗語篇[M]//漢藏語概論: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15]徐通鏘,葉蜚聲.內部擬測方法和漢語上古音系的研究[J].語文研究,1981(1):65 -82.
[16]鄭張尚芳.漢語與親屬語同源根詞及附綴成分比較上的擇對問題[M]//[美]王士元.漢語的祖先.李葆嘉,主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
[17]潘悟云.對華澳語系假說的若干支持材料[M]//[美]王士元.漢語的祖先.李葆嘉,主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
[18]黃布凡.古藏語動詞的形態(tài)[J].民族語文,1981(3):1-13.
[19]潘悟云.漢語歷史音韻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0]鄭張尚芳.上古音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1]梅 耶.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M].岑麒祥,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
[22]龔煌城.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自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 郭慶華)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Hypothesis and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Proto-Languages:A Critical Review of Genea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 and Its Research Methodology
ZHANG Min-quan
(School of Literature,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24,China)
The so-called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is just a unverified hypothesis,with its historical scope and the gene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remaining a controversy and with no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is area universally accepted by scholars in the linguistic community so far.The hypothesis,therefore,has yet to be prov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In this process,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of utmost importance.We can not identify the basic vocabulary,choose cognate words and reconstruct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merely out of our imagination.This paper i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hypothesis and its research methodology.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hypothesis;genealogical relationship;time-and-space differences;research methodology
H01
A
1000-5935(2012)05-0010-08
2012-06-18
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萬光泰音韻學稿本與漢語上古音研究”(10BYY048)
張民權(1957-),男,江西南昌人,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