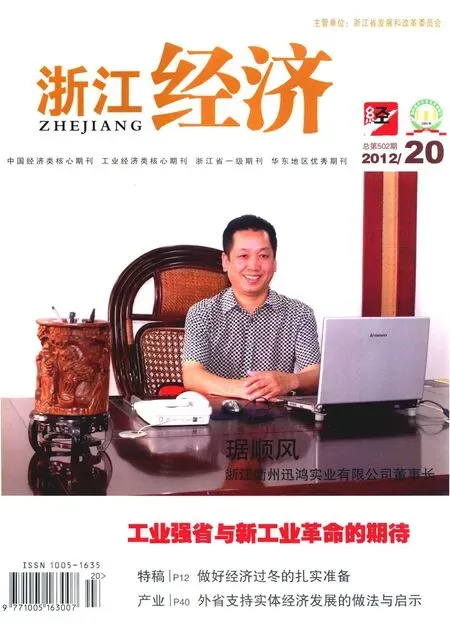打開農民工市民化通道
□ 文/柳博雋
農民工的戶籍由農村遷入城市,把那些依附在戶籍上的“資源”特別是土地帶入城市,符合發展的歷史邏輯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民工問題,制定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農民工的就業和生活環境,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也無可否認,農民工的“邊緣化”現象仍無實質性地改善——他們依然“候鳥”般地遷徙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未能有機融入城市的經濟、政治、文化體系。
究其原因,與農民工市民化通道的普遍缺失有關。盡管很多城市都有“購房落戶”、“人才引進”等政策,有些城市還推出“積分落戶”的辦法,但對農民工而言,這些市民化通道的“門檻”顯然過高。僅憑目前的收入和人力資本積累,大多數農民工是很難跨越的。毋庸置疑,農民工市民化需要“另辟蹊徑”。
眾所周知,農民工市民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轉變農民工的戶籍身份。由于我國的戶籍制度還附加了資源分配、公共服務等多項功能,轉變戶籍身份實質上是一種利益關系的調整。農民工的戶籍在農村,由此而取得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其教育、衛生、住房等資源也配置在農村。在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農民工的戶籍由農村遷入城市,把那些依附在戶籍上的“資源”特別是土地帶入城市,也符合發展的歷史邏輯。

對農民工而言,如果能將附在戶籍上的“資源”,隨著戶籍遷移而帶入城市,那么農民工在城市安居樂業就有了一定基礎,所創造的財富也就不會再繼續“沉淀”在農村。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實物形態的土地不可移動,可以將相應的土地指標帶入城市,采取以土地指標換城鎮戶籍、住房和社會保障的方式,享受城鎮居民的各種生活待遇,主要包括子女入學、就業扶持、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待遇和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住房保障,平等參與當地的民主政治建設,實現與城鎮居民“同城同待遇”,從而真正完成農民工的市民化。
對城市而言,吸納農民工進城需要擴大相應的發展空間,需要進行城市擴張所引發的功能設施、社會設施以及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解決農民工的基本權利保障、公共服務供給、社會經濟適應、城市生活融入等問題。如果農民工能帶著“資源”進城,特別是在實行“兩個最嚴格”土地政策的背景下,能夠帶著土地指標進城,那么城市在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投入壓力將明顯減輕。更重要的是,早已“捉襟見肘”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隨著農民工相應土地指標的輸入,也將大為緩解。
從歷史上看,建國以來農村居民向城鎮居民的身份轉換,無論是招工還是大學錄取進城,只要“農轉非”為城鎮居民,都必須將土地交給國家或集體經濟組織。近幾年城市近郊農民的市民化,也是以土地換取城鎮居民的戶籍、住房和社會保障的方式,來完成向城鎮居民的身份轉化。這是因為我國的制度安排,就是農村居民擁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城鎮居民享有住房保障等福利政策。由于土地具有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在福利保障方面的差距。如要轉變戶籍身份,用土地換取福利保障也在情理之中。
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世界各國工業化、城市化的普遍趨勢,也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2011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已達到51.3%,這其中就包括在城鎮居住半年以上的大量農民工。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總量大約有2.5億人,并呈現出農民工就業穩定性逐步提高、舉家外出務工數量快速增長等特征。將在城鎮具有穩定工作和住所的農民工轉化為城鎮居民,已成為我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的“當務之急”。為此,要順應工業化、城市化的客觀規律,在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有序轉移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建立土地指標置換、公共服務流轉、投入成本分擔等機制,打開農民工市民化的通道,從而實現從農民工到市民的“驚險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