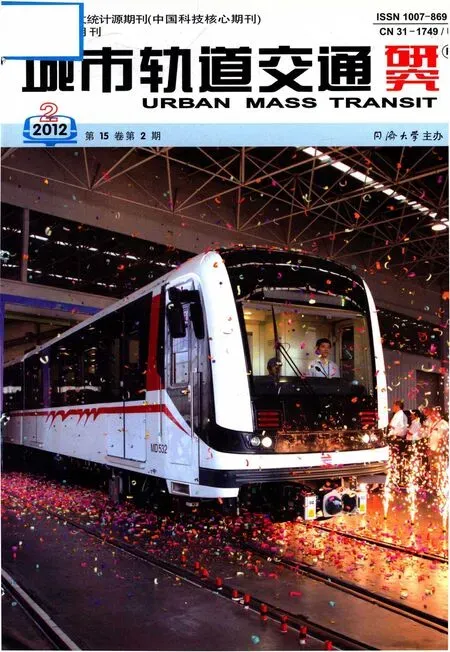苛求軟件可靠性方法、技術(shù)與模型研究
武延華 薛小平 王小平
(同濟(jì)大學(xué)電子與信息工程學(xué)院,201804,上海∥第一作者,碩士研究生)
近年來,軟件越來越多被應(yīng)用在安全苛求(Safety-Critical)、任務(wù)苛求(Mission-Critical)等領(lǐng)域,如航空航天、軌道交通、核工業(yè)等。但苛求系統(tǒng)需求增長(zhǎng)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構(gòu)建和維護(hù)這類系統(tǒng)的能力發(fā)展,因軟件失效造成關(guān)鍵任務(wù)失敗和生命財(cái)產(chǎn)損失的案例屢有報(bào)道[1-3],軟件可靠性受到了廣泛關(guān)注。軟件可靠性定義為系統(tǒng)在給定時(shí)間和條件下完成其規(guī)定任務(wù)的能力,當(dāng)系統(tǒng)正常工作時(shí)(即可靠時(shí))是安全的,即可靠性蘊(yùn)含安全性。為描述方便,本文中提及可靠性時(shí),同時(shí)也包含了安全性。
軟件開發(fā)活動(dòng)極其復(fù)雜,在整個(gè)生命周期中把握軟件可靠性本質(zhì)更為困難。受包括項(xiàng)目預(yù)算、開發(fā)周期、團(tuán)隊(duì)管理水平、程序員能力經(jīng)驗(yàn)、商業(yè)軟件模塊、軟件運(yùn)行環(huán)境等在內(nèi)的多種因素影響,容易在不經(jīng)意的情況下引入錯(cuò)誤。
目前,保障軟件可靠性的方法很多,如N版本編程、恢復(fù)塊以及形式化方法等在軟件開發(fā)不同階段較為有效地保證了可靠性。本文試圖從瀑布式開發(fā)模型的角度,討論苛求系統(tǒng)中的軟件可靠性方法、技術(shù)和模型,包括需求形式化建模、多版本軟件容錯(cuò)、函數(shù)式程序設(shè)計(jì)及可靠度評(píng)估模型。
需求形式化建模雖然可有效提高軟件規(guī)格的質(zhì)量,但非形式化描述與形式化模型間的語義一致性及對(duì)其驗(yàn)證的可行性、可信性等仍是難題。因語義扭曲導(dǎo)致的規(guī)格錯(cuò)誤可能會(huì)帶來系統(tǒng)失效風(fēng)險(xiǎn);多版本軟件容錯(cuò)試圖屏蔽設(shè)計(jì)錯(cuò)誤,卻對(duì)由規(guī)格錯(cuò)誤等原因?qū)е碌南到y(tǒng)共因失效(Common-Cause Failure,簡(jiǎn)為CCF)無能為力;函數(shù)式程序設(shè)計(jì)作為輕量級(jí)形式化實(shí)現(xiàn)技術(shù),在編寫可靠代碼方面有諸多特征和優(yōu)勢(shì),但并未受到軟件界的廣泛重視;可靠度評(píng)估模型雖然無法直接改善軟件可靠性,但定量評(píng)估軟件可靠度卻能為可靠性改善提供依據(jù)和指導(dǎo)。
1 需求與規(guī)格形式化方法
目前,苛求系統(tǒng)開發(fā)通常采用形式化方法,即通過數(shù)學(xué)方法對(duì)軟件生命周期中各個(gè)階段的活動(dòng)客體進(jìn)行建模,分析并驗(yàn)證其隱含性質(zhì),并在開發(fā)過程中采用V&V(驗(yàn)證與確認(rèn))方法達(dá)到安全和可靠的目的。文獻(xiàn)[4]指出,廣義的形式化方法可跨越軟件工程的整個(gè)生命周期,各個(gè)階段擁有其獨(dú)特的形式化方法。但狹義上的形式化方法大多特指需求階段的各種規(guī)格說明語言(例如Z,VDM(維也納開發(fā)方法),Alloy等)和并發(fā)建模框架(例如CSP(通信順序進(jìn)程)、CCS(通信系統(tǒng)演示)等進(jìn)程代數(shù))。
需求是軟件開發(fā)活動(dòng)的基礎(chǔ),需求規(guī)格錯(cuò)誤對(duì)可靠性的影響貫穿了整個(gè)軟件生命周期。文獻(xiàn)[5]對(duì)系統(tǒng)集成和測(cè)試階段發(fā)現(xiàn)的387個(gè)軟件錯(cuò)誤進(jìn)行研究后指出,與安全相關(guān)的大多數(shù)軟件錯(cuò)誤都出自不完整的需求規(guī)格或是對(duì)其的誤解,而文獻(xiàn)[6]指出傳統(tǒng)技術(shù)不足以捕捉許多需求錯(cuò)誤。
需求階段本身由多個(gè)活動(dòng)組成,例如需求獲取、需求分析、需求演化等。該階段的形式化方法也有多種。需求工程的形式化也稱早期需求的形式化,可解決需求過程中的二義性、不一致性、不完整性等,主要針對(duì)極易變動(dòng)的不穩(wěn)定需求進(jìn)行建模和驗(yàn)證。形式化規(guī)格則是等需求穩(wěn)定后,作為整個(gè)需求階段完成后的產(chǎn)出文檔。早期建模和驗(yàn)證活動(dòng)具有很多優(yōu)勢(shì),如盡早排除需求中的錯(cuò)誤可進(jìn)一步指導(dǎo)完善規(guī)格并減少完整模型建立、驗(yàn)證、演化和維護(hù)的成本,而作為從最初非形式化需求到最終完整規(guī)格的中間過渡,早期模型為需求工程提供了更細(xì)粒度的可追蹤性等。
文獻(xiàn)[7]給出了形式化方法成功應(yīng)用于任務(wù)苛求系統(tǒng)早期需求建模的3個(gè)案例。由于采用輕量級(jí)形式化方法,這些模型并沒有完全保證目標(biāo)需求的完整性和正確性,而是通過盡可能揭示非形式化需求中的錯(cuò)誤來改善需求質(zhì)量和促進(jìn)可靠性保證等級(jí)。對(duì)早期需求建模,考慮到需求本身的粗略性和易變性,這種決策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文獻(xiàn)[7]對(duì)3個(gè)案例分別采用了標(biāo)注(Annotated)流程圖、與或表(AND/OR table)和目標(biāo)建模技術(shù)(OMT)作為初始需求描述到需求模型轉(zhuǎn)換過程的中間結(jié)構(gòu)化表示,用以澄清二義性、深化對(duì)需求結(jié)構(gòu)的理解,進(jìn)一步確定采用何種合適的建模表示法,并給出了使用方法。此外,中間結(jié)構(gòu)化表示同樣為早期需求建模活動(dòng)提供了更明晰的可追蹤性,保持模型與非形式化需求間緊密的同步一致性。
從需求的非形式化描述,到半形式化表示,再到形式化模型,這個(gè)過程通常采用轉(zhuǎn)換的方法。而轉(zhuǎn)換過程通常由人手動(dòng)完成,同一份需求的不同語法形式要保持其內(nèi)容之間的語義一致性十分困難。目前主流形式化框架中的B方法和SCADE(安全苛求應(yīng)用開發(fā))環(huán)境提供了完善的工具支持建模、設(shè)計(jì)、實(shí)現(xiàn)、驗(yàn)證一體化的廣譜式(Entire Spectrum)開發(fā)方法[8],即從形式化規(guī)格開始,通過程序精化演算,將抽象模型逐步轉(zhuǎn)換為具體模型,最終生成可編譯執(zhí)行的程序語言代碼。每一步轉(zhuǎn)換都必須進(jìn)行模型驗(yàn)證和精化驗(yàn)證來保持語義,規(guī)格的形式化保證了該工作的可行性。然而,對(duì)需求模型進(jìn)行類似轉(zhuǎn)換和驗(yàn)證的難度在于,需求總是從非形式化描述開始的,若要求將其自動(dòng)轉(zhuǎn)換為形式化模型并進(jìn)行驗(yàn)證,會(huì)涉及自然語言處理,且依賴于特定應(yīng)用領(lǐng)域。
文獻(xiàn)[9-11]基于這種思想,提出基于模板(Template)和模式(Pattern)的方法,將針對(duì)特定應(yīng)用領(lǐng)域模型的公共特征(Property)分段和分句成固定格式的半自然語言描述。需求分析師提取領(lǐng)域問題中的參數(shù)并應(yīng)用到模板中就能得到需求規(guī)格實(shí)例,再利用集成自然語言處理的輕量級(jí)形式化方法及其支持工具[12]對(duì)這些規(guī)格實(shí)例進(jìn)行早期分析和驗(yàn)證。從本質(zhì)上看,需求分析對(duì)用戶需求最初總是采用非形式化的表述,非形式化需求和形式化規(guī)格間的語義一致性保證問題仍然需要進(jìn)一步研究。
2 多版本軟件容錯(cuò)
基于B方法或者SCADE環(huán)境的苛求系統(tǒng)項(xiàng)目,設(shè)計(jì)僅僅作為規(guī)格到實(shí)際代碼的中間過渡階段,需求、設(shè)計(jì)和實(shí)現(xiàn)之間的區(qū)分變得模糊,基于嚴(yán)格數(shù)學(xué)定義的模型精化及每一步轉(zhuǎn)換完成的證明責(zé)任(Proof Obligation)確保不會(huì)引入設(shè)計(jì)錯(cuò)誤。但若采用了工具支持薄弱的Z表示法(Notation)或提倡輕量級(jí)形式化的Alloy表示法等建立規(guī)格,設(shè)計(jì)與實(shí)現(xiàn)活動(dòng)仍需開發(fā)人員介入完成,容易造成規(guī)格與設(shè)計(jì)間的語義分歧,即導(dǎo)致設(shè)計(jì)錯(cuò)誤。
多版本軟件容錯(cuò)可不完全處理系統(tǒng)中的設(shè)計(jì)錯(cuò)誤,能保證軟件中某些失效不至于引起整個(gè)系統(tǒng)失效。如果說形式化方法通過確定地排除軟件錯(cuò)誤而保證可靠性,多版本軟件容錯(cuò)就是一種不確定的、概率化的錯(cuò)誤屏蔽方法。作為傳統(tǒng)的軟件可靠性提高手段,20世紀(jì)70年代研究人員就提出的N版本編程(N-version Programming,簡(jiǎn)為 NVP)[13]和恢復(fù)塊(Recovery Block,簡(jiǎn)為 RB)[14]成為軟件可靠性開發(fā)模式的典型代表。
NVP根據(jù)同一份需求構(gòu)建多份設(shè)計(jì)差異化(Design Diversity)的軟件版本,順序或并發(fā)運(yùn)行,對(duì)各版本輸出采取某種表決算法選出最優(yōu)解。設(shè)計(jì)差異化可降低各版本間因相同設(shè)計(jì)錯(cuò)誤而導(dǎo)致共因失效(CCF)的可能性,即系統(tǒng)不可檢錯(cuò)率。假設(shè)各軟件版本失效相對(duì)獨(dú)立,可靠度為Rm1,Rm2,…,Rmn,表決器采用多數(shù)表決(Majority Voting)且可靠度為Rv,則系統(tǒng)可靠度

RB則將各軟件版本順序運(yùn)行,用各版本對(duì)應(yīng)的接受測(cè)試(Acceptance Tests)代替NVP中表決器的職能,選擇最先通過接受測(cè)試的輸出為最優(yōu)解。假設(shè)各軟件版本和接受測(cè)試的失效兩兩間均相對(duì)獨(dú)立,前者可靠度為Rm1,Rm2,…,RmN,后者可靠度(包括若檢測(cè)出故障則正確回滾的概率)為Rt1,Rt2,…,RtN,則系統(tǒng)可靠度

由于RB只需一份軟件版本通過測(cè)試就能得到最優(yōu)解,而NVP要求多份版本正確無誤才能表決出最優(yōu)解,因此只要接受測(cè)試設(shè)計(jì)得當(dāng),RB可獲得比NVP更高的系統(tǒng)可靠度。但RB的問題在于:接受測(cè)試是依賴于其對(duì)應(yīng)軟件版本內(nèi)部邏輯的,沒有統(tǒng)一、明確地構(gòu)造簡(jiǎn)單而高可靠接受測(cè)試的普適方法。此外,本質(zhì)上RB要求各版本嚴(yán)格順序執(zhí)行,這導(dǎo)致了潛在的巨大延時(shí)風(fēng)險(xiǎn)。意味著對(duì)實(shí)時(shí)性要求較高的應(yīng)用并不適合,需結(jié)合監(jiān)視定時(shí)器(Watchdog Timer)[15]等機(jī)制予以輔助。
研究人員嘗試通過NVP和RB的組合來進(jìn)一步提高可靠性。文獻(xiàn)[16]提出的一致性恢復(fù)塊將NVP與RB串聯(lián)起來,并復(fù)用軟件版本甚至運(yùn)算結(jié)果;文獻(xiàn)[17]提出的接受表決(Acceptance Voting)將RB中的接受測(cè)試應(yīng)用于NVP中每一版本,使每個(gè)版本輸出只有通過接受測(cè)試才能參與系統(tǒng)輸出表決。這些方法雖然使系統(tǒng)比使用純NVP或純RB達(dá)到更高的可靠度,但依然存在諸如接受測(cè)試編寫困難、潛在延時(shí)風(fēng)險(xiǎn)大的問題。
NVP和RB也可采用數(shù)據(jù)差異化[18]實(shí)現(xiàn)某些變種(Variant)。其核心思想是尋求一種或多種數(shù)據(jù)重表達(dá)(Re-expression)算法,將系統(tǒng)輸入轉(zhuǎn)換成語義相同的不同形式,提交給各路冗余軟件。采取數(shù)據(jù)差異化形式的NVP變種稱為N副本(NCopy),其RB變種稱為重試塊(Retry Block)。數(shù)據(jù)差異化存在的問題與RB類似,即數(shù)據(jù)重表達(dá)嚴(yán)重依賴于應(yīng)用領(lǐng)域,即便為某一特定應(yīng)用尋求完備、可靠的重表達(dá)算法也是相當(dāng)困難的。
設(shè)計(jì)差異化和數(shù)據(jù)差異化均無法消除CCF,如需求中遺留的錯(cuò)誤、設(shè)計(jì)人員做出的相同錯(cuò)誤決策、程序員錯(cuò)誤實(shí)現(xiàn)同一個(gè)算法等,都會(huì)為不同軟件版本埋下通向相同失效模式路徑的隱患。因此,CCF的存在使預(yù)測(cè)系統(tǒng)可靠度變得困難,而僅能在測(cè)試和運(yùn)行階段采用CCF模型或軟件可靠性增長(zhǎng)模型(Software Reliability Growth Model,簡(jiǎn)為SRGM)對(duì)其進(jìn)行評(píng)估(Estimation)。但在此之前,通過刪除和避免程序中的實(shí)現(xiàn)錯(cuò)誤來改善軟件代碼質(zhì)量,又對(duì)系統(tǒng)可靠性的改善做出一定貢獻(xiàn)。
3 函數(shù)式程序設(shè)計(jì)
函數(shù)式程序設(shè)計(jì)(Functional Programming,簡(jiǎn)為FP)是一種聲明式編程泛型,與軟件形式化方法協(xié)同發(fā)展起來,兩者共享絕大部分?jǐn)?shù)學(xué)基礎(chǔ),尤其是FP的理論根基(λ演算)來自于形式化方法中基于演算的方法。大多數(shù)自動(dòng)定理證明器或輔助證明系統(tǒng)都采用FP語言編寫,例如Coq、LCF(可計(jì)算數(shù)邏輯)、HOL(高階邏輯)、Isabelle等。FP把“軟件系統(tǒng)即求值器”的本質(zhì)在語法層面體現(xiàn)出來,每個(gè)函數(shù)作為最小模塊單元,具有優(yōu)良的數(shù)學(xué)性質(zhì),即在任何時(shí)候?qū)ν瑯虞斎攵籍a(chǎn)生同樣輸出,沒有副作用。這種引用透明性既避免了命令式語言中常見的編碼錯(cuò)誤,又使得代碼驗(yàn)證近似于數(shù)學(xué)函數(shù)驗(yàn)證,無需繁復(fù)冗長(zhǎng)的證明規(guī)則指導(dǎo)。
文獻(xiàn)[19]闡述了FP的重要性,認(rèn)為FP優(yōu)勢(shì)的本質(zhì)在于提供了新的模塊化能力:高階函數(shù)將所執(zhí)行操作從具有共性的應(yīng)用模式中抽象出來,惰性求值則將某些迭代計(jì)算分離為生成器和篩選器兩個(gè)獨(dú)立模塊的組合。模塊化的軟件系統(tǒng)突顯了代碼本身及對(duì)代碼驗(yàn)證工作的重用性,使程序更易于理解、編寫、測(cè)試和維護(hù),對(duì)其可靠性的改善顯而易見。
3.1 FP應(yīng)用案例
愛爾蘭都柏林城市大學(xué)軟件工程中心主導(dǎo)開發(fā)的SADLI(診斷實(shí)驗(yàn)室圖象安全保證)項(xiàng)目[20]通過在安全苛求方法學(xué)指導(dǎo)下采用FP實(shí)現(xiàn)診斷顯微鏡中的成像系統(tǒng),以確定這種開發(fā)方法在該領(lǐng)域中的優(yōu)勢(shì)和限制,其中探索了與FP相關(guān)的兩個(gè)方面:一是采用FP語言開發(fā)復(fù)雜軟件系統(tǒng)的可能性;二是安全苛求軟件開發(fā)過程中FP語言與傳統(tǒng)安全苛求方法學(xué)中最佳實(shí)踐準(zhǔn)則之間的協(xié)調(diào)一致性。
研究結(jié)果表明,雖然開發(fā)該系統(tǒng)需要考慮的實(shí)踐問題很多,包括用戶交互、硬件控制、圖像處理、圖像顯示、統(tǒng)計(jì)模式識(shí)別及與現(xiàn)有軟件的接口,F(xiàn)P依然能順利實(shí)現(xiàn)該系統(tǒng)運(yùn)行。這表明采用FP作為關(guān)鍵技術(shù)來實(shí)現(xiàn)具有相當(dāng)規(guī)模的復(fù)雜系統(tǒng)是切實(shí)可行的。圖1展示了SADLI的生命周期。

圖1 SADLI的生命周期
從圖1中可見該系統(tǒng)規(guī)格也采用了純FP語言Haskell(Gofer為早期Haskell解釋器)來描述(文獻(xiàn)[21]討論了該做法的可行性),將快速原型開發(fā)和形式化方法結(jié)合起來(從而使得對(duì)設(shè)計(jì)和實(shí)現(xiàn)兩者都能進(jìn)行形式化驗(yàn)證),又使設(shè)計(jì)到實(shí)現(xiàn)的轉(zhuǎn)換在同一種泛型內(nèi)進(jìn)行,從兩方面將轉(zhuǎn)換中可能引入的錯(cuò)誤最少化。項(xiàng)目人員將SADLI基于IEC 61508標(biāo)準(zhǔn)[22]的早期版本進(jìn)行開發(fā),這就證實(shí)了FP與安全苛求系統(tǒng)開發(fā)標(biāo)準(zhǔn)間的協(xié)調(diào)一致性。
3.2 領(lǐng)域?qū)S茫―omain Specific)FP語言
除了通用FP語言在苛求系統(tǒng)中的工業(yè)實(shí)踐外,研究人員更嘗試為苛求系統(tǒng)設(shè)計(jì)領(lǐng)域?qū)S玫腇P語言。LUSTRE[23]是一種專為實(shí)現(xiàn)反應(yīng)式系統(tǒng)或進(jìn)行硬件描述的同步數(shù)據(jù)流語言,兼并FP模型和并行模型,程序形式化與時(shí)態(tài)邏輯相似,使該語言既能編寫代碼又能表達(dá)和驗(yàn)證時(shí)間屬性。LUSTRE作為法國Esterel公司安全苛求系統(tǒng)開發(fā)環(huán)境SCADE的核心語言,在工業(yè)界應(yīng)用已有20年[24],包括航空航天、軌道交通等領(lǐng)域的控制系統(tǒng)。
Hume[25]是一門較新的應(yīng)用于安全苛求系統(tǒng)的FP語言,其設(shè)計(jì)者指出圖靈完備語言的程序等價(jià)性(Equivalence)、終止性(Termination)及時(shí)間空間使用情況這些嚴(yán)格屬性都是不可判定的,而能判定這些屬性的語言(如有限狀態(tài)機(jī))缺乏足夠強(qiáng)的表達(dá)能力。因此Hume的目標(biāo)是既能提供高層的抽象能力和表達(dá)能力,又能保證程序執(zhí)行時(shí)間和空間消耗這類動(dòng)態(tài)行為屬性。這其實(shí)反映了安全苛求系統(tǒng)將強(qiáng)制(Strong)的正確性要求和嚴(yán)格(Strict)的性能要求整合的意圖,而又使語言維持在高層次抽象。
來自Ericsson公司的Erlang語言[26]是一種現(xiàn)在廣泛應(yīng)用于電信領(lǐng)域的并發(fā)函數(shù)式語言。作為基礎(chǔ)設(shè)施,通信系統(tǒng)需要高可靠地完成所請(qǐng)求任務(wù),即它們是任務(wù)苛求系統(tǒng)。此外,任何建設(shè)于這些系統(tǒng)之上的安全苛求系統(tǒng),也使前者帶上了安全苛求的屬性。Erlang作為一種面向并發(fā)的分布式容錯(cuò)語言,最適合處理通信系統(tǒng)的動(dòng)態(tài)性、并發(fā)性和實(shí)時(shí)性,開發(fā)出高可靠的分布式并發(fā)系統(tǒng)。
3.3 FP中的軟件容錯(cuò)
多版本軟件容錯(cuò)與語言無關(guān),可用FP語言部署NVP和RB。此外,根據(jù)純FP語言引用透明性易于并行計(jì)算的特點(diǎn),文獻(xiàn)[27]又提出了一種基于并行圖歸約的FP程序容錯(cuò)方法。在惰性求值的純FP程序中,作為表達(dá)式的整個(gè)程序可看作一個(gè)圖,求值過程意味著對(duì)該圖做歸約。并行體系中各節(jié)點(diǎn)接受該圖的子圖作為計(jì)算任務(wù),并對(duì)其它節(jié)點(diǎn)的子圖進(jìn)行備份。一旦檢測(cè)到某節(jié)點(diǎn)進(jìn)程出錯(cuò),則請(qǐng)求有其備份子圖的其它節(jié)點(diǎn)傳回該子圖,并通過檢查點(diǎn)和消息日志(Message Logging)等機(jī)制將出錯(cuò)節(jié)點(diǎn)回卷到初始狀態(tài)后重新歸約。由于引用透明性形成各子圖相互獨(dú)立,因此,可按任意順序歸約,這就賦予整個(gè)恢復(fù)過程最少限制和最大自由度。
4 可靠度評(píng)估模型
需求、設(shè)計(jì)和實(shí)現(xiàn)階段的任何可靠性方法和技術(shù)雖然提高了軟件質(zhì)量,卻無法完全屏蔽或消除軟件錯(cuò)誤,且沒有提供定量分析并以此為依據(jù)持續(xù)改進(jìn)可靠性。另一方面,通常并不要求苛求系統(tǒng)完全可靠,而是允許其具有既定閾值下的可接受失效率。軟件可靠度評(píng)估模型正是實(shí)現(xiàn)對(duì)系統(tǒng)可靠度進(jìn)行定量估計(jì)的一種統(tǒng)計(jì)方法。
4.1 CCF建模
在NVP和RB中,若假設(shè)各軟件版本失效相互獨(dú)立,則系統(tǒng)可靠度Rsys是組成系統(tǒng)各組件可靠度R1,R2,…,Rn的函數(shù),即 Rsys=f(R1,R2,…,Rn),如式(1)、(2)所示。這意味著在系統(tǒng)被真正構(gòu)建出來之前就可預(yù)測(cè)其可靠度。差異化嘗試使該獨(dú)立性假設(shè)趨于合理,然而Knight等人進(jìn)行的27版本實(shí)驗(yàn)[28]及對(duì)其進(jìn)行的故障分析卻揭示了復(fù)雜軟件開發(fā)過程總會(huì)不經(jīng)意引入相關(guān)故障的事實(shí),使差異化軟件系統(tǒng)仍會(huì)產(chǎn)生CCF。
4.1.1 CCF模型
CCF模型針對(duì)采用了容錯(cuò)技術(shù)的軟件結(jié)構(gòu),考察組合軟件組件后引入的系統(tǒng)失效新質(zhì)。最流行的CCF模型是1975年Fleming提出的β因子模型[29],僅用單個(gè)參數(shù)β描述冗余組件間的失效耦合。通常只能等系統(tǒng)真正構(gòu)建出來后通過測(cè)試和運(yùn)行并記錄歷史數(shù)據(jù)來估計(jì)CCF模型中的參數(shù),然而β因子模型的簡(jiǎn)單性及其工程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使得針對(duì)特定應(yīng)用就能直接確定β值。例如Humphrey方法[30]、部分 (partial)β 因子法[31]和IEC 61508 標(biāo)準(zhǔn)[22]中β因子模型的查表(checklist)法等。
文獻(xiàn)[32]對(duì)其它CCF模型的現(xiàn)狀和趨勢(shì)進(jìn)行了總結(jié),包括Fleming對(duì)β因子模型擴(kuò)展后提出的多希臘字母(Multiple Greek Letters,簡(jiǎn)為MGL)模型、Mosleh和Siu提出的α因子模型、Vesely提出的二項(xiàng)失效率(Binomial Failure Rate,簡(jiǎn)為BFR)模型等。
(1)MGL模型克服了β因子模型假設(shè)CCF為全部組件失效的局限,加入更多參數(shù)以表征不同數(shù)量組件失效間相關(guān)性的條件概率。
(2)α因子模型根據(jù)由共同原因造成k路組件失效率與系統(tǒng)失效率之間的比值αk為參數(shù)計(jì)算不同形式CCF的概率。
(3)BFR模型將系統(tǒng)組件失效分為獨(dú)立失效和由沖擊引起的任意數(shù)量組件失效。其中沖擊的發(fā)生滿足齊次泊松分布,且當(dāng)沖擊發(fā)生時(shí)每個(gè)組件以概率p失效,則因沖擊導(dǎo)致的失效組件數(shù)滿足二項(xiàng)分布B(n,p)。
國內(nèi)學(xué)者對(duì)CCF模型也進(jìn)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文獻(xiàn)[33]研究了應(yīng)用貝葉斯網(wǎng)絡(luò)建立CCF系統(tǒng)可靠性模型的方法,將系統(tǒng)中的共因元件分離為具有串聯(lián)關(guān)系的獨(dú)立失效子元件(失效率K1)和共因失效子元件(失效率K2),再分析它們與其它非共因元件的相應(yīng)關(guān)系(如串聯(lián)、并聯(lián)等),并對(duì)典型系統(tǒng)進(jìn)行了可靠性分析。文獻(xiàn)[34]提出的CCF新模型對(duì)假設(shè)失效相互獨(dú)立時(shí)所得的系統(tǒng)可靠度表達(dá)式進(jìn)行變換,加入表征CCF的影響因子,從而將可靠性預(yù)測(cè)與評(píng)估聯(lián)系起來,能更全面地計(jì)算系統(tǒng)元件之間的相關(guān)性,彌補(bǔ)了傳統(tǒng)CCF模型的信息遺漏問題,避免了傳統(tǒng)CCF模型所面臨的組合爆炸問題。
4.1.2 差異化模型
CCF模型并沒有解釋失效間相關(guān)性的產(chǎn)生原因,對(duì)差異化系統(tǒng)的分析造成困難。例如β因子模型假設(shè)各路組件完全相同,這對(duì)差異化系統(tǒng)顯然無法成立。對(duì)于差異化系統(tǒng)的CCF分析,一種方法是采用傳統(tǒng)CCF模型,在考慮差異化的背景下重新定義和解釋其參數(shù),例如把β定義為各軟件版本失效率的幾何平均[32]。另一種方法是采用差異化模型[35]來解釋失效相關(guān)性,包括 Eckhardt-Lee(EL)模型[36]、Littlewood-Miller(LM)模型[37]等。
EL模型認(rèn)為軟件的運(yùn)行環(huán)境實(shí)際是其執(zhí)行時(shí)的輸入,即任何影響軟件行為的狀態(tài)變量。對(duì)所有可能開發(fā)出的軟件版本及其輸入x,難度函數(shù)(Difficulty Function)θ(x)表示在該輸入下軟件失效的概率。若θ(x)越大,則表明輸入x的難度越大,多個(gè)軟件版本在該輸入下都失效的概率也越大,導(dǎo)致失效正相關(guān)性。
在EL模型中,設(shè)計(jì)差異化僅僅是選擇不同開發(fā)團(tuán)隊(duì)隨機(jī)達(dá)到的,即仍然可能存在相同設(shè)計(jì)。而LM模型是EL模型的推廣,對(duì)不同版本間的設(shè)計(jì)差異進(jìn)行強(qiáng)制(Force),包括選擇不同的開發(fā)過程、程序設(shè)計(jì)語言、測(cè)試方法等。例如,對(duì)版本A和B強(qiáng)制不同的設(shè)計(jì)方法學(xué),使得當(dāng)版本A失效概率越大時(shí),版本B失效概率越小,形成失效負(fù)相關(guān)性。
4.2 軟件可靠性增長(zhǎng)模型(SRGM)
大多數(shù)可靠度評(píng)估模型都屬于SRGM,通過對(duì)軟件測(cè)試和運(yùn)行階段收集到的失效數(shù)據(jù)應(yīng)用統(tǒng)計(jì)推理來估計(jì)軟件從時(shí)間維度上的可靠度演化曲線。其目的是預(yù)測(cè)為達(dá)到指定可靠度目標(biāo)所需的額外測(cè)試時(shí)間,或是預(yù)測(cè)當(dāng)測(cè)試結(jié)束時(shí)軟件的可靠度[38]。
現(xiàn)有的SRGM已有數(shù)百種,適用于不同的開發(fā)過程和假設(shè),不少文獻(xiàn)對(duì)已發(fā)表SRGM進(jìn)行了總結(jié)[39-40]。文獻(xiàn)[41]在此基礎(chǔ)上系統(tǒng)地分析了軟件可靠性建模方法的最新研究進(jìn)展,包括分別與混沌理論、未確知理論和機(jī)器學(xué)習(xí)相結(jié)合的研究方向。
文獻(xiàn)[42]指出尚不存在某個(gè)普適的SRGM能對(duì)所有情形下的軟件可靠度給出準(zhǔn)確評(píng)估,也沒有先驗(yàn)知識(shí)(Priori)能判定在某特定上下文中哪個(gè)模型是最優(yōu)的。于是文獻(xiàn)[43]提出了多模型加權(quán)平均的軟件可靠性綜合模型,用貝葉斯方法通過權(quán)值的動(dòng)態(tài)調(diào)整實(shí)現(xiàn)模型的選擇與混合,找出最適合待評(píng)估軟件的模型并綜合各模型的評(píng)估結(jié)果,以犧牲模型的高精度換取其穩(wěn)健性、實(shí)用性和可靠性。
近年來隨機(jī)過程類SRGM不少研究工作嘗試抽象現(xiàn)有模型并建立統(tǒng)一的框架對(duì)其進(jìn)行考察,例如文獻(xiàn)[44]通過使用加權(quán)算術(shù)平均、幾何平均、調(diào)和平均等,提出了非齊次泊松過程模型(NHPP)的統(tǒng)一框架,現(xiàn)所有NHPP模型都可通過該框架變換而得,從此框架中也可推導(dǎo)出一些新的NHPP模型。文獻(xiàn)[45]中推廣的NHPP模型則將不完全調(diào)試(Imperfect Debugging)和除錯(cuò)效率(Fault Removal Efficiency)考慮進(jìn)來。Ledoux在文獻(xiàn)[46]中則更進(jìn)一步,使用自激勵(lì)點(diǎn)過程(Self-Exciting Point Processes)作為基本工具對(duì)失效過程進(jìn)行建模,將大部分黑盒SRGM(即隨機(jī)過程類SRGM)統(tǒng)一起來。
SRGM一般用來對(duì)單版本軟件進(jìn)行可靠性評(píng)估,但對(duì)多版本軟件也同樣適用。文獻(xiàn)[47]首先提出了針對(duì)NVP系統(tǒng)的SRGM,但沒有考慮不完全調(diào)試對(duì)獨(dú)立失效和共因失效的影響,并且過于復(fù)雜,難以應(yīng)用于N>3的多版本情形。Teng和Pham嘗試克服這些限制和困難,在為NVP建立SRGM同時(shí)考慮測(cè)試和調(diào)試階段的除錯(cuò)效率及新錯(cuò)誤引入率[48]。他們將NVP的失效分為共同失效和并發(fā)獨(dú)立失效,其中共同失效定義為由各版本功能對(duì)等模塊中的相似或相同錯(cuò)誤引起的失效,即CCF,因此可以將該NVP-SRGM看成一種動(dòng)態(tài)CCF模型。
5 結(jié)語
可靠性是衡量軟件質(zhì)量最重要的指標(biāo)之一,對(duì)苛求軟件系統(tǒng)來說可靠性甚至是項(xiàng)目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因而苛求系統(tǒng)的軟件開發(fā)模型常采用較為保守、成熟的瀑布模型及其改進(jìn)變種。本文從瀑布式模型的需求、設(shè)計(jì)、實(shí)現(xiàn)、測(cè)試和運(yùn)行等各階段來分析了苛求軟件開發(fā)過程中常用的方法、技術(shù)和模型,表1總結(jié)比較了這些方法、技術(shù)和模型所使用的開發(fā)階段、所面向的目標(biāo)錯(cuò)誤類型及各自的優(yōu)缺點(diǎn)。

表1 苛求軟件可靠性方法、技術(shù)和模型的特點(diǎn)比較
[1]Lee L.The day the phones stopped ringing[M].New York:Plume,1992.
[2]NASA.Mars climate orbiter mishap investigation board phase i report[R/OL].[1999-11-10].ftp://ftp.hq.nasa.gov/pub/pao/reports/1999/MCO-report.pdf.
[3]Dalal S R,Horgan J R,Kettenring J R.Reliable software and communication:software quality,reliability,and safety[C].//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Los Alamito: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1993:425.
[4]Woodcock J,Larsen P G,Bicarregui J,et al.Formal methods:practice and experience[J].ACM Computing Surveys,2009,41(4):19.
[5]Lutz R R.Analyzing software requirements errors in safetycritical,embedded systems[C].//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Washington: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1993:126.
[6]Kelly J C,SherifH J S,Hops J.An analysis of defect densities found during software inspections[J].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1992,17(2):111.
[7]Easterbrook S,Lutz R,Covington R,et al.Experiences using lightweight formal methods for requirements modeling[J].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1998,24(1):4.
[8]肖美華,薛錦矛.形式化方法B及其程序規(guī)約機(jī)理[J].計(jì)算機(jī)工程,2004,30(16):16.
[9]Bertrand P,Darimont R,Delor E,et al.GRAIL/KAOS:an environment for goal-driven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C].//Proceedings of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Washington: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1998:58.
[10]Dwyer M B,Avrunin G S,Corbett J C.Patterns in property specifications for finite-state verific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New York:ACM Press,1999:411.
[11]Denger C,Berry D M,Kamsties E.Higher quality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s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patterns[C].//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Science,Technology & Engineering.Washington: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2003:80.
[12]Gervasi V,Nuseibeh B.Lightweight valid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 requirements:a case study[J].Software:Practice& Experience,2002,32(2):113.
[13]Chen L,Avizienis A.N-version programming:a faulttolerance approach to reliability of software oper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ault-Tolerant Computing.[S.l.]:[s.n.],1978:3.
[14]Randell B.System structure for software fault tolerance[J].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1975,1(2):220.
[15]Hecht H.Fault-tolerant software for real-time applications[J].ACM Computing Surveys,1976,8(4):391.
[16]Scott R K,Gault J W,Mcallister D F.Fault-tolerant software reliability modeling[J].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1987,13(5):582.
[17]Brlli F,Jedrzejowicz P.Fault-tolerant programs and their reliability[J].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1990,39(2):184.
[18]Ammann P E,Knight J C.Data diversity:an approach to software fault tolerance[J].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1988,37(4):418.
[19]Hughes J.Why functional programming matters[J].The Computer Journal,1989,32(2):98.
[20]Chudleigh M,Berridge C,May R,et al.The SADLI project:safety critical software research in the medical diagnostic domain[J].Computing & Control Engineering Journal,1995,6(5):211.
[21]Butler J.Use of a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for formal specification[C].//IEE Colloquium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Formal Methods.[S.l.]:[s.n.],1995:2/1-2/3.
[22]IEC 61508, Functional safety of electrical/electronic/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afety-related systems,parts 1-7[S].
[23]Halbwachs N,Caspi P,Raymond P,et al.The synchronous data-flow programming language LUSTRE[J].Proceedings of the IEEE,1991,79(9):1305.
[24]Benveniste A,Caspi P,Edwards S A,et al.The synchronous languages 12years later[J].Proceedings of the IEEE,2003,91(1):64.
[25]Hammond K,Michaelson G. Hume:a domain-specific language for real-time embedded systems[C].//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erative Programming and Component Engineering.New York:Springer,2003:37.
[26]Armstrong J,Vipding R,Wikstr M C,et al.Concurrent programming in ERLANG[M].2nd ed.Hertfordshire:Prentice Hall PTR (UK),1996.
[27]Kitakami M,Kubota S,Ito H.Fault-tolerance of functional programs based on the parallel graph reduction[C].//Proceedings of Pacific Ri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ependable Computing.Los Alamitos: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2001:319.
[28]Brillant S S,Knight J C,Leveson N G.Analysis of faults in an n-version software experiment[J].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1990,16(2):238.
[29]Fleming K N.A reliability model for common mode failures in redundant safety systems,report GA-A13284[R].San Diego:General Atomic Company,1975.
[30]Humphreys R A.Assigning a numerical value to the beta factor common cause evalu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Reliability Conference.[S.l.]:[s.n.],1987:2C/5/1–2C/5/8.
[31]Johnston B D.A structured procedure for dependent failure analysis (DFA)[J].Reliability Engineering,1987,19(2):125.
[32]Hokstad P,Rausand M.Common cause failure modeling:status and trends[M].New York:Springer,2008:621.
[33]尹曉偉,錢文學(xué),謝里陽.基于貝葉斯網(wǎng)絡(luò)的系統(tǒng)可靠性共因失效模型[J].中國機(jī)械工程,2009,20(1):90.
[34]王學(xué)敏,謝里陽,周金宇,等.相關(guān)失效系統(tǒng)的可靠性模型[J].東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自然科學(xué)版,2004,25(9):887.
[35]Littlewood B,Popov P,Strigini L.Modeling software design diversity:a review[J].ACM Computing Surveys,2001,33(2):177.
[36]Eckhardt D E,Lee L D.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nalysis of multiversion software subject to coincident errors[J].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1985,11(12):1511.
[37]Littlewood B,Miller D R.Conceptual modelling of coincident failures in multiversion software[J].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1989,15(12):1596.
[38]Dalal S R.Software reliability models:a selective survey and new directions[M].New York:Springer,2003:201.
[39]Singpurwalla N D,Wilson S P.Software reliability modeling[J].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Review,1994,62(3):289.
[40]Gokhale S S,Marinos P N,Trivedi K S.Important milestones in software reliability modeling[C].//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S.l.]:[s.n.],1996:345.
[41]樓俊鋼,江建慧,帥春燕,等.軟件可靠性模型研究進(jìn)展[J].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2010,37(9):13.
[42]Brocklehurst S,Chan P Y,Littlewood B,et al.Recalibrating software reliability models[J].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1990,16(4):458.
[43]鄒豐忠,劉海青,王林.軟件可靠性綜合模型[J].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工學(xué)版,2003,36(1):86.
[44]Huang C Y,Lyu M R,Kuo S Y.Unified scheme of some nonhomogenous poiss on process models for software reliability estimation[J].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2003,29(3):261.
[45]Zhang X M,Teng X L,Pham H.Considering fault removal efficiency in software reliability assessment[J].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Man and Cybernetics,Part A:Systems and Humans,2003,33(1):114.
[46]Ledoux J.Software reliability modeling[M].New York:Springer,2003.
[47]Kanoun K,Kaaniche M,Beounes C,et al.Reliability growth of fault-tolerant software[J].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1993,42(2):205.
[48]Teng X L,Pham H.Software fault tolerance[M].New York:Springer,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