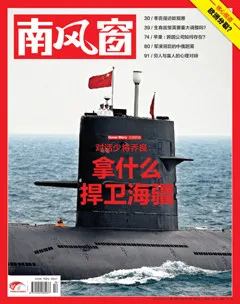共治本質是破除權力壟斷
趙義
5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其評論部對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的采訪,內容涉及社會管理創新。王榮認為,“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的時代已逐漸過去,理性改革和決策問責的時代正在到來。尤其是在社會管理上,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頭”難以摸著的問題,也有社會轉型期矛盾疊加、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現狀。深圳將加大政府改革、簡政放權的力度,把政府為主的社會管理行為轉化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共治行為。
深圳只是一個最新的例子,廣東順德幾年前就開始類似試點。在重啟改革成為當下最強音的時候,廣東的著力點日益明確放在了政府改革和簡政放權上,與之對應的就是政府與社會協同共治的新取向。尤其是在增城新塘鎮大敦村事件、潮安古巷鎮事件等發生后,廣東的主政者認識到,社會矛盾已經到了節點上,小事崩出大事,“不做一些花錢的事,掙錢的事也干不下去”,補齊社會“短板”的核心就是培育和壯大社會組織。2011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將之總結為:“廣東維穩,已從依靠政府管治轉向政府、社會共治。”
共治問題的突出,不僅僅與“維穩”有關。近些年,政府的職能進行了又一輪以社會公共服務為主體的擴張,其投入動輒以百億、千億計。政府集中財力然后履行更多公共服務職能,而基本公共服務現在一般都是由政府部門或者其下屬事業單位提供,在監督乏力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效益審計薄弱、難以問責、腐敗等難題。2012年全國“兩會”,溫家寶總理首次提到,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社區,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全文公布。126萬家、3000余萬人的事業單位群體未來將分三類進行改革:“參公”、推向市場、強化其公益屬性。第三類實際上將成為公益類社會組織。這也預示著,實現共治的參與主體將是體制內的轉身者,真正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北京市有一年計劃采購社會組織2億元的公共服務,但符合條件的民間組織寥寥。對此,政府一方面應保證體制內組織“與政府脫鉤”即“去行政化”的到位,另一方面應以更大力度促進“社會開放”,形成良性競爭。
與此同時,隨著一些社會問題的突出,政府的施政目標也日益廣泛,比如文化覺醒、信用建設、道德重建等。客觀而言,這些問題都應該重視,但僅僅依靠“有形之手”恐怕會南轅北轍,陷入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悖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社會管理變成“管理社會”,而不是社會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文化道德性目標將只能淪為虛偽的代名詞。
共治這個概念與“治理”、“善治”(good governance)等上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的理念密切相關,其針對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政府獨大”和“無法治理”兩種現象并存的矛盾。與“善治”有關的治理原則包括透明、責任、回應、參與和有效等。因此,社會共治從本質上說就是破除權力的壟斷。破除這種壟斷,意味著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即政府只是治理社會問題的一個主體,在該止步的地方必須停下來,承認自己在一些問題上的低效或者無效,讓社會發揮功能。
從長遠看,隨著政府職能主動或被動的擴張,有可能會進一步固化全能型政府,固化政府過度汲取財力和政府職能及官員偏好單兵突進的惡性循環。共治理念的扎根和繁盛,會給這個趨勢增加“剎車裝置”。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在近日關于青島植樹增綠行動中,如果不是社會輿論持續發力,預算能夠澄清,植樹出現的局部過密、占用人行道等問題能夠這么快進入有關部門的視野嗎?
尤其是在官員競爭性選舉程度不高的現實下,共治也能增進民眾對于政府的更大認同。問題在于,共治絕非只是給政府減壓,透明、責任、回應、參與和有效等原則實際上就是民主的內涵,只不過這種民主是局限在行政層面上,但同樣會觸動根深蒂固的利益格局。
但愿“共治”不會成為花拳繡腿,而是真正走出社會管理的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