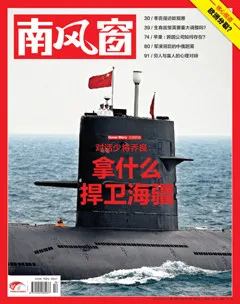轉型期的富人慈善
邢少文
雖然在中國人的財富觀上,我們總能在故紙堆里找到它道德勸說的千年歷史,但每個時代社會轉型的因素都在記錄并決定著這些富人們的所作所為。
在中國富豪榜的變化上,從國美的黃光裕到現在百度的李彥宏,一個身陷官商勾結的囹圄,一個被譽為新知識時代英雄,首富位置的轉換本身就充滿著強烈的時代意味。
首富的轉變我們大概可以做一個類比:在美國的鍍金時代,像約翰·D·洛克菲勒這樣的巨富,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時代發展的車輪,但在車輪底下,亦曾輾軋著他人的血汗之軀。不過,在人生的后半段,洛克菲勒終于將精力從“在其他惡性競爭的商人們身上賺取盡可能多的金錢”轉到“用這些金錢發展有益人類的事業”。此后的百年中,除了石油事業,洛克菲勒家族也持續不斷地從事貧困、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慈善事業。
到了20世紀末,新時代的知識英雄比爾·蓋茨成為了美國新的財富人物象征。他的資本積累過程雖和洛克菲勒創造的托拉斯一樣曾遭受過壟斷的指責,但并沒有那個時代骯臟的血汗,而他成立的蓋茨基金會為他贏得了新一代大慈善家的隆重聲譽。
從這個方面看,美國富豪的更迭軌跡,是產業變遷的軌跡,也是富人慈善事業發展的軌跡。而中國是否也會復制這樣的軌跡?
細究今日中國的富豪排行榜,你也會發現名單中名列前茅的,主要還是來自能源、礦產、房地產(土地)等資源性行業。他們的致富之路,很大程度上與整個國家急劇轉型過程中一小部分人靠占有或壟斷本屬國民所有的自然資源有關,財富積累的過程中涉及大量的權力尋租行為,而普通人卻很少能分享到這些公共資源的租金。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衡量中國富人,似乎都帶著某些“原罪”。因此,富人行善常被認為是“贖罪”。而社會轉型的緩慢與停滯,加劇了貧富差距,也加劇了不同階層間心理層面的對立,社會越來越缺乏相互間的包容和理解,在慈善問題上,輿論“逼捐”的現象屢屢出現,富人身處道德緊箍咒中。
這個體制給了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予便利,也終將反過來損害他們。財富積累方式中不光彩的一面和公辦慈善組織、捐款機構的不公開、不透明,壓抑了富人慈善的意愿,給他們的名聲帶來了損害,常被冠上“為富不仁”的惡名。
公眾期待這些富人們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知識分子甚至“不切實際”地期望他們在公共事務上發出更多的批判之音。但作為體制的獲利者,相當部分富人私下里也會做出受害者的勢態,但當復歸利益,他們就自覺地禁口忌語,認為這與“本分”無關;他們也呼吁改革,但當面對自身利益不確定性時,也體現出中產階層的首鼠兩端;或者,他們干脆就移民去了。這部分人,期望他們不作惡,是底線,為善,則是更高的要求。
當然,事實也并不完全如此,我們也看到,有許多中國富人一直在做慈善,或低調,或高調,或博利他之名,或圖自我提升的愉悅。只是,如同從洛克菲勒到比爾·蓋茨的轉變,一個階層完成自我救贖與造福他人,既需要社會體制的轉型,也需要這個階層集體意識的覺醒。
遺憾的是,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旗下企業常被批評為“流氓企業”的李彥宏先生在慈善榜上有很好的表現,看來,這個過程還很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