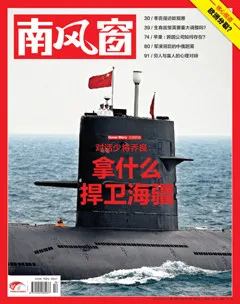農村金融:為誰服務?
李北方

走進河南信陽平橋區的郝堂村,撲面而來的感覺是環境好,村里沒有垃圾,道路與河道修繕整齊,已經翻新和正在改建的民居富有中原歷史文化特色。這個村所呈現出來的面貌與城市化、工業化背景下出現的鄉村凋敝的趨勢形成了鮮明對照。
此前,這里與絕大多數農村沒有什么不同。2009年底,郝堂村“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成立是變化的起點。圍繞這一金融組織,自分田到戶以來就原子化生產經營的村民重新發生了聯系,鄉村自治的能量得到煥發;同時,資金合作社為村委會和村民都提供了金融上的支持,村里的公共事業和村民翻新房屋、擴大生產等都得益于此。
農村發展缺乏金融的支持,是一個老話題了,現有的金融體系非但不能向農村“輸血”,反而如“抽血”機一般,將農村的金融資源提取供城市使用,近年來,很多邊遠地區的分支金融機構裁撤,農民存款都成為難題。
雖然多年的討論見證了問題的持續惡化,但也有人在為解決這一問題而努力。破題農村金融的思路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外置”的,即外部金融資本下鄉,鼓勵發展私人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內置”的,如郝堂村建立自己的村社金融組織。兩種方式的選擇實則指向截然不同的農村發展前景。
大資本與小農:“外置”金融的矛盾
按照《浙江省溫州市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確定的12項任務,第二項即為“鼓勵和支持民居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據稱,溫州試驗如果在一年內證明不成功,就會被叫停,重新調整思路,成功的部分將在其他地區快速復制。
與這一思路相配套的改革取向是農村土地產權改革,持此論調的人士認為,只要明晰土地產權,農民就能用土地、宅基地、林地等向外部金融機構抵押貸款,農村的資產就可以實現金融化。但事實上,問題并沒有那么簡單。
現代化的進程一般被認為是減少農民的過程,即通過使農民與土地分離實現無產化,變成產業工人,同時將土地聚集起來進行大規模雇工生產。但這個趨勢在中國沒有發生,時至今日,中國農村仍以家庭為基本的經濟單位,每家每戶占有少量土地,進行分散的、精細化的農業生產。
學者黃宗智認為,無論是傳統的經濟理論還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都不足以解釋和指導中國農村的問題,尤其是后者的理論體系預設的平等交易主體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黃宗智的觀點是,在農戶與外來資本打交道時,首要的問題是雙方在權力上的高度不平等。具體而言,在與外部金融資本的博弈中,農民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缺乏有效抵押物。
以郝堂村的實際情況為例,信陽是河南農村綜合改革試驗區,按照“金融下鄉+產權改革”的邏輯,政府給農民發了各種各樣的產權證,規定農民的土地、宅基地、林地都可以抵押、買賣、繼承,同時還發了紅頭文件規定銀行必須接受農民這些抵押物并放貸。農民也花錢辦了產權證,也做了估價認證,事實上卻沒有銀行愿意接受農民的土地、宅基地作為抵押物。
“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說,以為明晰了農村的土地產權就可以實現農村土地金融資產化的想法,是缺乏常識的。這個邏輯只對大城市郊區和發達地區成立,因為這些農村土地是有“農轉非”和農業服務化預期的。在偏遠地區,農地、山林等不僅過于零碎、價值偏低、且周期內升值預期為零,基本沒資格成為有效的抵押品,因為銀行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經營,也難以變現。
這種現狀導致了政策性惠農貸款也無法落到實處,據報道,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銀行與基層政府合作,將“惠農卡”發給“優質客戶”,即并不需要貸款的富裕農戶,或者將“惠農卡”集中起來轉讓給“龍頭企業”。結果仍是不需要貸款的得到貸款,需要貸款的求貸無門。
其次,小額貸款公司可能做到不需要抵押即可貸款,但相應地,小額貸款的利息要遠遠高于銀行水平。一年多前,小額貸款的先行者尤努斯被孟加拉國中央銀行解職,孟加拉、印度、墨西哥等國發生的貸款者因不堪重負而自殺或陷入更深的貧困的消息也相繼被爆出,小額貸款的光環褪色,其引發的問題值得更深的反思。
在農村治理機制潰敗,家族、宗派等勢力猖獗的情況下,金融資本與小農之間存在的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不排除導向黑社會化高利貸蔓延的情形。
另外,金融資本下鄉還無可避免地要面對貸款對象分散、管理成本高、信息不對稱、風險難管理等問題,使得在操作中面臨重重困難。“外置”金融的思路將在中國農村遭遇水土不服,是不可避免的。
走向村社金融
郝堂村的“內置”式資金合作社的模式顯示了破解農村金融困境的另一種可能性。
2009年,李昌平應信陽平橋區的邀請前往講座,在交流中誘發了與當地政府合作、嘗試村社金融的想法。經過選點,郝堂村“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于10月成立。
在李昌平等外來專家的參與下,合作社的第一批發起成員們經過兩天的爭吵,制定出了合作社章程。綜合各種意見,大家達成的共識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條是,將合作社的活動范圍限定在村的范圍,即僅在郝堂村的范圍內進行活動。
合作社發起股金34萬元,其中包括7名敬老社員作為發起人,每人出資2萬元,第一批入社的老年社員15人每人出資2000元,平橋區科技局代表區政府投入10萬元,郝堂村村委會投入2萬元,李昌平的課題組投入5萬元。發起人敬老社員、區政府、李昌平等不要利息、不參與分紅,村委會股金的收益用于五保戶幫扶,合作社利息收入中,40%用于老年社員的養老,30%作為積累,15%為風險金,15%為管理費。
根據章程,貸款審批權掌握在由老年社員組成的“10人小組”,理事會只擁有否決權;老年會員除享受分紅權外,還有為村民擔保貸款5000元的權利。村民從合作社貸款的利率為月息1%,村民可以用承包地、林地作為貸款抵押。合作社也吸收社會社員的存款,上限為10萬元。
合作社發展至今,股金已經發展至160萬元,吸收存款150萬元,累計放貸金額290萬元。不但郝堂村村民發展生產、翻新房屋從合作社貸款,村委會也貸款數十萬用于公共事業和從村民手中拿地準備建設養老地產項目。
從郝堂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實踐可以看出,金融資本下鄉會遇到的問題輕而易舉地得到了解決。最根本的原因是,將村社金融限于村社范圍,可以借助原有的社會資本,金融機構放貸要承擔信用評估和風險管理引發的高昂交易成本,這個成本在村社內部可以降到很低。在低管理成本和人情關系的作用下,村社金融的利率可以控制在較低的水平,不會對借貸人造成過重的壓力。
其次,農民的承包地、林地對銀行來說是無效抵押物,但對合作社是有效的,因為經營和變現都很容易。長遠看來,這種形式還有利于土地在村社內部的集中,讓更適合種地的人規模經營,其他人在得到補償的同時脫離農業生產。
尤為重要的是,“內置”金融產生的利息收入留在村社內部,使得農村更能留住人、留住錢,有利于村社共同體的積累和長遠發展。而外來金融資本起到的作用是恰好相反的。郝堂村的經驗目前在信陽平橋區得到推廣,建立數十家村社資金互助合作組織,每家都得到了政府5萬~10萬元的啟動資金支持。
農村的運行邏輯與金融資本的運行邏輯存在根本的矛盾,在農村發展“外置”金融還是“內置”金融,根本的分歧在于是為了資本的發展還是為了農村的發展。
但李昌平認為,外來金融資本和村社金融是可以找到結合點的,他的建議是銀行將資金“批發”給農村的資金合作社,再由資金合作社“零售”給農民。“很簡單,我支持村社一級的金融,超出村一級的我都不支持。”李昌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