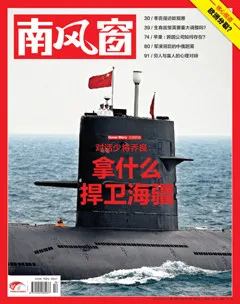利益之上的理念
丹尼.羅德里克
最受推崇的政治理論也是最簡單的:最強大的人才能為所欲為。金融監(jiān)管由銀行利益驅動,醫(yī)療衛(wèi)生政策被保險公司的利益所擺布,而稅收政策則取決于富人的利益。最終能為所欲為的,是那些通過對資源、信息、渠道或純粹暴力機器的控制,最能影響政府的人。
這點在全世界范圍內一樣適用。據說外交政策的首要考慮是國家利益—而不是與其他國家的關系或者對全球社會的關心。除非能和美國(或者其他日漸崛起的大國)的利益取得一致,否則國際協(xié)議不可能達成。在獨裁政權中,政策就是統(tǒng)治者及其裙帶盟友利益的直接表達。這是一個有說服力的說法,不管是在民主國家、獨裁國家或者世界舞臺上,事實總是:狹隘的特定的利益集團擁有足以損害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能力。
但這個解釋還遠稱不上完美,并且經常會產生誤導。利益并不是固定或預設的。它們本身是由理念—關于我們是誰,嘗試去實現(xiàn)什么以及世界如何運轉的信念—所塑造的。我們對自身利益的認知也經常受到理念的加工。
試想有一個公司正想方設法提升自己的競爭地位。它有兩個選擇: 可以解雇一些工人并把工序分包給要價更低的亞洲地區(qū),也可以在工人技能方面進行投資,建立生產力更強、忠誠度更高并因此減低了流失成本的勞動力隊伍。不錯,私營業(yè)主都是利己主義者,但對這一事實的了解并不能告訴我們他們將采取何種政策。最終決定企業(yè)選擇的是一整套對于不同情境可能性的主觀權衡,加上對他們對自身成本和利益的計算。
同樣,試想你是一個窮國的專制統(tǒng)治者。維護你的權力并應對國內外威脅的最佳手段是什么?你是建設一個強勁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還是自我封閉,用損害國內絕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方式來賄賂軍界中人和權勢密友?有的獨裁統(tǒng)治者們采取了第一個戰(zhàn)略;而他們在中東地區(qū)的同行則選擇了第二項。對于自己的利益取決于哪里,兩者擁有不同的概念。
或者思考一下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隨著這個人民共和國逐漸成長為一個大國,他們的領導人必須決定自己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際體系。或許他們會選擇繼續(xù)營造并強化現(xiàn)存的多邊體系,而這個體系過去對他們也多有裨益。但或者他們會喜歡一個特別設定的雙邊關系,使他們可以在與單個國家做交易時占到更大優(yōu)勢。中國及其利益日漸膨脹,但單憑對這一狀況的觀察,我們也無法預測世界經濟的走向。
例子還有很多。對于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來說,究竟是繼續(xù)用緊縮政策扼住希臘的咽喉,并不惜以下一個債務重組為代價,還是放寬相關限制,給希臘一個機會擺脫債務負擔,兩者哪個更能為其國內政治利益服務?對美國在世界銀行的利益來說,究竟應該直接指定一個美國人,還是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同選擇一個最合適的候選人—不管是不是美國人,兩者哪種更好?
我們熱烈討論這些問題時,意味著我們對自身利益的著眼點有不同的概念。我們的利益其實是自身理念的附屬品。那么這些理念從何而來?政策制定者們,像我們所有人一樣,都是時尚的奴隸。他們對何謂可行的政策、何謂理想之事物的觀點都被時代思潮,也就是“風行一時的理念”所塑造著。這意味著經濟學家和其他意見領袖能發(fā)揮極大影響力—不論目的是好是壞。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有一句名言:“即使是最現(xiàn)實的實干家,也往往會被某些早已入土的經濟學家的理念所束縛。”我認為他表述的力度還有所不足。比方說,過去幾十年間毫無約束的自由主義和金融過度膨脹的狀況都是由那些(絕大多數(shù))尚在人世的經濟學家的理念所制造的。
在反思金融危機的時候,譴責大銀行的勢力已經成為經濟學家們最時尚的行為。他們說這都是因為政治家們被金融利益掌控了,而監(jiān)管環(huán)境則放任這些利益集團以巨大的社會成本為代價來攫取巨大回報。但這一論調往往忽略了經濟學家自身擁有的能使事物獲得合法性的角色。政策制定者和監(jiān)管者們相信:對華爾街有利的也是對大眾有利的—而正是經濟學家和他們的理念,使得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抱有這樣的信念。
經濟學家們鐘情于這樣的理論,即所有的政治惡魔都植根于集團化的特殊利益之上。但在現(xiàn)實世界中,他們不可能輕而易舉地脫身,對那些由他們自己大量散布的壞理念所帶來的后果置若罔聞。伴隨著影響力而來的,必須是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