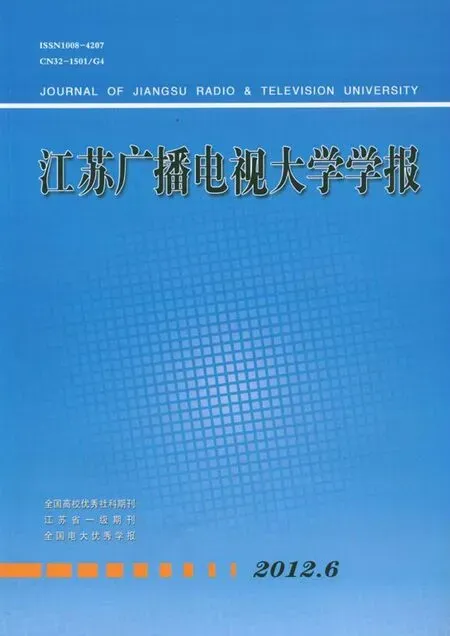認知視角下的翻譯能力探討
張向陽,洪淑秋
從認知科學的角度看,翻譯是人類的認知過程。[1]在原語的選取、理解、語碼轉換的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解決問題,同時也要做出許多決擇。 Wilss[2]認為,翻譯的認知過程是經由原語文本分析過渡到目標語產出的過程,譯者翻譯策略與決定的選擇都是以目標語文本的整體性為終極目標。因此,翻譯過程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為目標語文化中的目標文本的預設目標[3-4]。應該指出的是,就翻譯過程而言,所有類型的翻譯都是話語意義的真實重建[5-6]。
但在翻譯實踐中,多數譯者并沒有完全意識到在翻譯過程中,他們把翻譯文本拆解成可翻譯的單位、搜索功能性對等詞,或者將翻譯完畢的文本重新構建成接近原語文本的類似文本這些過程。事實上,譯者并沒有意識到上述語言學概念與翻譯過程相關。
本文欲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首先探討譯者所應具有的翻譯能力的定義,繼而探討翻譯的過程,而后討論影響翻譯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以及可以觀察到的翻譯能力的外顯形式。最后,討論翻譯能力對翻譯實踐和翻譯教學的潛在用途,希求對英漢互譯和翻譯教學的提升盡到微薄之力。
一、翻譯能力的定義
翻譯能力是一個較為復雜的概念。因為從認知的角度來看,能力屬于一個黑箱(black box)。翻譯能力可以簡單地歸納為能夠進行很好的翻譯工作所具備的知識[7-8]。這些知識可以細化為目標語知識、文本類型知識、原語知識、現實世界知識以及對比知識等[9]。所謂翻譯能力也就是掌握上述不同類型的知識,能夠利用這些知識,在翻譯過程中解決問題、做適當決定的能力。
翻譯能力這個術語最初見于Toury[10-11]《翻譯理論探索》一書,因其與Chomsky[12]著名的語言能力和語言表現的區分很相似,便用來指翻譯實踐的某些方面。但是,我們通過文獻檢索發現,學者們在討論翻譯能力時,所用的術語還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有些學者[7,13-14]討論的是翻譯技能或技巧(translation abilities or skills);有些學者[15]討論的是翻譯成效(translation performance);Nord[4]使用的術語是轉換能力(transfer competence);唯有Chesterman[16]探討的是翻譯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
就翻譯實踐而言,翻譯能力不僅表現在譯者所擁有的語言知識和技能,也表現在譯者所擁有的專業知識中的復雜性、多樣性和近似性(the complexity,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approximation)。另外,為了獲得所需的翻譯效果,譯者還具有翻譯的情景性(situationality)意識,使自己能夠適應不斷變換的新場景,同時還能夠從歷史性(historicity)的角度來處理變化中的情景。[6,3-18]由于譯者處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中,上述語境因素中的各要素相互交織,相互關聯,呈現在整個翻譯的過程中,故而翻譯能力的獲得僅靠語言能力是不夠的。翻譯能力直接影響翻譯的訓練和翻譯工作的不同層面,也決定著譯者的素質。
二、翻譯過程
Nida[17]將翻譯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分析、轉換和重建。所謂分析是對原語不同層次意義的理解,這是翻譯的第一步。只有充分理解了字匯的意義、句法、篇章結構、內隱的文化信息、背景等含義,方能有效、貼切地轉換成目標語表達。轉換就是把一種語言文字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這個過程充分體現譯者的專業技能,需要譯者具有跨語言轉換進行溝通的能力。然而,這個轉換階段卻不是任何精通兩種語言的人都能夠勝任的,需要譯者的翻譯能力,即原語轉換所需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技能。這個能力是需要學習和訓練的。重建就是譯者將需分析和轉換的原語用目標語盡可能準確、完美地再現。
理解是翻譯過程當中的首要環節, 錯誤的理解和偏差的理解, 勢必導致譯文與原語的出入。因此, 理解是準確翻譯的基礎和關鍵, 表達是理解的結果, 即譯者在譯語中盡可能完整準確地把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翻譯新手在翻譯時往往缺少對原文的深層分析, 或是從一詞多義中隨便取其一義, 或是對其語法結構不進行邏輯上的分析而隨意構建譯語文本,導致目標語表達失去了可靠的保障。此外, 在表達上往往不能到位, 致使譯文“譯”痕累累。
三、影響翻譯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在過去,翻譯的能力被認為是天賦能力,是蒼天賦予某些人的能力。具有這種超凡能力的人,可以將原語的文本轉換成目標語的文本[10,18]。在教學上,學翻譯的學生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在開始學習翻譯前就已經是熟練掌握兩種語言能力的人。但是,雙語者并不能順理成章的是稱職的翻譯者。掌握兩種語言知識只是可以進行良好的翻譯活動的前提條件。翻譯者所要獲得的,是語言的聚合(paradigmatic )和組合(syntagmatic)結構,是概念結構的表征。除了語言之外,與語言相關的文化、社會、心理、歷史等因素也與翻譯密切相關。所以,翻譯能力是一種宏觀能力,由不同的能力、技能、知識甚至專業翻譯者的態度構成[19]。這種能力的培養需要后天的訓練。
就翻譯教學實踐而言,提升翻譯能力可以透過語義場中的詞匯理解,以及翻譯錯誤的修正來獲取。
1.詞匯在語義場中的解義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首先要解決的是詞匯。 翻譯者遇到的最困難的事不是碰到了生字,而是從原語文本中抽取概念意義,并將譯文基于概念意義重組,而不是譯文詞匯或結構的編碼。在意義的某些基本領域,原語和目標語在基本詞匯方面有所相同,而在其他領域可能大相徑庭。
根據語義場理論,語言的詞匯內容不該被當成孤立的詞匯,而是應被看做是詞匯間相互交織的網絡的集合體[20]。所謂語義場就是共享顯性的語義組分的系列詞匯單位[21]。多數詞匯的意義部分受制于同一語言中其他詞匯,這些詞的詞義功能以某種方式與語言使用的情景環境或文化相連。語義場中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表示親戚關系的詞匯: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son, daughter, uncle, aunt等。這些詞屬于同一個詞義場,其相關特征包含有輩分、性別、父/母系的家庭成員等。很明顯,這些詞的詞義都具有意義的某一方面。
另外,根據二語習得的研究結果來看,母語使用者習慣使用約定俗成的短語型的表達方式,而二語或外語學習者常會使用不常見的詞匯組合或搭配(collocation)。Siyanova & Schmitt[22]和 Wray[23]認為,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二語學習者過于依賴創造性,所以對語義相似的字匯搭配、組合對等詞組做出了過度自由化的推演。也就是說,當兩個詞為同義詞時,二語學習者可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在詞匯搭配組合中可以隨意調換。比如surgery 和operation,它們互為同義詞。但是,plastic surgery(整形術)并不能隨意地換成plastic operation (整形手術)。在我們的漢譯英文本中,常常會發現缺失這種約定俗成的搭配組合。比如,中文的“巨大變化”這個概念在《牛津搭配詞典》中change前的可搭配形容詞列出了74個形容詞[24],但唯獨少了我們在自己翻譯的文獻里常見的great這個形容詞。
毋庸置疑,若要查找詞匯的意義,自然就要使用詞典。詭異的是,翻譯過程中需要查詞典的詞匯偏偏不是那些生僻的或陌生的詞匯。Nida[25]認為,很多詞典都不太合用,尤其是雙語詞典為甚,因為它們只提供了對應詞而沒有定義。這一點對于新入門的譯者需要特別注意。他們往往認為雙語詞典具有權威性,是非常可靠的工具。若要更好地利用雙語詞典,新入門的譯者要通過利用單語詞典的信息來建立語言間的聯接,投射兩種語言的詞匯區,或建構詞義領域的平行表征。
通過語義場中的詞匯解義活動,譯者可以獲得相應的語義洞察力,同時也會增強翻譯者的翻譯準確度,使他們意識到:原語和目標語的詞與詞之間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對等;一種語言可能有很多詞匯,而另一種語言可能只有一個詞表達類似的概念;有些語言可能缺失其他種語言所對應的詞匯。
2.翻譯錯誤
在二語習得領域,Corder[26-27]曾提出過語言錯誤分析的程序:選擇收集資料、識別語料中的錯誤,將錯誤分類描述、解釋錯誤的原因、評估錯誤以改進教學。同時他還提出二語學習者的錯誤會表現出顯性錯誤和隱性錯誤。所謂顯性錯誤就是在句中存在明顯語法錯誤;而隱性錯誤則看似無錯,但在語境中會導致理解困難。也就是說,顯性錯誤是句子層次的錯誤,而隱性錯誤則是篇章層次的錯誤。
在翻譯界,對翻譯錯誤尚無共識。Pym[14]認為翻譯錯誤太過復雜,既有語言的,又有語用的,還有文化的等不一而足。因此他提出二元性錯誤(binary errors)和非二元性錯誤(non-binary errors),將錯誤的分類簡單化。
周兆祥[28]將翻譯錯誤分成大大小小12種:錯誤最多的是語言方面的;文化、理解方面次之;還有就是翻譯態度方面的。何慧玲[29]從英中視譯的教學觀察結果,列出9類錯誤:缺乏常識、不識復合字或短語、不解幽默風格、假設錯誤、無法正確分析復雜的語法、陌生字或不熟悉的用法、不懂文化指涉、緊張粗心、字匯搭配錯誤等。廖柏森[30]的研究發現,大學生英譯作業中的語言錯誤高于解譯錯誤,英語文本的文體也會造成學生的翻譯錯誤。從翻譯實踐來看,我們可以在《中國翻譯》《外語與外語教學》等國內很多學術期刊中讀到許多有關翻譯失誤及修正的論文,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列舉。整體來說,學生和翻譯新手常犯的錯誤主要集中在詞匯、短語搭配、句子和語篇層次上。至于中譯英的錯誤可能集中在詞匯的精準性、搭配的地道性和英語文本的重建諸方面[31]。
翻譯錯誤并非一無是處,了解翻譯錯誤可使我們窺見譯者們在翻譯過程中的思維過程,也可以間接地了解到譯者的翻譯過程,以及翻譯能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3.翻譯能力提升的觀察點
翻譯能力說到底是認知的過程和產物,是隱性的,難以量化的。但是,我們可以從下面的若干方面觀察。如果看到翻譯者有了正向的變化,我們就可以感悟到翻譯能力的提升。
翻譯單元的擴大:翻譯者所關注的翻譯單元隨著譯者翻譯能力的提升會變得更加寬廣。具體地說,就是譯者從僅關注個別詞義,進而拓展到關注整個句子、整個段落、最終到語篇的整體結構。正所謂以篇章的視野進行整體翻譯,全文貫通。逐步增加的翻譯歷練會使譯者能夠處理更加復雜多變的翻譯問題,比如會從文本結構上去考慮選詞而不僅僅是簡單的尋找對應詞。
參考書的利用:專業的譯者使用參考書有著獨特的習慣。專業譯者使用參考書的頻率遠大于學翻譯的學生或雙語者。專業譯者使用參考書主要在于解決文本的翻譯問題,而學翻譯的學生只是用來解決理解問題。新手主要是用詞典來查生詞,而專業譯者卻是用許多詞典來解決產生翻譯問題的詞條。另外,新手喜歡用雙語詞典,而專業的翻譯卻更喜歡使用單語詞典。
原語文本與目標文本的處理:資深的譯者較少利用拘泥于原語的顯性翻譯,會更多地進行推論,更多地考慮文本的語篇關聯。隨著翻譯能力的提升,譯者對翻譯中出現的問題更加具有意識,會有更多的翻譯對等可供選擇,然后再進行編輯、修訂;也會更加評判性地監控自己的臨時翻譯問題解決方案。另外,資深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會考慮更多的面向,為特定的讀者群提供特定功能的文本。比如,他們會采用宏觀策略或整體策略來進行廣告的翻譯等。
自然,隨著翻譯能力的提升,翻譯過程自動化的程度也會提升。譯者就有能力去處理翻譯過程中更加復雜的方面,做更加重要的翻譯決定。
四、對翻譯教學的啟示
如何提升翻譯能力已經困擾了翻譯教師多年。在圈外的人看來,只要學會了、掌握了外語就自然而然獲得了翻譯能力,完全是外語學習的附屬產品。這種觀點恐怕在國內很有市場。我們在英文的公示語中常發現的錯誤恐怕都是出于這些人之手。但是,研究翻譯的學者或教師都知道,雖然在語言教學中,常常使用翻譯練習來提升語言能力,但是翻譯決非外語學習的附屬產品。在上述翻譯能力的定義討論中,我們就已充分了解翻譯能力包含多個面向的能力。
透過對原語和目標文本,以及相關背景文化等因素的關注,教師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來提升學生的翻譯能力[4,30]:
語言能力的培養:加強學生對英語原文的理解,在課堂上加強閱讀和文本寫作等技能訓練,增加詞匯、短語數量和語法知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要提高學生中文的表達能力。不少翻譯教師都有這個體會:學生的英譯漢能力反而弱于漢譯英能力。這是因為學生對自己的母語表達能力往往過于自信,不求上進。在翻譯過程中,漢語的表述往往受到英語原文結構的制約,從而形成翻譯腔。
翻譯工具的使用:引導學生多使用翻譯輔助工具,例如,單語詞典、好的雙語詞典、搭配詞典、專業詞典、參考工具書、語料庫和網絡搜索引擎等。培養學生獨立自主地進行翻譯和翻譯學習的能力。另外,使用網絡詞典要多加小心,因為那上面的詞典良莠不齊。
翻譯技巧的培養:在課堂內外,為學生提供大量的翻譯練習和講評。讓學生將自己的譯作與別人的譯作比較,這里的別人,可能是同學,也可能是其他媒體已經公開發表的譯作。通過譯作對比,可以取別人之長,補自己之拙。
訓練學生的翻譯技巧,提升他們的翻譯能力。教會他們如何做詞性轉換、順譯逆譯、加減譯法、直譯和意譯等技能的靈活和綜合運用。培養學生自覺、靈活地運用技巧來處理翻譯的難題,而不是憑直覺進行翻譯。
培養學生重建譯文文本的能力,在完成翻譯譯文文本后,進行校訂和篇章調整,防止漏譯、缺譯和誤譯等。
知識面的培養:拓展學生的百科知識,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包括不同語言的文化背景和專業領域的主題知識,督促學生加強閱讀,廣泛閱讀。盡快提升自己的閱讀能力,以提升翻譯能力和水平。
本文討論了翻譯能力的定義和翻譯的過程。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分析語義場中的詞匯解義和翻譯能力提升的影響,并就翻譯課堂應用的可能性提出了相應的策略。在翻譯實踐或翻譯教學中, 應努力增強譯者或學生的英漢雙語的語言能力,配合翻譯理論和技巧的學習與實踐,以及相關百科知識和文化背景的學習,逐步提高翻譯能力。
[1]Danks, J. H. Shreve, G. M. Fountain, S. B. and McBeath, M. K. (eds.)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M]. Sage Publications, 1997.
[2]Wilss, W. A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in Translation[J]. 1994 Target 6, 131-50.
[3]Reiss, K & Vermeer, H. J. Grundlagen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 [M]. Tubingen: Max Niemeyer, 1984.
[4]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M]. Amsterdam: Rodopi, 1991.
[5]Neubert, A. Models of translation[M]∥In S. Tirkonnen-Condit (e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Tubingen: Narr, 1991:17-26.
[6]Neubert, A. Competence in language, in languages and in translation [M]∥In B. Adab and C. Schaeffner (eds.). Develop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3-18.
[7]Hatim, B. and I. Mason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M]. London: Routledge, 1997.
[8]Beeby, A. Teaching Translation from Spanish to English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6.
[9]Bell, R.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M]. London: Longman, 1991.
[10]Toury, G.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Tel Aviv: Porter Institute of Poetics and Semiotics, 1980.
[11]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12]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5.
[13]Lowe, P. Revising the ACTFL/ETS Scales for a new purpose: rating skill in translating [M]∥In M.G. Rose (ed.) Translation Excellence: Assessment, Achievement, Maintenance. New York: SUNY Binghamton Press, 1987:53-61.
[14]Pym, A. Translation error analysis and the interface with language teaching[M]∥In C. Dollerup and A. Loddegaard (eds.)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2:279-288.
[15]Wilss, W. Towards a Multi-facet Concept of Translation Behaviour [J]. 1989 Target, 3, 129-149.
[16]Chesterman, A. Memes of Translatio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7.
[17]Nida, E. A. Toward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 E. J. Brill, 1964.
[18]Seleskovitch D.& M. Lederer (éds). Interpréter pour Traduire [M]. Paris, Didier Erudition, 2003.
[19]Kelly, D. A Handbook for Translator Trainers, Translation Practice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ers 2005.
[20]Stubbs, M. Words and Phrases: Corpus Stud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M].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21]Mel'cuk, I. A. Dependency Syntax: Theory and Practice [M]. SUNY, 1988.
[22]Siyanova, A. & Schmitt, N. L2 Learner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Collocation: A Multi-study Perspective [J].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La Revue canadienne des langues vivantes, 2008,64(3):429-458.
[23]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Crowther, J. 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 Students of Englis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5]Nida, E. A.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M]. Bruxelles 1996.
[26]Corder, S. P.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67,5:160-170.
[27]Corder, S. P.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M]. Hard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1973.
[28]周兆祥.翻譯實務 [M]. 香港:商務印書館,1986.
[29]何慧玲.英中視譯錯誤分析與教學關系[J].翻譯學研究集刊,1997(2):111-135.
[30]廖柏森.大學生英譯中的筆譯錯誤分析與教學上的應用[J].翻譯論叢,2010,3(2):101-128.
[31]謝志強.翻譯與網絡資源:理論、標準、實務 [M]. 臺北:文靜書局有限公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