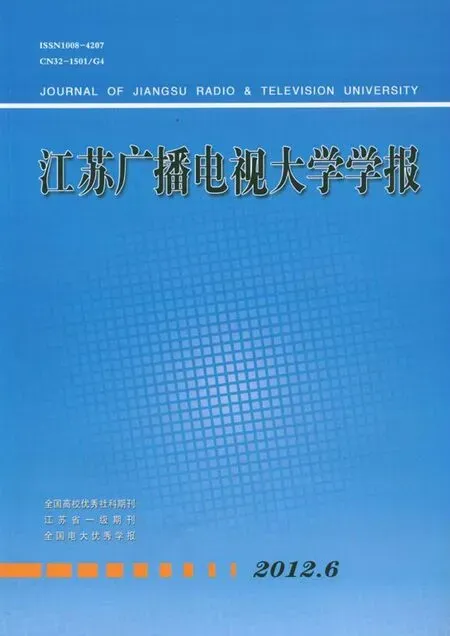論我國親屬免證權(quán)制度確立的路徑選擇
——兼從程序法與實體法的思考
馬 濤
親屬免證權(quán)是刑事訴訟法中證人作證豁免權(quán)的一種,是傳統(tǒng)法制之“親親相隱”原則的集中體現(xiàn)。*雖然,筆者此處所言親屬免證權(quán)是對“親親相隱”傳統(tǒng)法制理念的沿襲或者傳承,但須明確的是,這種沿襲和傳承是超脫于法令規(guī)定的。因為傳統(tǒng)意義之 “親親相隱”偏向于一種互為容隱的義務(wù),違者論罪;而現(xiàn)代法治意義上的“親屬免證制度”則為純粹的權(quán)利,可為放棄。另據(jù)學(xué)者考證:因受西方法律的影響,至《大清新刑律》,基本上取消了親親相隱之“干名犯義”的強制性法定義務(wù)或綱常義務(wù)的規(guī)定,只剩下容隱權(quán)利的規(guī)定,即親親相隱實現(xiàn)了從以義務(wù)為主要特征到以權(quán)利為主要特征的轉(zhuǎn)變。因此,稱“親屬免證制度是傳統(tǒng)法制之‘親親相隱’原則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不存疑義的。參見范忠信《中西法律傳統(tǒng)中的親親相隱》,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1997年第3期,第87-104頁。具而言之,“親屬免證權(quán),是指在訴訟中證人由于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存在某種特定的親屬關(guān)系而享有的拒絕作證的權(quán)利,其權(quán)利內(nèi)容包括拒絕充當(dāng)證人、拒絕陳述某些問題、不出庭作證”。[1]確立親屬之間的免證,不僅是對親情人倫的重視,為維護(hù)倫理體系所必須,更是證人作證之人權(quán)與犯罪國家追訴主義之間的博弈與權(quán)衡。然而,我國國民觀念雖深受“親親相隱”之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但我國的刑事立法(包括程序法與實體法)不僅沒有堅守此項傳統(tǒng),并且通過程序法之查明客觀真實的訴訟理念及實體法“窩藏、包庇”等罪名的設(shè)置,幾近完全將親屬免證權(quán)排除在現(xiàn)行刑事立法之外。筆者以為,這種立法模式在導(dǎo)致立法與民眾觀念相“脫離”,造成“徒法不能以自行”之困境的同時,也為社會帶來不穩(wěn)定的潛在因素。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是必要的,且親屬免證權(quán)的確立必須兼從程序與實體兩個角度探討路徑。
一、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的依據(jù)
親屬免證權(quán)制度是西方法治發(fā)達(dá)國家訴訟程序法中一項重要的證據(jù)規(guī)則,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在規(guī)定公民作證義務(wù)的同時,出于保護(hù)親情、保護(hù)特殊關(guān)系等多種因素的需要,均承認(rèn)親屬免證權(quán),只不同的是享有免證特權(quán)的證人范圍有寬有窄”而已。[1]但是在我國的立法進(jìn)程中,由于秉承發(fā)現(xiàn)客觀真實的訴訟理念,過分地強調(diào)對犯罪的追究而忽視對人權(quán)的尊重和程序性權(quán)益的保障,因此,立法體系中并無有關(guān)親屬免證權(quán)的明確規(guī)定。筆者以為雖然此為訴訟理念的差異使然,但更為立法上的缺陷、司法中的不足,亟待完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親屬免證并非完全意義的“舶來品”,中國古代“親親相隱”原則已蘊含著親屬免證特權(quán)的思想。“從孔子的‘父子相隱’觀念起源到漢初‘親親得相首匿’在法律上的正式確立,至唐朝的‘同居相隱’……綿延至明清,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比較完備的親屬證人證言規(guī)則系統(tǒng):一是親不為證;二是不得強迫親屬互證其罪;三是為親者證處刑。”[1]由是觀之,中國法制傳統(tǒng)關(guān)于親屬免證的規(guī)定相當(dāng)完備,而現(xiàn)行立法卻并未體現(xiàn)傳統(tǒng)。這是現(xiàn)實與傳統(tǒng)的“斷層”。因此,從法律制度的傳承性而言,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制度有著法制傳統(tǒng)之基礎(chǔ)。
第二,親屬免證權(quán)的確立,在回歸倫理、維護(hù)社會關(guān)系穩(wěn)定及證據(jù)規(guī)則之建立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親屬免證制度的確立是對倫理的回歸。為斷案令親屬指證其罪,不僅缺乏可期待性,同時也是對人倫、親情的漠視。親屬在庭上對峙,雖對于案件事實的查明可能有利,但對倫理秩序的破壞乃至給司法權(quán)威帶來的弊端則遠(yuǎn)大于對犯罪成功追究所帶來的好處;其次,親屬免證權(quán)的確立能夠促進(jìn)特定關(guān)系的穩(wěn)固。正如美國證據(jù)學(xué)家喬恩·R·華爾茲教授所言:“證言豁免權(quán)允許人們在訴訟程序中拒絕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某種秘密情報。這種特免權(quán)存在的一個基本理由是:社會期望通過保守秘密來促進(jìn)某種關(guān)系。社會極度重視某些關(guān)系,寧愿為捍衛(wèi)保守秘密的性質(zhì),甚至不惜失去遠(yuǎn)見結(jié)局關(guān)系的重大的情報”,接著他舉例稱,“婚姻關(guān)系很明顯是值得促進(jìn)和保護(hù)的關(guān)系”,所以“夫妻之間所享有的免證特權(quán)是絕對的或者說是不容侵犯的”。[2]當(dāng)然,親屬免證權(quán)所要保護(hù)的重要關(guān)系遠(yuǎn)不限于婚姻關(guān)系,如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guān)系等,均為其維護(hù)的對象;最后,親屬免證權(quán)的確立,其本質(zhì)上是對證據(jù)規(guī)則制度的完善和補充。采用強迫手段或者違反程序之措施獲得的親屬證言必須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jù),否則,對該類非法證據(jù)的采信不僅是對程序正義的踐踏,更會有損司法的權(quán)威與公正。
第三,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是邁向法治國的必經(jīng)過程,也是在與境外尤其是港澳臺等地區(qū)區(qū)際司法合作中,證據(jù)采信制度之銜接的需要。我國臺灣地區(qū)“刑事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了親屬證言特免權(quán)*其第180條規(guī)定:證人有如下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一、現(xiàn)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五親等之內(nèi)血親、三親等內(nèi)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二、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三、現(xiàn)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現(xiàn)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對于共同被告或自訴人中一人或數(shù)人有前項關(guān)系而就僅關(guān)于其他共同被告或其他共同訴訟之事項為證人者,不得拒絕證言。(《臺灣新編六法全書》,第100頁),香港與澳門的相關(guān)法律或者司法實踐中,亦有類似規(guī)定。*具體可見《香港證據(jù)條例》第6條、第7條及第11條的規(guī)定,如“本條例的規(guī)定,并不使丈夫有資格或可予以強迫在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中為妻子提供證據(jù)或者提供證據(jù)指證妻子,亦不使妻子有資格或可予以強迫在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中為丈夫提供證據(jù)或者指證丈夫”;《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刑事訴訟法法典》第121條,即關(guān)于“血親及姻親之拒絕(作證)”等等。所以,筆者認(rèn)為親屬免證權(quán)的存在有其重大的意義與價值,無論是從法治趨勢而言,還是就大陸與港澳臺刑事立法的協(xié)調(diào)以便于區(qū)際司法協(xié)助的建立而論,均應(yīng)當(dāng)通過立法的形式對親屬免證權(quán)做出直接的規(guī)定。
二、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的困境:兼顧程序與實體
親屬免證制度遲遲無法在刑事立法中得以確立,其中固然有立法傳承性的影響,但在筆者看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程序法與實體法修改的不同步性導(dǎo)致了親屬免證權(quán)確立的困境。
1.親屬免證權(quán)確立的程序法之困境
親屬免證權(quán)確立的程序法困境主要表現(xiàn)為在《刑事訴訟法》上的“障礙”。如前文所言,我國《刑事訴訟法》持查明客觀真實的訴訟理念,過于注重對犯罪的追究及國家利益的維護(hù),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個體訴訟權(quán)利的保障。就證據(jù)立法而言,刑訴法規(guī)定“凡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wù)”。單就證人主體而言,除“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dá)的人,不能作證人”外,并無例外規(guī)定。在最新通過的關(guān)于《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下稱新《刑事訴訟法》)中,為了保證證人出庭作證,對“經(jīng)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dāng)理由不出庭作證的”情形,在規(guī)定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的同時,對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做了例外之規(guī)定。因此,“業(yè)界人士認(rèn)為,這些規(guī)定確立了近親屬的免證權(quán)。”[3]但是,筆者以為新《刑事訴訟法》第188條所確立的規(guī)則并不是親屬免證權(quán)。因為,新《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guī)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wù)”,并沒有明確將親屬排除在證人范圍之外。第188條僅規(guī)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得被強制到庭,但也并不能得出就此而免去該類人的作證義務(wù)的結(jié)論。相反,按照第60條的規(guī)定,雖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得被強制到庭,但仍然不能排除公安司法機關(guān)庭外取證的可能。因此,稱新《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了親屬免證權(quán)的依據(jù)并不充分。
有論者以刑事訴訟中的“直接言詞原則”結(jié)合新《刑事訴訟法》第188條關(guān)于“不得強迫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證”的例外性規(guī)定,認(rèn)為在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與司法實踐中已確立親屬免證制度。理由是對“直接言詞原則”的踐行阻卻了對不得強制到庭人員 “庭外取證”的可能,但筆者認(rèn)為這種論證思路是失當(dāng)?shù)摹?/p>
首先,何謂“直接言詞原則”? “直接言詞原則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法官必須在法庭上親自聽取雙方當(dāng)事人、證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陳述或辯論,從而形成對案件事實真實性的內(nèi)心確信;其二、審判程序應(yīng)以言詞陳述的方式進(jìn)行,當(dāng)事人在訴訟中就事實主張和證據(jù)的可信性進(jìn)行攻擊和防御時必須以言詞辯論的方式進(jìn)行。”[4]因此,直接言詞原則主要是針對法官及審判程序的要求。雖然,理論上“貫徹直接言詞原則,也要求證人必須出庭作證”[5],但在實踐中卻并非如此,相反,長期以來我國刑事司法實踐存在著證人出庭作證難的情形,導(dǎo)致“全國法院出庭率普遍低下”[6],所以“庭外取證”的方式普遍存在。其次,原《刑事訴訟法》第157條明確規(guī)定“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應(yīng)當(dāng)當(dāng)庭宣讀”,從而肯定“未到庭作證證人的書面證言經(jīng)宣讀也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4],即便新《刑事訴訟法》對于原《刑事訴訟法》中促使證人不出庭作證的因素予以修正,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后者的不當(dāng)影響必將延續(xù),更何況親屬免證權(quán)的內(nèi)涵并不局限于免證親屬不到庭作證?最后,就刑事訴訟模式而言,職權(quán)主義是我國刑事審判的傳統(tǒng)模式,與英美法系中的當(dāng)事人主義審判模式不同的是,其不重視對抗式庭審中的證人質(zhì)證,因此也導(dǎo)致中國刑事審判實踐中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困境。綜上,以理論上的直接言詞原則和新《刑事訴訟法》第188條的規(guī)定,認(rèn)為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已經(jīng)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的觀點不具說服力。
盡管新《刑事訴訟法》朝著親屬免證權(quán)的方向邁出了一步,亦即通過強制措施強調(diào)證人的出庭義務(wù)及第188條的例外規(guī)定,但這僅僅只是一小步,因為刑事訴訟追求客觀真實的理念、刑事追訴的國家本位與證人出庭作證難的現(xiàn)狀,與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的訴求相去甚遠(yuǎn)。
2.親屬免證權(quán)確立的實體法之阻礙
親屬免證權(quán)確立的實體法之阻礙,其本質(zhì)是《刑事訴訟法》沒有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之必然結(jié)果;但同時,實體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親屬免證權(quán)在程序法中的確立,最大障礙在于《刑法》第310條對“窩藏、包庇罪”的規(guī)定。筆者此言,并非質(zhì)疑窩藏、包庇罪設(shè)置的必要性,而是意在強調(diào):若想在程序法中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則必須同時在實體法上排除窩藏、包庇罪對得免證親屬的適用,否則,缺少實體法保障的親屬免證權(quán),在程序法上亦不可能真正存在。
刑法第310條所規(guī)定的窩藏、包庇罪,可分解為窩藏罪與包庇罪。“窩藏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匿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的行為;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作假證明包庇的行為。”[7]從此罪的構(gòu)成要件而言,構(gòu)罪主體為一般主體;但是從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因?qū)Ψ缸锵右扇擞懈C藏、包庇行為而獲此罪的犯罪嫌疑人近親屬則不在少數(shù)。將親屬尤其是近親屬之間的窩藏、包庇行為以罪論處,此舉是否合適,值得反思。比如,“曾有報道:一位母親因藏匿自己犯罪的兒子被捕入獄,在獄中,面對前來采訪她的記者,她仍說:‘我能藏一天算一天,盡一盡做母親的心’。”[8]雖然刑法的功能,部分在于打擊犯罪,但更在于保障人權(quán)。針對這種近親屬間“親親相隱”般的窩藏、包庇行為,無視親情上的期待可能性的缺乏,仍以窩藏、包庇罪論處,筆者認(rèn)為是不妥當(dāng)?shù)摹!皩Ψ缸锶说慕H屬實施的窩藏、包庇行為,應(yīng)認(rèn)定為缺乏期待可能性,不宜以本罪(窩藏、包庇罪)論處。”[7]“即使構(gòu)成犯罪的,也應(yīng)從寬處罰。”[9]對這種基于親情人倫而不予處罰或雖予以處罰但減免其罰的情形,我國臺灣地區(qū)“刑法”在“藏匿人犯或使之隱避罪”(第164條第1款,相當(dāng)于大陸地區(qū)的“窩藏、包庇罪”)的“減免特例”(第167條)中規(guī)定“配偶、五親等內(nèi)的血親或者三親等內(nèi)的姻親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的脫逃人,而犯本罪(指第164條第1款所規(guī)定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10]
關(guān)于親屬間窩藏、包庇行為的定性,亦有其他的觀點與見解,如:有主張對直系血親或姻親犯窩藏、包庇罪的,法律應(yīng)有減免處罰的區(qū)別規(guī)定[11];或為使家屬免予刑罰處罰而實施窩藏、包庇行為的,不予處罰[12];及基于親情、人權(quán)保護(hù)等多方面考慮,可對親屬間的窩藏、包庇行為雖定罪但免罰[13];等等。那么,結(jié)合本文的主題,窩藏、包庇罪與親屬免證權(quán)的確立與否,乃至與程序法中的親屬免證權(quán)存在何種關(guān)系呢?筆者認(rèn)為:窩藏、包庇罪侵犯的法益是正常的司法秩序,而犯罪人親屬拒絕作證,甚至隱匿證據(jù)、窩藏犯罪人則是對窩藏、包庇罪所保護(hù)的法益的侵犯。如果在程序法上確立親屬的免證權(quán),將免證親屬之間所為的缺乏期待可能性的窩藏、包庇行為不以實體法中的此罪論或減免其刑,那么從實體法的角度而言,程序法對親屬免證權(quán)的確立為近親屬間合乎倫理的窩藏、包庇行為的非罪化或刑罰輕緩化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從程序法上講,實體法對免證親屬的上述行為做出合乎人倫的評價,則間接地為在程序法中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提供了實體法上的保障。而且,無論從實體與程序,還是親屬免證權(quán)與免證親屬間窩藏、包庇行為的非罪化或者輕罰甚至非罰化,都應(yīng)當(dāng)被認(rèn)為是對“親親相隱”法制觀念的復(fù)歸。
三、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的路徑探討
1.基于程序法的思考
如前文所言,筆者認(rèn)為,若要確立親屬免證權(quán),在程序法上必須從證人資格的一般條款中明確將免證親屬“技術(shù)性”*所謂“技術(shù)性”排除,并非是指根本否定免證親屬的證人資格。因為親屬免證作為免證親屬的一項權(quán)利,當(dāng)然可以放棄。筆者謂之“技術(shù)性”排除,即是為了防止自愿放棄免證權(quán)的親屬因無證人資格而無法出庭指證的尷尬情形的出現(xiàn)。地排除在外;同時,并為防止司法機關(guān)向被告人親屬非法取證,有必要利用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對侵犯親屬免證權(quán)而取得的證據(jù)予以排除。
首先,關(guān)于得免證親屬的證人資格的規(guī)定。親屬免證權(quán)是出于親情倫理的考慮而作的注意規(guī)定,非免證親屬無作證能力的擬制。因而,在規(guī)定證人資格時,不應(yīng)將免證親屬完全排除出證人之列,剝奪其證人之資格。但必須對享有免證權(quán)的親屬做出不得強迫其證明的規(guī)定,對因強迫而獲得的證人證言,明定不得作為斷案的依據(jù);另外,為了確保得享有免證權(quán)之親屬能切實享有此權(quán),司法機關(guān)應(yīng)負(fù)有權(quán)利闡明義務(wù),否則,即便是非以強迫手段獲取的證言,亦應(yīng)被排除。
其次,關(guān)于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例外”。新《刑事訴訟法》第188條的規(guī)定,是為了避免親屬當(dāng)庭對質(zhì)而過分淡漠親情倫理給社會普通民眾帶來難以接受的道德危機。但是,根據(jù)證人均具有作證義務(wù)、肯定庭外所取證言之證明力的規(guī)定和司法實踐,此“例外”情形并未見其維護(hù)親情的功用。因此,筆者認(rèn)為真正意義上的親屬免證不僅包括免強制出庭之義務(wù),更應(yīng)一并賦予免證親屬拒絕庭外作證之權(quán)利。對此,需要相關(guān)部門在刑事審判過程中,嚴(yán)格遵守直接言詞原則,確保當(dāng)庭質(zhì)證能夠作為采信證人證言的必需環(huán)節(jié)。
最后,關(guān)于對非法取得的親屬證言的排除。新《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采用暴力、脅迫等方式搜集的證人證言,應(yīng)當(dāng)予以排除。而對非法取得免證親屬之證言的排除,筆者認(rèn)為,無論取得的手段是暴力、脅迫等非法手段還是“庭外取證”、未進(jìn)行權(quán)利告知的程序性違法,均應(yīng)采用嚴(yán)格的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即一律排除。
總之,親屬免證權(quán)在《刑事訴訟法》上確立,一方面要積極且明確地規(guī)定親屬免證權(quán);另一方面,要就侵犯親屬免證權(quán)的行為規(guī)定救濟(jì)措施,且在所有的救濟(jì)措施之中,最有效也是最應(yīng)該被采用的即為對非法取得的免證親屬的證言進(jìn)行排除,即否定其證明力。
2.基于實體法的考量
從實體法上探討親屬免證權(quán),實質(zhì)在于為程序法中已然確立的親屬免證權(quán)提供免罪或減免刑罰的保障。關(guān)于《刑法》第310條對“窩藏、包庇罪”的規(guī)定與親屬免證權(quán)之間的關(guān)系,筆者前文已言明。司法實踐中,符合免證特權(quán)主體的親屬,常有對犯罪人窩藏、包庇之作為。因此,如果僅在程序法上確立親屬免證制度,但不就相關(guān)實體法中可能被觸犯的罪名作相應(yīng)的注意性規(guī)定,那么前者毫無疑問地難以實現(xiàn)。因此,必須將實體罪名刑罰之配置的變動作為完善程序之配套措施。
具體就“窩藏、包庇罪”對于行使免證權(quán)親屬應(yīng)如何配置的問題,前文中基本上已經(jīng)有原則性的表述。但筆者想借此強調(diào)的是:親屬免證權(quán)固然體現(xiàn)親親相隱,即在“具體場合下行為人因親情原因而無法實施法律所要求的作證、檢舉及揭發(fā)的義務(wù)”,甚至假設(shè)其實施情節(jié)較輕的窩藏、包庇行為,都應(yīng)認(rèn)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因而不能歸責(zé)于行為人。”[5]但這并不意味著具有免證特權(quán)的親屬便可以無所顧忌地幫助犯罪人逃避罪責(zé)。因此,對具有免證特權(quán)的親屬實施的觸犯《刑法》的行為,要結(jié)合具體情節(jié)視其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而判斷是否影響其答責(zé)能力,作為對其或不以罪論或雖以罪論但可減免其刑之依據(jù)。
3.立法修正之討論
就《刑事訴訟法》而言,一是在第50條“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中,增加“以及不得強迫有免證特權(quán)的人提供證人證言”;二是完善第60條第1款規(guī)定,即“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wù)。但是法律法規(guī)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三是在第九章“其他規(guī)定”中增加一項,即“(七)‘具有免證特權(quán)的人’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近親屬(即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及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其他人員”。
對《刑法》相關(guān)條文作相應(yīng)之“配套”保障式的變動,在第310條增加一款作為注意性規(guī)定,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屬犯前款所述之行為,情節(jié)輕微的,可不以犯罪論;情節(jié)嚴(yán)重的,按前款之罪論,但應(yīng)當(dāng)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刑罰。”
四、余論
親屬免證權(quán)的確立,修正立法是前提,但更為關(guān)鍵的是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實施和行使。言及親屬免證權(quán)的司法運作,就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即親屬免證權(quán)當(dāng)如何行使:需要得免證親屬進(jìn)行申請,抑或司法機關(guān)予以告知?對此,筆者認(rèn)為澳門地區(qū)“刑事訴訟法典”的規(guī)定極具啟發(fā)意義,該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guī)定:享有免證權(quán)的“血親及姻親”“得拒絕以證人身份作證言”,且“有權(quán)限接受該證言之實體,須提醒上款所指之人有權(quán)拒絕作證言,否則所作證言無效”。由此觀之,親屬免證作為一種權(quán)利,應(yīng)當(dāng)由權(quán)利人主動行使,具體的行使方式可為向司法機關(guān)主張,但無需申請;如若主張,應(yīng)當(dāng)證明親屬關(guān)系的存在。再者,為了防止因權(quán)利人不了解權(quán)利而出現(xiàn)違背親情人倫的情形,司法機關(guān)應(yīng)當(dāng)盡到“提醒”的闡明義務(wù),否則“所作證言無效”。只有如此,才能契合親屬免證制度的價值初衷。
[1]張建飛.親屬免證權(quán)制度及其法律效益價值探微[J].政治與法律,2008(7):99-104.
[2]喬恩·R·華爾茲.刑事證據(jù)大全[M].何家弘,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1993:252,283.
[3]彭劍鳴.免證權(quán)的合理化——從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入手[J].貴州警官職業(yè)學(xué)院學(xué)報,2012(1):52-55,66.
[4]趙嵬.直接言詞原則與刑事證人出庭作證問題研究[J].北京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8(3):80-85.
[5]卞建林.刑事訴訟的現(xiàn)代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328.
[6]胡云騰.證人出庭作證難及其解決思路[J].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06(5):557-561.
[7]張明楷.刑法學(xué)(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57-561.
[8]謝佑平,陳瑩.“親親相隱”與親屬間窩藏、包庇類犯罪的豁免[J].河北法學(xué),2011(12):39-44.
[9]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90.
[10]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冊)[M].修訂五版.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124-126.
[11]汪永樂.關(guān)注刑法的人倫精神——以新刑法310條規(guī)定的窩藏、包庇罪為視角[J].政法論壇,2001(1):80-85.
[12]汪鈞.從“親親相隱”原則談對窩藏、包庇罪的立法完善[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2006(2):130-132.
[13]沙影.對親屬應(yīng)否成為窩藏、包庇罪的主體的探討[J].湖北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6(11):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