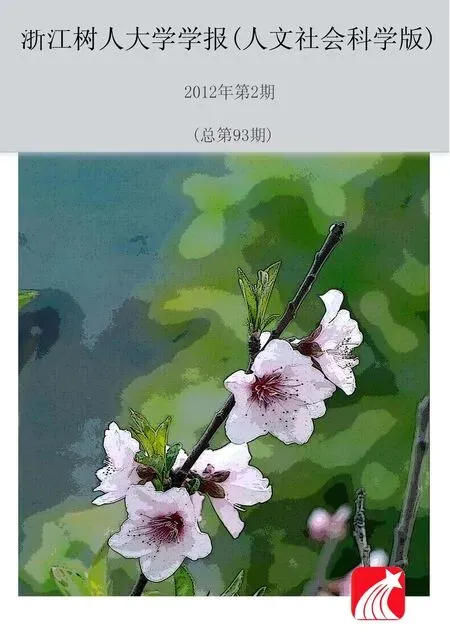中國傳統詩學視閾下的詩歌意象翻譯
叢滋杭
(浙江樹人大學外國語學院,浙江杭州310015)
以往在中國古詩中才出現的“意象”一詞似乎越來越被文人所濫用,只要搭上點隱喻的邊便是意象。甚至,西方龐德創造的彼“意象”也被等同于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縱觀之,對意象的理解不外乎有三種觀點:一是意象一詞涵義不分中西方,具有普適性;[1]62,[2-3]二是西方所謂的“意象”有其自身發展歷史,似乎與中國古詩沒有任何淵源;[4][5]三是西方“意象派”創造的意象是接受中國古詩的結果,但內涵有著實質不同。[6-8]而意象的涵義到底是什么,卻總是語焉不詳,由此出現了翻譯中五花八門的現象。筆者擬站在中西方詩學的角度,從中國古詩意象的淵源及特征,試圖對“意象”一詞涵義進行再思考,以期拋磚引玉。
一、中國傳統詩學與意象
說到中國古典詩歌意象,古典詩學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詩與禪的關系一直存在不同觀點。主張詩禪一致論者倡言“大抵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滄浪詩話·詩辨》)[12],“妙悟”是嚴羽以禪喻詩的核心內容。在佛教禪宗里,妙悟本指主體對世界本體“空”的一種把握,所謂“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12]就詩而論,妙悟即“真”是指詩人對于詩美的本體、詩境的實相的一種直覺。而反對者認為,詩與禪相類,亦有合有離。比如,詩以道性情,而禪則期于見性而忘情。詩人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而詠歌之,而禪卻不以置懷,動于中輒深以為戒,而況形之于言乎?總之,在詩與禪的關系上,古人或見其同而不見其異,或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對此,當代學者也未加深究。周裕鍇對詩禪相通的內在機制從四個方面加以概括,即價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維方式的非分析性,語言表達的非邏輯性,肯定和表現主觀心性。①應該說,這種概括較為全面地揭示了禪與詩本質上的相通,給人以啟迪。而蔣寅認為這還不夠,還應揭示出一種內在的驅動力。他認為:“詩與禪在經驗的不可傳達性、傳達的迫切要求以及傳達的方式上有著驚人的相似,或者說有一種異質同構的相似關系,正是這點決定了以禪喻詩的可行和必要。”[1]62蔣寅集古今中外學者對禪宗和詩學的觀點,闡述了禪與詩的特點:一是不可言說的言說;二是不說破和悟入。不論他概括得是否全面,筆者更關注詩人以何種方式表達這些特點。蔣寅雖然提到了中國古代詩學在表達方式上的兩個特點——意象性和“不說破”,但卻語焉不詳。筆者認為,僅一個意象就完全可以把禪與詩的特點表現出來,也就是說,意象是表現禪與詩特點的獨特方式。
國內許多學者都對意象概念作過界定,蔣寅更是從語象、物象、意象和意境等方面試圖闡明其不同,還意象以本來面目。然而,由于其長期的中西詩學的浸潤,在界定概念時,往往中西結合,最終導致概念不倫不類。他一方面列舉古人對意象約定俗成的觀點,另一方面又搬出龐德的意象觀和克羅齊的直覺觀作為印證。于是,意象在詩歌中成了滿天飛的東西,似乎只要有點顏色、有點動作的名詞就成了意象。例如在他看來,“兩只黃鸝”雖加上數量限定,仍只是黃鸝的一般狀態。“鳴”和“上”賦予黃鸝和白鷺以動作,“翠柳”、“青天”再增添環境和氣氛,于是鮮活的意象奪目而出。[1]21再如他認為,“雞聲”、“茅店”或“月”都只是名詞提示的簡單的象,根本沒有意,只有三個視覺表象融合而成的復合體才具有了意象的性質。[1]20
意象首先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核心概念,不應將其與西方學說相提并論。比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在龐德創立的意象疊加的基礎上,創立了意象并置(Juxtaposition)的技巧,以此擯棄隱嵌在所謂意象中的主觀意識,著力于生動、準確地描繪事物,在狀景寫物之中使義理或思想得以自然呈現,即所謂“凡理皆寓于物”(There are no ideas but in things)。[9]蔣寅就這樣把意象派創作的詩歌技巧簡單地套在了中國古典詩歌意象上。其次,正如中國古代詩學傳遞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象集語象和物象于一體,簡單地運用西方二分法的做法把三者嚴格區分顯然不合常理。也許,韋利在解釋為什么他的中國詩翻譯幾十年來一直受到歡迎時說的一段話能夠說明這個觀點:
……他們之所以覺得中國詩合他們的口味,是因為中國詩主要跟具體的特定的可觸可見的事物打交道,它談一顆美麗的樹,一個可愛的人,而不談諸如美或愛之類的抽象概念。[10]276
韋利的話說對了一半。在具體的、特定的和可觸可見的事物背后,中國古詩意象帶有言外之意,即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但其聯想是自然的,仿佛是隨意的,是景色本身所固有的。所謂“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11]。中國古詩意象以平淡現激情。正如嚴羽所說:“未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之風,殆川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可謂不幸也。”[12]詩人很少讓感情泛濫出來,而是冷靜地將個人的感受放進“具有共通性”的自然意象中去。因此便有學者聯想到了艾略特提出的“非個性化”,似乎認為二者之間有著某種共通之處。[10]276事實上,除了字面上的相似外,完全是毫不相關的詩學觀。為此,從中國古典詩歌意象表現出來的特征加以分析,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
二、古詩含蓄的體現
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辨》中提出“別材別趣”說。“材”即詩歌題材,“別材”即是說詩歌創作在題材和內容方面有自己特殊的要求和規定,即:吟詠情性。反對以知識學問為具體內容和表現對象,反對江西詩派的創作風氣。[12]他認為,只有吟詠情性的詩歌才具有感發讀者的審美效果。“趣”指藝術旨趣,“別趣”即是說詩歌有其特殊的藝術旨趣。它要求詩人在詩歌的語言、情感和意趣等方面做到“不落言筌”,“無跡可求”。“妙悟說”便是其主要審美思想的體現。嚴羽根據“悟”的程度,把“悟”分為不假悟(漢魏詩人)、透徹之悟(謝靈運至盛唐詩人)和一知半解之悟(中晚唐詩人)三類,并要求詩者以盛唐為師。
唐代自開元至大歷間,為唐詩的全盛時期,有著名詩人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高適和岑參等。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直至“安史之亂”爆發以前,是唐代社會高度繁盛且極富藝術氣氛的時代。唐詩經過一百多年的準備和醞釀,至此達到了高峰。雖然,在唐詩的初、盛、中和晚期四個階段中,盛唐為時最短,但其成就最為輝煌。這一時期,不但出現了偉大的詩人李白,還涌現出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優秀詩人。許多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廣為傳誦的詩篇,便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熱情洋溢、豪邁奔放和郁勃濃烈的浪漫氣質是盛唐詩的主要特征;即使是恬靜優美之作,也同樣是生氣彌滿、光彩熠熠的。這就是為后人所艷羨的“盛唐之音”。一般來說,詩歌“以盛唐為法”的理由有三:一是具有吟詠情性、不落言筌和無跡可求的審美特征;二是透徹之悟,運用妙悟的藝術思維方法進行創作;三是筆力雄壯,氣象渾厚,具有自然含蓄又深沉的內在力量。
從上述三個特征看,含蓄的特征貫穿始終。含蓄作為詩歌表達的基本原則,與直露、一覽無余相對,意味著一種富于暗示性的、有節制的表達。這種修辭特征發軔于《詩經》,到唐詩臻于爐火純青的境地。關于含蓄概念的豐富和發展,蔣寅認為,禪僧說禪“不說破”和“繞路說禪”的言說方式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或者更明確地說,是禪宗的“不說破”對詩學產生了直接的影響。[1]84-85
佛教闡釋教義有兩種方式,即表詮與遮詮。不作直接肯定的遮詮可以說就是一種不說破,它將禪宗的言說方式導向隱喻、暗示的方向。據此,蔣寅把“不說破”歸結為修辭規則和要求,其內容包括代語、不犯題字和不著題。而這三者是漸次的關系,代語只是個別詞語的置換,與詩所詠對象或主題無關;不犯題字是以更接近禪家“不說破”本旨的方式獲致含蓄效果的思路;而不著題則將“不說破”推向極致,所謂“萬物驅從外物來,終篇不涉題中意”。總之,在他看來,古典詩學的藝術表現論以體物為支點,完成了一個由粗到精,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的理論深化過程。正是在對這些修辭規則及其具體手法的研討中,含蓄概念的內涵愈益豐富,外延愈益明晰,終于完成其理論化過程,確立起作為體現古典詩學審美理想的核心概念的地位。[1]90
在筆者看來,盡管蔣寅無法舉出詩家明言取法于禪的材料,但是從佛教禪宗角度考證含蓄有其事實根據。然而,僅僅把詩學傳統中的含蓄觀念的形成看做是吸收“不說破”命題所包含的藝術經驗似乎有掛一漏萬之嫌。說到含蓄,意象一詞萬萬不可舍去不論,它有著“不說破”的諸多特征,但其內涵又遠非修辭手段或以禪喻詩所能囊括,無怪乎有學者提出以意象為核心建構中國的文藝理論體系。
三、古詩意象及翻譯
關于古詩翻譯,呂叔湘從中國文字之艱深,詩詞鑄語之凝練的角度道出翻譯之難。[13]事實上,古詩意象的翻譯難度恐在語詞之上,這也是為什么一些西方譯者避之不及的緣故。從呂叔湘搜集的中詩英譯數目看,歷經詩經、楚辭、漢魏六朝及唐詩,總共才60首詩。即便這區區幾十首詩歌的翻譯,呂叔湘通過比錄,也發現了不少問題,翻譯主要是圍繞語詞、人稱、語序、音律、詩體和變通等,古詩意象竟未提到,可見譯者大多繞道而走或略去不譯。我們不妨來看看這方面的情形。
例一:王維的《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
但去莫復問,白云無盡時。
詩的開頭寫飲酒餞別,是點題。第二句設問,君到哪里去。由此引出下面的答話,過渡到寫歸隱。這一質樸無華的問語,表露了作者對友人關切愛護的深厚情意。送別者的感情起始就滲透在字里行間。“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不得意”三字,顯然是有深意的。不僅交待友人歸隱的原因,表現他失意不滿的情緒,也從側面表達詩人對現實憤懣不平的心情。這三字是理解這首詩題旨的一把鑰匙。詩人在得知友人“不得意”的心情后,勸慰道:“但去莫復問,白云無盡時。”你只管去吧,我不再苦苦詢問了,其實你何必以失意為念呢?那塵世的功名利祿總是有盡頭的,只有山中的白云才沒有窮盡之時。這兩句表現了作者很復雜的思想感情:既有對友人的安慰,又有自己對隱居的欣羨;既有對人世榮華富貴的否定,又似乎帶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聯系前面“不得意”三字看來,在這兩句詩中,更主要的是對朋友的同情之心,并蘊含著詩人自己對現實的憤激之情,這正是此詩的著意之處和題旨所在。從寫法上看,前面四句,寫得比較平淡,似乎無甚意味,最后兩句作結,詩意頓濃,韻味驟增,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當然,如果沒有前四句作鋪墊,這兩句結尾也就不會給人這樣強的“清音有余”的感覺。
依筆者之見,詩中的“南山陲”和“白云”就是意象。前者尚可根據上下文理解,而后者則是典型的意在言外。對此意象的翻譯可謂五花八門,對語句的理解也各有不同。限于篇幅,我們看國外譯者對最后兩句的翻譯。
But oh seek not to pierce where my footsteps may stray,
The white clouds will soothe me for ever and ay.(Her-bert A.Giles)
You went.I asked no more.The white Clouds pass,
And never yet have any limit found.(W.J.B.Fletcher)
So give me leave and ask me no questions,
White clouds pass there without end.(Witter Bynner)
Giles讓白云撫慰詩人而不是友人,把對象搞顛倒了;Fletcher把云擬人化了,似乎也隨著友人的離去而永遠飄走了;Bynner筆下的白云沒有任何含義,僅僅是物象。再看國內譯者,最后兩句的譯文也是不知所云。
Be gone,ask no more,friend,
Let cloud drift without end!(許淵沖)
許淵沖的譯文還不如Giles和Fletcher,至少后者還清楚此白云非彼白云,是意象詞。事實上,在有限的詩歌篇幅里要融進豐富的意蘊實屬不易,不像《馬勒復活交響曲》,創作者可以不斷反復著“白云無盡時,無盡時,無盡時……”音樂漸漸緩慢,漸漸消失,從而讓聽眾悟出詩人在這短短五個字中所蘊含的深意,即要永遠辭別這個混濁黑暗的世界,飄然而去,歸臥南山。但這不是悲觀厭世的思想,不是死亡而是生活。當然,這種表現手法一不小心也會使聽眾誤入歧途,產生厭世輕生的想法。
例二:常建的《破山寺后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
詩人在清晨登破山,入興福寺,旭日初升,陽光照耀山上樹林。詩人穿過寺中竹叢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唱經禮佛的禪房就在花叢樹林深處。這樣幽靜美妙的環境,使詩人驚嘆、陶醉、忘情地欣賞。寺后的青山煥發著日照的光彩,鳥兒自由自在地飛鳴歡唱;走到清清的水潭旁,只見天地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湛然空明,心中的塵世雜念頓時滌除。此刻此景此情,詩人仿佛領悟到了空門禪悅的奧妙,擺脫塵世一切煩惱,象鳥兒那樣自由自在,似乎大自然和人世間的所有聲響都寂滅了,只有鐘磬之音,這悠揚而宏亮的佛音引導人們進入純凈怡悅的境界。鐘馨之音,遠遠超出了“晨鐘暮鼓”的報時功能,而被賦予了寓意深刻的象征意義。
這首詩題詠的是佛寺禪院,可我們分明感受到詩人抒發的寄情山水的隱逸胸懷。通過后四句詩中的意象,如“山光”、“鳥性”、“人心”、“萬籟”和“鐘磬音”等,又通過“悅”和“空”兩個動詞,詩人欣賞這禪院與世隔絕的居處,領略這空門忘情塵俗的意境,寄托了自己遁世的情懷,禮贊了佛門超凡脫俗的神秘境界。我們不妨看看不同譯者對后四句的翻譯:
Around these hills sweet birds their pleasure take,
Man's heart as free from shadow as this lake;
Here worldly sounds are hushed,as by a spell,
Save for the booming of the altar bell.(Herbert A.Giles)
In the mountain light!Like one's dim reflection
Lo!The heart is melted Wav'ring out of sight.
All is hushed to silence Harmony is still.
The bell's low chime alone Whispers round the hill.(W.J.B.Fletcher)
Here birds are alive with mountain-light,
And the mind of man touches peace in a pool,
And a thousand sounds are quieted
By the breathing of a temple-bell.(Witter Bynner)
In mountain's aura flying birds feel pleasure;
In shaded pool a carefree mind finds leisure.
All worldly noises are quieted here;
I only hear temple bells ringing clear.(許淵沖)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這兩句中,后半句比較復雜,尤其一個“空”字。Giles把“空”等同于影子,來無影去無蹤;Fletcher把“空”理解為像冰雪一樣的東西可以融化;Bynner的翻譯似乎比較接近原詩,寓意“平和”;許淵沖則把“空”解釋為“悠閑”。事實上,一個“空”字寓意深刻,遠非其字面所能涵蓋。首先,這首詩題詠的是佛寺禪院,佛教提倡六根清凈,無欲無求,苦修苦行正是“空”的寫照。其次,一個“空”字,沉寂了“潭影”,淡定了“人心”。潭影幽暗而似空無一物,人心無所求無所欲,空空中而異常的滿足。要在短短一行詩中把“空”的內涵表現出來,讓讀者心領神會,豈是“平和”、“悠閑”兩個字所能涵蓋?
最后兩句“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的翻譯關鍵在于“萬籟”和“鐘磬音”。前者分別被譯成“塵世的聲音”、“所有的聲音”、“千種聲音”和“塵世的噪音”等。筆者比較傾向Giles的翻譯,加上一個“worldly”。因為詩人在這里一定是有所暗示的。如果結合常建的身世,這樣的理解當是順理成章。僅以“聲音”譯之,無法給人想象的空間。譯成“噪音”,似乎這世界一無是處,這不合常理且顯得太極端。關于“鐘磬音”,四位譯者都只譯為平常寺廟的鐘聲。殊不知,在萬籟俱寂之時,只在那鐘磬上一擊,余音裊裊,不絕如縷的金玉聲縈繞在禪院上空,與那日光相融,與那紫煙相繚,仿佛梵音入耳,滌蕩盡胸間塵垢,悠遠悠長,回味無窮。詩人在山光潭影之中,早已俗塵洗凈,心空性悅,完全遁入于自然與禪宗那完美統一的靜美世界中。鐘磬之音反襯出闃寂的禪院更為空寂,肅穆的世界更為莊嚴。有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二者可謂有同工異曲之妙!
一些西方詩人陶醉于中國古詩意象,也會創作一些模仿之作,如美國詩人施奈德的山水詩,單從意象角度品味,實實地差之千里。
Pine Tree Tops
in the blue night
frost haze,the sky glows
with the moon
pine tree tops
bend snow-blue,fade
into sky,frost,starlight
the creak of boots
rabbit tracks,deer tracks
what do we know
施奈德深受美國詩哲梭羅返回自然的影響,力主心靈的純凈,并向東方取經,修行禪宗。但是,他骨子里承繼更多的還是歐洲和美國的傳統文化。他的詩往往開頭很有道家韻味,似有深意在其中,但是,漸漸地西方浪漫主義田園詩的原型顯露出來,即主體想象力的支配,主體對客體的說明和凌越,在貌似東方式的物我兩忘境界里兜了一圈后,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主體對客體的反應和反思之途。除了貌不合外,神也不似。充其量只是描寫了一幅冬日夜晚的場景,它能讓讀者讀到背后的什么內容呢?作者自己在詩的最后作出了回答:若何吾所知。
葉維廉對王維和華茲華斯的山水詩作過評論,比較準確地闡述了中西方詩人的詩學觀:
簡單地說,王維的詩,景物自然興發與演出,作者不以主觀的情緒或知性的邏輯介入去擾亂眼前景物內在生命的生長與變化的姿態;景物直現讀者目前,但華氏的詩中,景物的具體性漸因作者的介入的調停和辯解而喪失其直接性。[3]85-86
山水景物存在于自然界中,而中西方詩人在表現它們的時候卻是大相徑庭。葉維廉把山水景物通稱為物象,這顯然混淆了他自己先前的評論。在筆者看來,應有物象和意象之區分。如果說山水景物在華氏詩中只居次要位置,是一種襯托的話,應視為物象;王維詩中的山水景物則是美感關照的主位對象,“即物即真”,應視為意象。現代批評家呂恰慈(L.A.Richards)曾把隱喻(Metaphor)的結構分為vehicle與tenor兩部分,即喻依和喻旨。喻依者,所呈物象也;喻旨者,物象所指向的概念與意義。而意象則是喻依和喻旨的合二為一,這正應和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道家思想,即“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很多中國古詩不依賴隱喻,不借重象征,而是原樣呈現。由于喻依喻旨的不分,所以也無需人的知性的介入和調停。王維和他的一些同輩詩人的作品中那種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寂中之音,音中之寂;虛中之實,實中之虛……原是天理的律動,所以無需演繹,無需贅詞,通過意象,詩人藏于心中的抱負、情懷、憂郁和欣喜都被讀者悉數收入腦中。
從中國傳統詩學到意象及至意象所含有的特征,古詩意象有其興起、發展、成熟的過程。它的意在筆墨之外,只將一些具有特征的“點”或細節點染出來,其余留給讀者盡情想象;它的“象外之象”,蘊含著多層意味;它的“不著判斷一語”,深藏作者的主觀傾向等特征,在翻譯中會留下無盡遺憾。中國古詩一旦譯得像西方詩那般直接,其本身固有的含蓄就蕩然無存了,最終淪落成四不像的東西。
注釋:
①周亮工:《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宣統三年國學扶輪社石印本。
[1]蔣寅.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3.
[2]劉燕.現代批評之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3]葉維廉.中國詩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85-86.
[4]陳仲義.“意象征”——現代詩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J].學術研究,2002(11).
[5]武新玉.從主體性意象疊加到客體性意象并置[J].外國文學研究,2010(1):76.
[6]劉華文.詩歌翻譯中的格物、感物和體物[J].外語研究,2010(4):75-78.
[7]叢滋杭.漢詩英譯中的意象轉換比較[J].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05(5).
[8]朱徽.中美詩緣[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9]William,William Carlos.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am Carlos Williams.New York:Random House,1951:264-265.
[10]趙毅衡.詩神遠游——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276.
[11]王士祺.帶經堂詩話(引《林間錄》)[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82.
[12]嚴羽.滄浪詩話﹒詩辯(見《詩人玉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
[13]呂叔湘.中詩英譯比錄[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0:序.